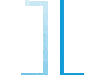利維坦按:還記得電影《分裂》(2016)里那個叫凱文(James McAvoy飾)的多重人格患者嗎(23種人格)?試想,一般人意識到自我是一個「我」,而對解離性人格障礙患者則意味着「我們」,這麼多「自我」該如何相處?
解離性人格障礙患者的每一個人格都是穩定、發展完整、擁有個別思考模式和記憶的。分裂出的人格包羅萬象,可以有不同的性別、年齡、種族,甚至物種。他們輪流出現控制患者的行為,此時原本的人格對於這段時間是有意識也有記憶的。分裂出的人格之間知道彼此的存在,稱為「並存意識」(co-consciousness),如果並存意識較好的,他們甚至可以內部溝通,或進行內部會議;也有一些情況,人格之間並沒有察覺彼此的存在,這會導致嚴重的「遺失時間」現象——比如文中出現的那種不記得自己已經結婚的患者。
本文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由大藥在利維坦發佈

在40歲之前,莫蘭尼·古德溫(Melanie Goodwin)對自己16歲以前的生活沒有任何記憶。接着,一場家中的悲劇在她身上觸發了毀滅性的精神病變。瞬間,她意識到存在於她體內的其他的個體,將她們分隔開的壁壘開始崩塌。這些不同的個體身份都屬於她,但是,莫蘭尼察覺到,這些個體分別是從3歲到16歲,和從16歲直到成年的不同「自己」。
這些人格的年齡不是隨機的。在不同的聲音交織混合而成的同一個顯意識中,她記起了自己在童年被虐待的經歷,第一次發生在她3歲時,最後一次在她16歲的時候。「我沒有證據,」她強調,「我只能經受着我以為發生過的事情,和我的現狀。」
莫蘭尼的症狀以前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現在廣泛使用的名稱則是解離性人格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名字的更替反映了人們對這種疾病認識的更新:它不僅僅改變患者的人格。記憶、行為方式、態度和心理年齡都會隨人格切換。
「我們」——她通常把她自己稱為「我們」——「有不少成年人的成分。成長應該是沒有斷層的……但是我們沒有自然地長大,我們使用更新的形式自我的形式成長的……最後,這裏有9個不同的成年身份,每個身份都管控着不再受虐的成年生活中的不同階段。」
她把和解離性人格一起生活的日子比作「在地獄中」。我們正常人習以為常的那種「我即自我」的狀態她的生活中瓦解了。對莫蘭尼來說,多重身份的突然鬥爭足以讓她失去理智。她怎麼可能找到辦法讓這些身份安定下來呢?
「在絕境中,你得靠消散自我的方式來活命。創傷會讓你覺得時間停滯。」
位於英國諾維治的博特蓋人格解離與創傷中心(Pottergate Centre for Dissociation and Trauma)的一間安靜的諮詢室中,莫蘭尼坐在沙發上,講着自己的故事。這家中心的負責人是萊米·阿奎龍(Remy Aquarone),這位精神分析治療師曾經掌管着國際人格創傷與解離學會(the Study Trauma and Dissociation)。
在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阿奎龍已經面對過數百個有人格解離病症的人。大多數情況下,他說,病人從5歲前就開始經受着虐待。
按照理論,在處理創傷經歷的嘗試中,孩子開始「解離」——他的自我被分成幾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來承擔受到的虐待、擔驚受怕的情感和身體上的傷痛,另一部分則伴隨着他繼續生活。或者,一部分被用來承受虐待,另一部分幫她拖着身子回到臥室,當第二天早上,她下樓吃早餐的時候,又是一個不同的人格主導着他的行為了。如果虐待持續了多年,過程中有受虐的場景和施虐者產生變化的情況出現,會促使其剝落更多不同的自我碎片。
人格解離使得孩子能夠繼續生存。事實上,「這是種終極的適應系統。它利用你潛意識的認知,通過改變你行為、想法的方式以保全自身,」阿奎龍說。
莫蘭尼這麼描述這件事:「在絕境中,你得靠消散自我的方式來活命。創傷會讓你覺得時間停滯。這種可怕的經歷持續了多年,所以這種『停滯』處處都有。」
不是每個經歷童年虐待(或者任何形式的長期創傷)的人都會有人格解離的症狀。根據他的研究,阿奎龍說,「人格解離」的形成還有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缺乏和一個成年人正常、健康的依戀關係。
從發展心理學的視角看,「依戀」有特殊的含義:它指的是在一個嬰幼兒和看護、養育他/她的人之間形成的聯結,這種聯結既是感情上的,又是在實際生活中的;「依戀」有助於嬰幼兒學習並管理他/她的反應。當由於喪親、遭受父母的忽略或者虐待時,這種聯結便無法形成,一個受到精神創傷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己來面對情況。
作為DID患者群體中的一員,莫蘭尼反思道:「在我們是小孩的時候,我們不知道還有一個可以護着你、幫你學會處理自己問題的家長的存在。」
擁有這種穩定關係的嬰幼兒在未來的生活中會過的更好,溫迪·瓊森(Wendy Johnson)說。她是一位在愛丁堡大學工作的心理學教授。「首先,他們對待他人的方式更成功;和人的關係更為融洽。他們掙錢更多,更受人尊敬、認可,更少地被絞入爭鬥中。他們的生活軌跡也更平緩,也就是說,生活對他們而言更加舒適。」
這不是說我們的性格在嬰幼兒時期就已經定型。一種相對穩定的環境,包括更穩定的關係和事業,能夠幫助我們維持更加穩定的人格。「我覺得,趨於穩定的生活環境有助於我們在人前展現這種人格上的一致性,」瓊森說。但是這些來自外界的影響變化了,我們也會隨之改變。
養育孩子,失業——這些重大的人生轉折都會觸發我們自己意想不到的新行為,對人的性格特質也會有所改變,例如對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和外向性(extraversion)的影響。這樣就能解釋,為什麼處在早期成年階段的年輕人會頻繁地向自我發問,瓊森補充道,因為,在這個階段,很多事情,包括家庭、周圍環境、朋友,都處在不斷的變化中。
沒有「依戀」和穩定的環境,對自我的統一認識就很難形成,解離下的自我會讓一個人的性格看起來相當的搖擺不定。莫蘭尼有一部分患有厭食症的自我,還有一部分無法忍受迫近的人格邊界而兩次試圖自殺。當她遇到勾起舊時的創傷的回憶的事物,例如某種氣味或者某個男人走路的方式,這些東西很容易就會嚇壞她3歲的部分;這時她會害怕地一動不動或者乾脆躲起來。另一方面,16歲的她又喜歡賣弄風情。
「誰」在她腦海中佔據了主動,她的行為就會因此變化,這合情合理。她並不是像3歲時的莫蘭尼那樣行動,她甚至一點兒也不記得自己3歲時是什麼樣子。她就「是」那個3歲的小孩——直到另外一個人格取代她的位置。

「我知道我結婚了。但是我沒有全身心地在『經歷』婚姻,更像是我在看着、觀察着這一切發生。」
由於在一種人格下經歷的記憶不總和其他人格共享,因此有些患有DID的人會「失去」生命中的幾段時光——他們覺得自己在時間中向前跳,一次能跳過幾天甚至幾周時間。「(婚後)有些人出去,和別人發生了關係。好吧,其實算不上什麼婚外情,因為這些人壓根兒就沒有關於自己結婚的記憶,」莫蘭尼觀察到。
對她來說,上述的影響讓人無法分清生活中事件發生的次序。「在嬰兒時代,你被生出來,然後就有了一個貫穿你人生的時間表。如果,你的自我破碎了,這個時間表也不存在了。」
被壓迫的正常情感反應使她的記憶更加模糊。她和阿奎龍都提到,正常的情感反應對於面對創傷來說至關重要。但是,這種情感的缺乏在虐待停止之後依然繼續着:它變成了莫蘭尼大腦運作的方式。「我知道我結婚了,」她舉了個例子,「但是我沒有全身心地在『經歷』婚姻,更像是我在看着、觀察着這一切發生。」
患有解離性人格障礙的患者總表示自己只有膚淺的情感,阿奎龍說,「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確如此,因為那個真正的自我,重中之重,被藏起來了。」對於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我們有着真正自我中蘊含着的感情強化後的記憶。它讓我們覺得,我們的自我是連貫的。「打個比方,我可以回想起自己青春期時的舉止,」他說,「但同時又有能把控自己「完整」的形象……而解離後,人格的運作方式是……他們不能回憶起自己過去的房子。」不論和家人還是老友在一起,與這些在過去有許多共同經歷的人(交流)可以增強這種多年來自我維持不變的感覺。但是這種對過去的人的依賴也有問題,因為,註定地,老朋友們會搬走;人總有一死。
宗教信仰在心理上的益處之一在於,理論上來說,和神的關係,以及與其有關的記憶,能從童年延伸至死亡,並且無論你在地球上任何什麼地方,它都伴隨着你。像阿奎龍所言,「你不能帶走它——它超越了物理的所在。」
也有其他的辦法可以讓「自我」在過去重現。心理學家們曾認為,懷舊感——這種利用記憶,多愁善感地回溯美好時光的行為——是消極並有害的。但是,現在有研究表明,事實恰恰相反。實際上,懷舊感能夠培養自我的連續感,並且增強人對這個世界的歸屬感。
這種始終如一且連貫的自我感知可以幫人掌控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社會生活。但是如果它能隨着經驗強化和弱化,或在DID的情況下完全消失,這種自我感知能夠反映真實的你麼?
「我們在實驗中得出的結論與前幾個世紀中哲學家、神經心理學家們的想法恰恰相反。」
「在《油膩》(Grease)中,姍蒂(Sandy)從她開始的乖寶寶形象轉變成後來一身皮衣,行為浪蕩的壞妞形象。當然這個吸着煙、跳着舞的人是姍蒂。但是同時確鑿無疑的是,這是她為了贏得同學們好感所設計好的表演,並不是「真正的」姍蒂。」
妮娜·斯卓明哲(Nina Strohminger)和她在耶魯大學的同事們在一篇論文中着重描述了姍蒂的現象,以探討「真正自我」的概念,這個問題並不局限於DID患者,而是與所有的人都有關。
斯卓明哲提出另外一個例子,一個信奉宗教、相當虔誠的人卻有同性戀傾向。「他的信仰禁止他做出同性戀的行為……他每天都在與這種傾向搏鬥,」她解釋道,「他哪部分才是真實的?是那個努力遏制同性戀衝動的部分呢,還是那個有同性戀衝動的部分呢?」
她發現,結果與回答問題的人有直接的關係。「你問自由主義者,他們會說,『啊,當然有着同性戀衝動的那部分是他真實的自我。』最終,問題的核心還是人的價值觀。如果你覺得,同性戀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就不會覺得這些內心深處的衝動有什麼錯了。」
斯卓明哲沒有見過哪個研究問過經歷內心衝突的人到底是怎麼想的。「但從在研究中,我自己觀察到的方方面面來看,可能的結果會是……你投射在別人身上的價值觀,也同樣約束着你的行為。」
「我是個心理學家,不是形而上學家,」她補充道,「如果你想得到什麼形而上的結論,你得清楚,正常情況下,人們每時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和他人的身份,這些想法是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處境上的。」換句話說,這些都不是絕對的。
但是,斯卓明哲發現,在人標誌性的行為模式中,還是有個業內始終認為對決定一個個體是誰至關重要的方面。它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人的記憶,無論這個人是外向還是內向,是和風順水還是一點就着。
她先進行了思維實驗。在一個實驗中,她要求志願者想像其他人以多種方式發生變化。最終,是人身上道德品質——這些相對的因素包括他們是否誠實、忠誠或者別的——讓志願者們覺得,對他們來說,最能標誌着一個人的轉變。
接下來,斯卓明哲轉向家庭成員罹患失智症(dementia,又稱為痴呆症)的家庭,失智症不僅導致記憶的喪失,也會改變患者的人格和道德觀念(有些時候是消極的改變,例如有些患者會有虛言癖的症狀,有時候則是積極的,例如患者變得更溫順和善)。親屬們匯報,當他們愛的家人喪失了記憶,他們還不會覺得家人變成了「不同的人」,這種轉變往往發生在道德觀念產生變化的時候。
「傳統意義上講,對人類身份的學術討論中,道德並沒有得到多大重視。相比之下,記憶和突出的特徵,例如性格,才是一個人最重要的部分,」斯卓明哲指出。「我們在實驗中的發現和前幾個世紀哲學家、神經心理學家們的想法恰恰相反。」
莫蘭尼說,她的幾個人格的確好像有不同的道德觀。但是,她將其歸咎於每個人個迥異的人生經歷,還有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在某種態度占上了風之後產生的錨定效應[譯者註: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是指當人們需要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數值作為起始值,起始值像錨一樣制約着估測值。在做決策的時候,會不自覺地給予最初獲得的信息過多的重視]。
的確,人的道德觀會隨時間產生變化,溫迪·瓊森強調道。「我非常相信,存在着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最終成功改變的人,」她說。
所以,決定我們身份的核心要素——起碼對於他人而言——是會改變的。這意味着,多數人擁有的這種堅實固定的自我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虛幻的,這種幻想讓我們避免了多重人格帶來的精神焦慮。而且,就莫蘭尼和其他DID患者的經歷來看,這種幻覺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不是一個人,但是我們都同意彼此和諧地共同生活。」
莫蘭尼的多重人格完全浮現的四年後,在她做圖書管理員的時候,她發現了喬安·弗朗西斯·凱西(Joan Frances Casey)名為《群鳥》(The Flock)的著作。她意識到,自己和作者凱西一樣都有DID。
她向結婚20年的丈夫提出了這個想法。「他說,『你知道麼,其實這還挺合理的,』因為,他有天對我說,『你要喝咖啡嗎?』我說,『成,來一杯吧。』接着第二天,『你要喝咖啡嗎?』我會說,『你知道的,我不喝咖啡,我對咖啡過敏!』16歲的那個「我」不能喝咖啡,但是我很喜歡咖啡。他曾經說,他根本不知道回家的時候會碰見誰。我(當時)還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結婚那麼長時間的丈夫都沒發現她有不同的人格,難道不是很驚人嗎?「(現在)他覺得,他居然從來沒提過這件事還真是挺瘋狂的……但是他愛我。我是個好母親,起碼把孩子照顧得很好……我很擅長於模仿別人的行為。」和其他有着DID的人不同,莫蘭尼真切地感覺到,她有一個佔主導地位的主要人格,這個人格的年紀和她的身體相符。所以,難道這樣就可以說,「真正的」莫蘭尼不是那個容易害怕的3歲小孩、那個總在調情的16歲姑娘,也不是那個64歲,坐在雷米·阿奎龍諮詢室的沙發上繪聲繪色地講着自己與眾不同的存在感的老太太嗎?
良好的治療可以造成巨大的改變。第一步就是要正確地診斷疾患,但是,醫師很容易將DID誤判成其他病症。聽見不同人格聲音的人有可能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在憂鬱人格和興奮人格間切換的人有可能被診斷成躁鬱症患者;有着擔驚受怕的三歲人格,因為害怕躲在醫院裏的人容易被認為是精神失常;(由於人格切換)情緒波動巨大的人有可能被診斷有邊緣型人格障礙。
並且,至少在英國,DID的診斷還存在爭議。在世界通用的精神病手冊上,DID位列其中[兩個手冊分別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編著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和世界衛生組織編篡的《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但是在實踐中,阿奎龍表示,仍然有精神病醫師不願意接受這種疾病的存在。據信,全世界有大概1%的人口罹患DID(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相同),但是有懷疑的聲音稱,可能是病人表演出了不同的人格,DID的本質是就是妄想。
大腦成像技術支持了DID並非表演的觀點,而且,也有其他的研究駁斥了上述的理論。例如,在2016年,倫敦國王大學的研究團隊發表了對65個經診斷患有DID的女性的研究。他們的結論是,有DID的女性不一定比正常人更易妄想、輕信或者產生錯誤的記憶。研究者們稱,這個結果挑戰了「妄想論」的核心假設。
莫蘭尼現在在一個名為「複數第一人稱」的解離性人格紊亂組織內擔任指導員。她經常與心理學家、神經學家、普通科醫生和醫護人員交流,普及DID的現狀。她和阿奎龍最近正在組織一場活動,這將是第一場為經歷創傷性人格解離的患者提供服務的活動,將來自國民保健署和社會各界報名參加的護工們聚集在一起。他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要真正地幫助一個人格解離的病人,一個有效的療程要花去一位專家數月的時間,並且,通常情況下,有效的療程不是公共服務(免費醫療)的一部分。
這種治療改變了莫蘭尼的世界,她說。當人格間的壁壘崩塌的時候,她完全無法自控。當她和一位治療師建立起強力的聯繫後,治療師才得以幫助不同的人格互相交流、尊重,使她內部的「戰爭」逐漸平息。
在她的多重人剛開始顯現的10年中,莫蘭尼發現自己除了日常生活行為以外,什麼都做不了。接着,當她學會了聆聽其他人格,聽到他們要講的故事後,「我們學會了分享共同的生活」。
當她覺得,自己能夠開始和丈夫出去幽會的時候,她體內的孩子人格會開始收集她需要的東西。「每個人都在幫忙拾掇。所以我們得為3歲的那個帶上像泰迪熊、被墊一類的東西,最後我可能得收拾出三四個包,因為每個人都要帶着自己的玩意兒。」
但是,即便她們達到了目的,但是莫蘭尼仍然沒有找到合適那一刻的衣服,她仍不能出門。因為,那一刻,她的意識是被8歲的人格佔據的,或者是16歲的那個,如果不按照她的年紀穿衣着裝,她們是不肯出門的。
有個階段,她曾經允許16歲的人格來「打扮身體」,如她所說,然後去圖書館上班:「我們會騎自行車去,因為16歲的那個不會開車。」她們達成了共識:白天上班的時候要由成年人來主導,晚上下班,她就把控制權讓給年輕的人格。「她們有機會做那些白天沒撈着做的事——小點兒的吃聰明豆、看天線寶寶,稍微大點的做做手工、玩泰迪熊或者拼拼圖。
「漸漸地,我們都開始明白作為整體我們在經歷什麼了,」她補充道。在一些危險的情形下,例如一個人走進圖書館的方式引起了可怕的回憶,「我會給那些小點兒的說,『我會讓你安全的……圖書館是個安全地方。讓我冷靜下來,看清楚我們是否真的處在危險中;而且我保證,如果我們真的面臨危險,我會解決的。』」
現在,那些人格依然在她體內,但是她們同時共存。「我們不屬於一體,但是我們容易和諧地共同生活,」莫蘭尼說。「這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