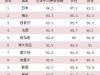作者按:講述故事的老人叫邵志寬,是筆者的外祖父。他生於1926年,是遼寧省莊河縣人。他童年上的滿洲國的學校,少年時期到遼陽日本紗廠做工,青年時期在滿洲國做行商,土改後參加過共產黨工作隊,中共建政後又到丹東做工人。2015年過年期間,筆者與他進行了幾次談話,重點講他在滿洲國和中共建政前的經歷,並錄音整理下來,留作資料。這份鮮活的記憶,對於了解滿洲國時期東北地區一般底層人民的生活,有着一定的參考價值。
以下為回憶全文,其中問句多為筆者和幾個親屬的插話。

1940年過年期間偽滿洲某地街頭秧歌隊
遼陽紡紗廠時期
邵:遼陽紡紗廠啊。
問:那是幾歲?
邵:那十五啊。十五去的,十五干一年,十六那年你大姥爺我哥,那個什麼,那時候我在那有病了,發瘧子,現在不知道叫什麼病,你大姥爺去了,說把我接回來。和管理員說一說,說我媽和我爹倆歲數太大了,八十多了,硬想我弟弟,我想領回去,你看行不行。我們宿舍的那個管理員哪,管着好幾百人,都是莊河這一個縣的,都是這一個管理員當頭,自己有個辦公室,就和他說同意了就能放你。要不啊,那個紡紗廠周圍都是大牆圍着,頂上都是電網,沒有出門證,根本就出不去。
問:那時候是日本人嗎?
邵:那時候是滿洲國啊,我十五歲。那時候那個人啊,那麼點小孩子,你怎麼能發出去,放心呢?十五歲小孩子就跟人走,就去紡紗廠去織布去了。日本人那個頭叫荒木,荒木下來招人,到莊河縣,25歲以下的,再歲數大的不要。
問:一天干幾個小時?
邵:一天也不少啊,干八個小時,九個小時那麼樣。三班倒,零點班,下午班,白天班。
問:能掙多少錢?
邵:都計件,不給你計工。每天你紡出來那個布,卸下來量一量,這一卷子布是二百四十尺,或是五十米,或是多少,就指着這個布算錢。一開始四個月試驗期,一個月給多少錢,一個月給多少錢。過了四個月自己上機器,就計件了,織多少給多少錢。
問:那時候一個月一般能掙多少錢?
邵:我這麼尋思,也掙不了多少錢。擱現在來說我這麼尋思也就一千來元錢多說着,也就個工錢。挺低啊,淨些小年輕小孩子,加上男的女的,沒有歲數大的。
問:記得你說下班還檢查?
邵:下班啊,自動自覺的,走到廠子那有個大門,自動站排,女的一趟,男的一趟,就從胳肢窩(由上到下手勢)這麼一摸,摸到底,放一個。再摸一個,再放一個。沒太耽誤事。一天下班摸這麼一遍,怕偷布,偷線,抓着又罰款,又打。
邵:吃飯的時候怎麼弄呢?吃橡子面加上豌豆擱那個線米裏頭,再就小米子。橡子面少,一般都是小米子,線米。一個月飯伙給多少,沒有糧票,什麼也沒有。那個飯啊,就像軲轆馬車一樣,修那麼一趟小型的火車道,拿那個車推,三層的。
問:菜都吃什麼菜呢?
邵:菜就是黃瓜片放點豆醬裏頭了,或者是蘿蔔絲子曬的乾乾的,不是鹹菜,也是炒的。再就有時候蒜毫,白菜,蘿蔔,也吃菜。怎麼弄的呢,一進食堂門,兩邊都是案子擺着菜,沒下班時候就都舀好了放在那擱着,一邊走道一邊你看哪個碗好你就端走吃,一人一個菜,飯呢,你自己盛,一個個大盆放在那,管飽。就是乾飯,有時候也有粥。紡紗廠就這麼弄。
問:在當時也算還行吧?
邵:小孩子夠嗆啊,三班倒,再一個不讓出去。
問:有沒有休息日?比如說禮拜天不上班?
邵:沒有,沒有禮拜。
問:比如說三班倒不上班的時候出去溜達行不行?
邵:出去溜達?有門崗啊。不讓,電網。得有出門證,就是個小監獄,不能去啊,不能去。我在那幹了不到二年。
問:這二年當中出來沒出來過?
邵:人家也不讓啊,沒出去。在裏頭呆不到二年。沒掙着幾個錢。
問:反正就是混口飯吃。
邵:那時候人就傻啊,尋思學手藝,那叫什麼手藝?再一個是,我這麼尋思啊,管你幹什麼也不能幹織布啊,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干別的活幹完了沒有事,這倒行。你看這一匹布,布面是不是得一米多寬,再加上二尺半來的,都是4000多線頭。一根線一根線你看多少線能擺出這麼一米寬。一個線有一個像家裏的鐵鋸條那樣的有個眼,一般寬,一根線一個小鐵條,四五百根線,有一根掉了,那小鋸條咔一聲掉底下去了,把那機器夾住了,站下了。你得趕快去把那個線頭接上,接上有個閘把子推上,咔噠咔噠又開始織了。你等這個還沒弄好,那台又停了。哎呀,那兩個錢掙得太不容易了。一點也坐不下,歡起來也忙不過來,有時候機器好啊,咔咔咔,你能稍微歇一會。一看那台又站下了,趕緊過去接上,一看這台又站下了。
邵:哎呀,傷心啊。咱們中國啊,這一個大房子四個車間,三個車間都是中國工人,一個車間是日本人。日本人也打工,男的女的,小年輕,他的那個屋裏呀,織布換梭子是機械化的,卡一聲那個線就上機器上進梭子裏了,中國人這三個車間就不行。就得人工換梭子。有的時候俺們沒有什麼事,就去日本人那個車間站着看,看他們織。
問:日本人說話你能聽懂嗎?
邵:不明白。有的時候他們也說幾句中國話。
問:他們和你們吃的一樣嗎?
邵:人家不在那吃啊。人家格外有食堂,日本食堂。不和中國混合。不在一個車間。都單獨的。
邵:你看那個布咱們穿着仿佛沒有什麼事,我感覺真不容易啊。一起先,弄大棉花,拿一個大桶子那麼盤盤盤,弄那麼老高,盤滿了就一大桶。那個車間就去紡線,我們這個車間就是織布。哎呀,那兩個錢掙得,太不容易啦。管幹什麼不能織布,線頭老掉。
問:紡紗廠這是哪年?
邵:紡紗廠這是遼陽,滿洲國康德十來年,十四年?31年到45年14年。
問:你是26年生的,15歲41年應該是康德八年左右。
邵:也就那麼來樣吧。
問:滿洲國歧視中國人嗎?是不是低人一等?害怕日本人嗎?
邵:八一五是光復,九一八來的。那時候也不惹什麼事,不是太害怕日本人。那時候日本人挺多啊。不是看不着日本人,縣級,科級幹部不少日本人,都是中國人當正的,日本人當副的。
滿洲國期間做行商經歷
問:那以前說的賣炕席是哪年?
邵:那就是紡紗廠以後的事了,我和我哥回來了,和我哥一人買了台車子,跑行商,也起個小票,辦的手續,叫行商手續。就是自行車馱着東西賣。
問:那時候自行車多少錢?
邵:記不清多少錢,那就不錯了。我們那堡子,咱家有兩台自行車,你說現在算個什麼。要擱現在就等於兩台小轎車。有些人上哪去上咱們家借自行車騎一騎。你說,上城壇,180里地,馱點鐵回來,賣給鐵匠爐,這那的,掙多一點錢。那炕席啊,滿洲國不讓隨便鋪,大孤山那邊,老百姓家弄點葦子回家編那個炕席,不讓出口,只能當地銷還行,往外賣就屬於經濟犯,抓着就沒收,這麼事。
問:經濟犯怎麼還管炕席?
邵:經濟犯啊,什麼事都管。你養豬,雞也要,棉花也要,不讓。咸鹽,洋火都得領。咸鹽一個大隊一個點,到多會兒多會兒放洋火,放咸鹽,到那去領。火柴都得去領。為啥大夥紡棉花呢?布買不着,那個線都自己紡的,買不着,沒有。
問:那時候多大?
邵:也就十八九歲。十九歲那年滿洲國倒的。賣炕席多大?也就十六歲,買個自行車,他們載10個炕席,我載6個,後來載8個。得黑天,睡一小覺再走。吃完飯走還是不行,看見不讓,派出所堵,區政府走。黑天走,天亮就能走到莊河西邊某地,那裏有個人家收炕席,收去了他賣,就算兌給他。
問:跑一回能掙多少錢?
邵:要是按現在這個錢,我這麼尋思能掙個一百五六十元錢。但是沒有地方掙,不像現在啊,誰都能掙着錢,那時候要不跑行商,就得窮死。你說扛活,誰用你。
邵:哎呀,那會兒那個苦惱勁就不用提了。你說我小時候你太姥領着我,在前爐我姥姥家住,沒有什麼燒的,就撿苞米杆子風颳掉那個稍,和苞米杆子葉,邊檢邊用胳肢窩夾着,那麼粗一捆就用繩捆上算一捆,往回走用繩背着回家燒。我問我媽,媽啊,你說這麼些地,怎麼咱們一壟也沒有呢?你說可山可嶺都是地啊,老邵家一壟也沒有。(哭了)「哎呀,孩子啊,咱們不是窮人麼。(落淚)地啊,不是人家地主的麼。咱們哪有啊。」就豆子落那個葉子啊,我媽那個姑舅弟弟在別的地方住,上我們這來種地,早早和他打招呼,你那個豆子葉子啊給我吧,拿個耙子去摟,拿回家來燒。你說那個苦惱勁,拿那個苞米葉子,豆根,拿回來燒。說「二月二,打豆棍」,那豆棍你說拔了幹什麼?就是拿回來燒。莊河也沒有什麼山,就算有山,山都有主的,你割柴火人家讓你麼?山都是人家的,也不讓去啊,摟點葉子也不讓。你說那麼多要飯的,誰愛要啊?有錢人家都養個大狗,要飯的拿個大棍子(做動作模仿),一邊走道,一邊這麼打那個狗,還領個小孩子,拿個葫蘆頭,裏面裝點菜湯,有什麼東西裝進去,你看那個窮人,就能窮到這個程度,能吃上飯就算好的。
邵:你說那次賣炕席啊,叫派出所抓住了,黑天叫他們堵住了。把炕席也留去了,自行車也給我扣下了。過了好幾天我去一看,自行車在後院給我放在自行車的棚子裏頭。操他個媽的我為什麼把氣門嘴心拔了,我就害怕他們騎,騎着我車子這一趟那一趟的,就給我造吧完了。我把氣門芯拔下來了。又過了好幾天,我就去要車子。那個警察你猜怎麼樣,喊我「哎呀,來來來,」我就去了,這一過去他媽了巴子好幾個人就把我抓住了。抓住了就拿棒子照我屁股上害,把我那屁股都打腫了。「你不是怕俺們騎麼?這回你來了,好,我就揍你!」我這一輩子,就挨這一回打,打了我七八棒子。屁股打腫了都不敢坐炕。最後把氣門芯給我了,「你騎走吧!」這個逼養的。滿洲國倒了我心裏想我能不能找到那個人,滿洲國這回倒了我也去報報仇,找幾個人把他好個打。怎麼找也沒有,找不着那個人。
問:你還真去找了?
邵:找了啊。另外當時咱們家那個炕席啊,從大孤山載來家,載到家就擱在豬圈裏頭。正好派出所有個姓畢的,姓畢這個人啊,他就可哪找事,聽說(咱家有炕席)就到咱們家來了。聽說派出所人來了,都穿着黃衣服,帶硬蓋帽子,我一看沒有什麼好事,騎着車子就躲了,咱們辛屯後面有個樹林子,上那裏去貓着。派出所人來了,就可哪找炕席。炕席藏在豬圈裏,拿苞米杆子這麼蓋着,能有十多捆炕席。你太姥爺一看派出所來了,他順着高粱稈子從豬圈那麼就跑了,從牆跳出去了。派出所來了也不走,這怎麼弄。後來就找於店有個王殿清,他過去當過警察,認識這個人,把他找去,弄點好飯好菜吃完了,又給他倆錢,說着,炕席沒有沒收也沒上報,把這一場戲弄過去了。我在房後趴着,聽說沒有事了,才回家。你太姥爺從豬圈跳出去跑了後來也回家了。說給他倆錢安排安排就算沒事了。為什麼說這段呢?因為還有下一段。就是滿洲國倒了,大夥一看拍手樂的了不得,操他媽這些警察媽巴子的都不敢坐在家裏了,大夥說那麼弄吧,去找那個姓畢的,你大姥爺也去了,東院的邵學林,俺們兩家,就受害的,就找到姓畢的,拿個棒子,找到姓畢的要打他。他們家嚇得,又磕頭又作揖的不讓打,又找人說合,拿出那個錢,雙份付給咱們。比如給他一百,滿洲國倒了要去揍他了給回來二百。具體多少錢不知道了,就打這麼個比喻。這個錢算要回來了。你說孩子啊,弄點炕席啊,不知道怎麼辦嚇完了。
滿洲國期間讀書經歷
邵:那你說(原來那麼窮)後來咱們家怎麼劃成分算中農成分?那是怎麼個道理?就是因為我們哥倆買個自行車子賣炕席啊,載豬崽子,載棉花啊,就這麼的(掙了點錢)。我們哥倆掙着錢呢,就買地。買了6天地,大概是二十四畝地。共產黨來了劃成分,破房子五間,地是這些,你姥姥分地那年我們結婚,分地她也有份,我們這些地也不多也不少,她要不來啊,還得往外拿。你姥來了,八口人也不九口人,地正相應,也不出也不進,弄個中農成分。以前都是貧農成分,比貧農還貧。
邵:你看我長這麼大還念4年書,俺們家你大老爺也沒念過書,其餘這些人沒有念書的,就窮到這個程度,你大姥爺十二歲就給地主放豬,冬天沒有事,就推碾子,弄高粱米,大碴子。柳條編那個斗,下面粗,頂上細,早年沒有秤,量糧就用鬥。這一斗是多少呢,45斤一斗。那時候扛活的一年掙三石糧是多少呢,35鬥。給人干一年活就掙那點玩意。你大姥爺給人家放豬,人家說小夥計啊,推碾子。你把這些米扛家去吧,回來再扛糠。你說彪不彪?扛着放頭頂頂着,兩個手把着,不敢扔,也沒有牆頭擱着,也不敢扔掉,扛家去一摸頭上的血一淌淌的,就那個柳條鬥壓得,不敢扔歡起跑回家把鬥放炕上一看摸一把頭出血了,壓得,腦瓜骨壓個大坑。低頭的時候一個癟子。你說彪不彪,不敢扔,怕給人扔了更壞了。
邵:後來你太姥爺也扛活,你大姥爺也扛活,輪到我怎麼樣,緩過來點了,沒扛活,還上了學念了4年書。小學畢業的時候我都哭了,再想往上念啊,也不供了,沒錢供。我去領那個小學畢業證書,就4年也發證書,往回走的時候我都哭了,這一生就這麼地了,念書什麼地沒有那個事了(難過)。我念書的時候,頭一年有日本語,上一年沒有日本語。
問:你是幾歲念的書?
邵:我是十歲,也可能十一歲念的書,念了4年。我頭一年第一課書是「一人二狗」,等我上學第一課書是「皇帝陛下」,第二課是「萬壽節」。
問:日語也學吧?四年都學?
邵:那時候滿洲國是滿洲國歌,日本國是日本國歌,唱完日本歌,就唱中國歌,是滿洲國,不是真正中國歌。滿洲國歌頭一句是天地內,「天地內出來個新中國,新中國變成個新天地,無苦無憂,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還有怎麼的,那些記不住了。東北這三個省是滿洲國,三千萬人口。講日滿親善。日本國歌我現在也沒忘。你給我錄啊,我唱個日本國歌。(唱)
問:您給翻譯翻譯什麼意思?
邵:哎呀翻譯不出來了。怎麼事的,忘了。小時候正好是滿洲國的時候。滿洲國倒台的時候19歲,安排勞工沒去把我樂完了。俺們爺三個,你太姥爺被安排去丹東浪頭修飛機場,趕車的,在那六個月,各家有壯勞力就得去。我哥哥輪着兩回勞工,一回去北滿,一回去本溪去柳塘下洞子,也是一回六個月,輪到我我趕上了,正好滿洲國倒台了我就沒去,沒去做勞工。
參加共產黨工作隊,親睹選客軍(壯丁)
問:後面這幾年你又幹什麼活了?
邵:當工作隊,工作隊完了在家幾年,後來上長春毛澤東汽車廠652部隊2年。
問:那你說要南下那是什麼時候?
邵:那是1947年也不48年。我是47年參加工作隊。
問:工作隊都管幹什麼?
邵:工作隊是區政府的區工作隊。就是地方搞工作的,打土豪劣紳,分田地,分房子,拉浮產,有錢人家東西都拉走了,攆到破房子住。就是當地幹部,也有槍,發的槍,79的,99的,長槍。兩個手榴彈,卡火那種的。那時候不光共產黨,還有好多(別的勢力),沒有槍也不行。我參加的是地方政府工作隊,就仿佛是公社似的,這一個縣13個公社都有工作隊,負責地方工作。小孤山47年下大雪,就把土豪劣紳打死二十五六個三十來個,還有個村打死四十多。主要是搞土地改革。以後區工作隊第二年1948年,俺們遼南省,丹東是遼東省,遼南省瓦房店是省會,區政府安排我去瓦房店重點培訓,培訓六個月,六個月完了。培訓叫什麼地方呢,叫軍政幹校。你看你姥爺也不善勁啊(也挺厲害的意思)在瓦房店軍政幹校培訓,六個月回來了以後要組織南下了,有的人就點名就得走,俺們家你大姥爺說老三那,能不能說一說咱們就不去了。我說那可不好說啊。(我哥哥說)你說也不掙銀子也不掙錢,你都有老婆有孩子都結婚了(那時候可能沒有孩子)就說南下了怎麼弄?你姥姥他爹,和我們那區政府指導員,就是一把手,二把手是區長,和他說一說,不去得了。正好趕上小孤山區和另一個區合併,撤掉一個村,工作隊減人,我要不下來也行,下來也算行,說一說。你姥姥他爹老王你太姥爺,和我們那指導員是怎麼個關係呢,你太姥爺的老媽是王瘋子,一年到頭要飯,瘋瘋癲癲的,就上指導員家要飯,他家孩子稀少,生個小小子,認個窮人乾媽好養活,就這麼認他個乾媽,和你太姥爺算干兄弟,借着減人這麼個關係我就下來了。槍就撤了,那時候也有緩了,國民黨就退卻了,共產黨開始勝利了。共產黨打蓋平了,那時候拉鋸戰。借這個機會,老王你太姥爺就把我發那個工作隊的黑衣服,一套單的,一套棉的,就給送去了,和干兄弟說一說,說他們家老太太老爹歲數大了,不讓他遠遊,衣裳交回來就打發他回家了。那時候要開個介紹信什麼的是不是好了,我現在工資能開四五千。這就回家了,又種地又幹這那的,後來就分開家了,我又去大營子學木匠,以後招工又去長春修毛澤東汽車廠好幾年,去梅河口修兵營一年來的,以後青城子鉛礦招工這才來到青城子鉛礦,56年端午節前後來的,原來某某某等幾個地方那些條子編的房子都是俺們來了蓋的。南下也沒去,工作隊也不幹了。
問:有沒有你認識的人說參加工作隊了後來如何如何的?有知道的嗎?
邵:都死了。興許有一個倆的。俺們指導員後來升的不善勁,後來丹東市地委書記。那個老宋家老太太的兄弟是俺們區長。
問:你要堅持幹革命現在興許也是大幹部,前提是能活下來。
問:那當時背着背包,捆着皮帶,也挺像樣。要不你姥姥能看中我這小眼不大一點不帶架的嗎?(大家笑)結婚那時候就是工作隊的。
問:那時候還掙錢麼?
邵:管什麼錢也不掙。三個月一條手巾,不掙錢,去當兵就是代耕,大夥給你種,挑糞,割,不用自己種。俺們那時候都是供給制,給你吃給你穿,不開錢,不掙錢,命都豁上了。俺們那個堡子烈士牌子,好多家都掛上了,打死老了。
問:你現在快90了在這享福,還是這樣好。當時要有手續就好了,就能享受待遇。
邵:我也去找過,有點不甘心,想去找一找。我和你媽(即筆者的母親)倆去上勞保去找了。找了他說啊,勞保主任姓羅,他說你哪年參加工作的?我說哪年。多會到礦里的?我說56年。他說啊,你老頭就消消氣吧,怎麼的呢?有個徐康全和你情況一樣,都是去工作隊以後不幹了,又來礦山當工人。有文件,拿出來看了,工作隊不幹了,不超過三年,又找到單位了,這樣的可以享受。你這樣間斷年限太多了,享受不着了。你老頭別上火,別生氣,回家坐着吃點飯,你就多活,那個錢就帶出來了。以後我也不生氣了,我也不上火了,拉倒吧。間斷這麼些年了,少掙就少掙吧。人過這一輩子,不容易啊。
問:你這一輩子經歷好幾個社會,年輕人聽起來挺稀奇。
邵:你說上瓦房店軍政幹校也不容易去啊。安排我去,一個區政府二十多個人安排我。我和你姥姥結婚二十一歲,你姥姥二十三,比我大兩歲。招人的時候我找個林會長,他是招人的頭頭,經常來咱們家說話。那時候參加兩個人,一個劉慶山,一個我。那時候也沒拿銀子也沒拿錢,就和他說,說區工作隊招人,你看我去得了。他就說回去研究研究看看啊,你聽信兒。哎呀,也相當緊張,你要不參加後方,我們家爺三個站不住腳,就得去前方。去工作隊一共就三個人,其他都上前方了,坐着膠皮車都送到莊河就走了,打仗去了。我們家哥倆還有個老頭,爺三個,不去幹什麼?區政府天天動員,客軍(就是招兵到外省去打仗),進行動員。不逼着你,叫你自己自願說話。俺那一個村上,三十多個年輕的民兵,從民兵里選客軍,都想些什麼辦法?弄那個炕上,燒的滋滋熱,再炒些花生叫你坐着吃,那些婦女啊,地下板凳坐着,唱歌,唱黨的這些歌,唱一會兒啊,你烤的受不了啊,就多少想站起一點來,站起來這些婦女馬上就鼓掌,你看某某某同意了,你看他都站起來了。你們大家快跟他學習啊!鼓掌!(大家笑)嘩嘩那麼鼓掌,又弄出一個。這是一種辦法,還有一種,民兵武裝隊長,他歲數大,領着民兵在操場跑步,領着跑的人啊輪班換,跑三圈兩圈就換別人,民兵就一個勁兒跑,誰要跑熊了站下,你看某某某又同意了,大家鼓掌!就不跑了,又弄着一個。你不發話,還有辦法。晚上去炕上繼續烤,坐不住起來了就算同意了,大家鼓掌,不讓坐墊。民兵跑步的時候一邊跑還一邊唱歌,不是瞎跑。唱《打沙嶺》的歌。「兵出山海關,遍地起狼煙。過了錦州,來到盤山縣。沙嶺做戰場,屍骨堆成山。血水流成河,人民遭苦難。白天不得閒,黑天不得眠,人民老百姓不得安康。」就唱這個歌,就是南方來的老兵唱的這個歌,不是老實坐着唱,一邊走一邊唱,是個悲調。打了三天三夜,血水流成河。這就是客軍,你說這些事我都趕上了,我一尋思,可趕緊找個地方站住腳吧。就是俺們那個兄弟邵志雲他堅持住了,這個人,又抗烤,又扛得住動員,怎麼說我也不去。咱們家爺三個,他們家就一個獨崩兒,哥一個,能豁得出去,怎麼說就不吱聲。我們家哥三個趁早想法吧。這一生就這麼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