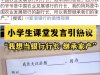清仁宗嘉慶像
顒琰繼位
嘉慶帝名顒琰,是乾隆帝第十五子,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母親是孝儀恭順純皇后魏佳氏。顒琰六歲開始讀書,以兵部侍郎奉寬為師,十三歲通五經,從工部侍郎謝墉學今體詩,從侍講學士朱珪學古文古體詩。十四歲那年,乾隆帝認定他為繼承人,按秘密建儲法,把他的名字寫上後,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面。也是這一年,乾隆帝為他完成了大婚。顒琰未即位前,喜讀歷史書籍,對上下幾千年曆朝治績一目了然。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被封為嘉親王。自此之後,每年東西陵春祀,壇廟祈禱,他都代表乾隆帝前往行禮。因此,雖然他的皇位繼承人身份內定後並沒有公開宣佈,但是他一天比一天更受乾隆帝寵信。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在位六十年的乾隆帝終於在勤政殿,召見皇子、皇孫以及王公大臣等,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屆期歸政。
這位王位繼承人主要有四點讓乾隆帝特別滿意:首先,從性格上看,顒琰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制力強。他起居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其次,此人品質「端淳」,生活儉樸,為人謙遜。特別是富於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摯,善於為他人着想;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歷了二十多年嚴格、系統、高質量的帝王教育,顒琰對儒家心性之學,頗有心得。他的修養是建立在學養的基礎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顒琰武功騎射成績雖然比不上他的父親和曾祖父,在兄弟當中也是首屈一指;第四,從外表看,顒琰長得端正、上相。他中等身材,皮膚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臉型介於方圓之間,顯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表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講話不慌不忙,富於條理。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親臨紫禁城太和殿,正式把皇位傳給嘉慶,自己稱太上皇,實行訓政。
嘉慶元年舉行的這個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嘉慶帝即位這一天,禮儀十分隆重,樂部設中和韶樂於太和殿前檐下,丹陛大樂於太和門內,傳位詔書、傳位賀表一應具備。九時三十二分,隨着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着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之一順利完成。嘉慶帝即位的消息,由禮部、鴻臚寺官員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國宣佈。
這一年,嘉慶帝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於經驗,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王朝的最佳年齡。
和珅跌倒
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乾隆得了輕微的感冒。嘉慶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乾隆拜年,乾隆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初二日,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徵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時,乾隆停止了呼吸。
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帝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着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普普通通的聖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大多數人認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發佈了一條讓全國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和珅被抄家時,抄出藏金32000多兩,地窖藏銀200餘萬兩,取租地1266頃,其他還有取租房屋1001間半、各處當鋪銀號以及各種珠寶、衣物等,其總家產折合白銀,有的說約1000萬兩,有的說2000萬兩,有的說達到了8億兩。當時清政府財政年總收入約7000萬兩。還有違制的珍珠、手串、寶石等,實際數字已經無法考據。
至此,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大老虎」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皇帝發佈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後,皇帝再次發佈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
這道諭旨發佈不久之後,他接到大臣的匯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准延期。皇帝發下了一道讓全國人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皇帝認為玉石雖美,無益民生。
連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嘉慶帝御書房像
腐敗成風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又可能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乾隆中後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一百數十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系隨之癱瘓。
甘肅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他們上下聯手,相互配合做假帳,把八百多萬元國庫銀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運作立刻癱瘓,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雖然殺了和珅,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典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底層官員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職員,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拔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裏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裏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藉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佔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裏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新政落空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連環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反腐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