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古今,這些傳統告密模式,或是群眾運動,或是當局撒網,雖然殘酷,但「親親相隱」總是最後的一道底線。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學的秦國,《商君書》裏雖有規定「民人不能相為隱」,否則必受株連,但云夢秦簡里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的規定。張家山漢簡里的規定更嚴厲:「子告父母,……勿聽而棄告者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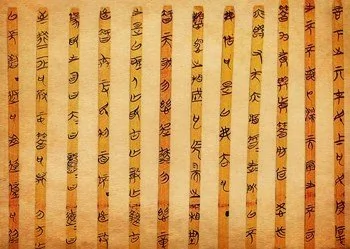
雲夢秦簡。秦雖鼓勵告密,但仍有「子告父母,勿聽」之規定
階級鬥爭新思維下,血緣感情須服從於階級感情,大義滅親式告密遂層出不窮
問題在於『近』什麼人的『情』,『認』什麼人的『親』。其中有一個顯明的界限,這就是階級立場
但在文革中,「大義滅親」事跡——子女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哥哥檢舉弟弟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弒母」這類案例,亦非鮮見,「親親相隱」的底線已全線崩潰。何以會如此?階級鬥爭新思維是個中關鍵。如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認為「任何種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問題就是階級性的問題」;再如1957年,針對社會上「不近人情」、「六親不認」的批評,《學習》雜誌刊文指出:「『人情』是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六親』也各有自己的階級地位,都是有階級性的。。」文章公開支持以「階級立場」為標準「大義滅親」:
「當一個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幹部檢舉自己親屬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與自己的反動階級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時,右派分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六親不認』。這又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好公民、好幹部為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要成為反革命分子或反動階級的俘虜。」
姚毫不留情地批評巴金的小說「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
1958年第22期的《中國青年》雜誌還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對巴金小說《家》的批評文章,在文章中,。文章說:
「(小說中的)高老太爺是這個黑暗王國的國王,所謂『一家之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人物,殘酷毒辣,死硬地維護封建道德,殺人不見血。……到他臨死的時候,作者不是用充滿仇恨的筆調去引導讀者無情地憎恨這條毒蛇的死亡,卻用十分哀痛的筆調叫覺慧、覺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個被有些人目為『英雄』的覺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慘的聲音叫着爺爺』,好象過去做了多少對不起祖父的事,現在在這最後的—剎那加以挽回,要請他『原諒』。這不是向地主階級妥協,為地主階級減輕罪惡,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又是什麼呢?而那位高老太爺竟也的確『原諒』了他們,小說中把他的臨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寫得那樣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動了,瘦臉上的筋肉弛緩地動着,他好象要做一個笑容,可是兩三滴眼淚開始落下來。他伸手在覺慧頭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開,然後低聲說:『……你回來了……馮家的親事不提了……你們要好好讀書……唉!』一聲長嘆,表現了高老太爺內心的懺悔,他在為覺民的婚事而難過。讀者看到這裏,不是會對他引起一種默然的同情和憐惜,覺得他『也是為了兒孫好』嗎?而這種和地主階級妥協的感情,會嚴重地削弱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論巴金小說<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並談怎樣認識覺慧這個人物》)
這類告密也不僅僅只是「文革」之惡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既以「階級情感」為準繩,自不可能僅僅發生在文革期間。「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所發生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數量,絕不會比「文革」期間更少。所以,若僅僅局限在文革範疇內反思「大義滅親」式告密,僅僅將其視作「文革之惡」,這樣的反思就難免有失偏頗。
「大義滅親」式告密不是「文革」特產,自50年代起即已泛濫
事實上,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鼓勵和宣傳,早在文革之前即已開始。以1952年「三反運動」中的《人民日報》為例,1月24日報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學青年團員王世桓檢舉他父親貪污行為》;2月4日報道了《北京大學學生展開坦白檢舉運動不少學生檢舉了自己親屬的違法行為》;2月6日,報道了《許東才站穩人民立場檢舉奸商父親》;3月8日,又報道了《門頭溝機電廠職工家屬大膽檢舉和規勸丈夫坦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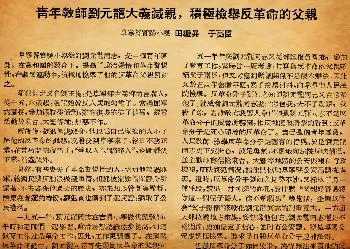
《江蘇教育》1955年第22期刊文表彰「大義滅親」式告密者
從這些報道里,不難看出當時的宣傳,竭力有意突出「階級情感」與「血緣情感」之間的鬥爭。譬如:「在運動開始時,(北京大學的)很多同學對檢舉貪污是有顧慮的。但隨着運動的展開,同學們對這一次運動的認識漸漸提高,顧慮也逐漸打消。中文系二年級同學胡祥達在運動開始時,想起他的家裏有兩本賬簿,其中一本是專門對付收稅人員的假賬。他想動員他的父親坦白,但是怕他的父親說他『忘恩負義』,因此他把這事放在心裏沒有說。後來他記起『中國青年』雜誌上批評鄭輝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時,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業聯合會節約檢查委員會檢舉他的父親,另一方面動員他的父親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學檢舉的案件達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檢舉自己家屬的。」「王世桓看出他父親心中有病,就對他解說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趕快坦白。但他依舊不肯低頭認罪。王世桓最後對他說:『你不坦白,我要向學校方面檢舉你。』他父親聽了非常氣憤地說:『我把你養大,你卻要檢舉我,你還有良心嗎?我要是特務,你也要檢舉?』王世桓堅決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務,我更要檢舉你!』」
「文革」期間大量幹部子弟被逼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這是一個特殊之處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特殊之處在於:在此之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主體,以「右派、「地主」等「階級敵人家庭」為主;1965年毛澤東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1966年「文革」爆發後,幹部家庭子女遂大規模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隊伍中來。如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回憶:
「我被『專政』了,他們還不放過那些比我小許多,正在上中學的小阿弟、小阿妹們。1968年2月,王少庸兩次給時任徐匯區『革委會』主任的黃克佈置任務,要他把家住在徐匯區的華東局、市委負責幹部的子女『管一管』。於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匯區紅衛兵軍區』主辦的第一期『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學習班』在上海縣北橋公社黃二大隊一座孤房子裏開班,歷時35天,有『學員』46人。第二期班從7月初開始,歷時45天,有『學員』92人。這兩期『學習班』共集中『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138名,全部是從14歲到20歲的初、高中學生。他們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關押、隔離、靠邊審查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黃克等人對這些青少年學生用盡了威脅、恐嚇、欺騙等手段:不許回家,不許與家裏通信,搞『一幫一』監督;大會套小會,個個要表態,搞人人過關;揭發父母親的『問題』,搞『家庭鬥爭會』;要大義滅親,與『反動父母』劃清界限……在兩期『學習班』中,他們先後11次組織『學員』們參加對他們父母的批斗大會,逼迫42名『學員』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面揭發父母的所謂罪行。這種卑劣的『學習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蠱惑和矇騙,造成了家庭分裂。這些『學員』中,先後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殺身亡,1人離家出走後下落不明。」
這種大規模的幹部子弟被逼加入「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現過。《紅衛兵懺悔「弒母」》這則新聞,就現有資料看來,大概也屬於幹部子弟「大義滅親」式告密——與兒子一起告發母親的父親,1940年參加新四軍,屢立戰功,文革前擔任本縣衛生局黨總支書記,文革爆發後被打成本縣衛生系統的的頭號「走資派」,兒子曾寫過大字報揭發父親;在母親說出支持劉少奇的言論後,父子二人先後前往縣群眾專政指揮部告密。
政治高壓下,許多「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
不可否認,建國後前30年發生的海量「大義滅親」式告密當中,確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階級感情必須高於血緣感情,是很真誠地在告密。一如當時的宣傳語境所言:「在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中,兒子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這正是人民群眾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十分可貴的」。但並不是所有人的「覺悟」,都能像方志敏(殺死親五叔)那麼「高」,多數「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紅衛兵懺悔「弒母」》這則新聞中,告發母親的兒子面對媒體,即公開承認:「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佔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當日已被打成「走資派」,母親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外祖父則在土改、鎮反中被槍決,自不難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態會有多麼強烈;其父在告髮妻子時的心態,大略也與兒子相似,作為一名現行「走資派」,其心態或許還會更為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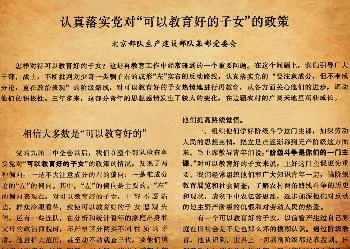
許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文革期間選擇「大義滅親」
李銳之女李南央在回憶母親對父親和自己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時,也認為母親告密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現實利益,「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說:「母親的『革命』變得越來越『真誠』,越來越『徹底』。她不但把父親的北大荒來信交給組織,還把夫妻間的枕邊話全部抖摟出來,用這種大義滅親的方式,證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黨的信任。……當我知道母親原來對『大躍進』持有與父親相同的看法;當母親一封封寄來對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單位領導揭發我的『反革命言行』;探親時領着我們早請示晚匯報;因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問題,讓我斷絕關係,在那以後,我心中殘存的一點親情徹底毀滅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個孩子的丈夫是反黨分子嗎?一定不是的,否則她怎麼會在20年後父親復出時動復婚的念頭?但是她被毛澤東所顯示出的絕對的威望、絕對的統治力震懾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階級』作為讓李銳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時她必須將自己與李銳劃分在兩個不同的陣營,才能夠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嚇壞了,她不能想像自己永遠和別人合住一個單元(母親在延安的信中,記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窯洞);她不能想像自己永遠做一個爐前工(母親在東北糖廠的信中,記述了受不了頂班的生活);她不能想像自己經過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幹部的優越生活條件和特權,從此不復存在(母親信中屢屢流露出瞧不起工農幹部和『舊』知識分子的態度,她在東北的信中記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驕嬌品格,決定了她根本無法面對這樣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復從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後只有緊跟毛澤東,除此別無選擇。」
再如:《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楊沫和他的丈夫馬建民,在當年的政治高壓下,也陷入了「大義滅親」式告密,互相揭發,並且招招險狠,直取對方政治生命。對此,楊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種高壓之下,人首先要生存,為生存而奮鬥。別的如夫妻之間的感情、倫理、道德、親情等等全顧不上了。我父親揭發母親1936年沒有入黨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啥重要問題,只是一個入黨手續不完備的問題。在巨大的壓力下,他為了表現自己聽黨的話,忠於革命路線,才把母親的這個事情交代出來了。」「母親也開始毫不留情地揭發父親。父親與武光的關係,父親與鄧拓的關係,這都是母親可以回擊的武器。」

晚年楊沫夫婦的合影
於2011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