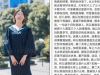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紐約一個青年醫生家中敘述身體狀況的胡適,突感不適,急送醫院後發現是突發胃潰瘍出血,吃藥後無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醫生輸血搶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險,醫生決定施行手術,結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後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適突然收到一個神秘人物的來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戰期間一度擔任中央社戰地記者的曹聚仁,於國民黨退往台灣後的1950年,別妻離雛獨自移居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島日報》專欄「南來篇」上發表文章,放聲高歌「我從光明中來」,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脫離《星島日報》加入新加坡《南洋商報》,並以該報記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的接見。據傳聞,後來曹氏又自香港潛往台灣,受到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秘密接見,並藉此做蔣氏父子的工作,說毛澤東給蔣介石制定「一綱四目」、「只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蔣氏父子以「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等六點意見相回應。曹氏曾建議,在兩岸和平統一後,蔣介石可將廬山作為終老頤養之地等。再之後,曹氏行動更加神秘莫測,他的妻子、親屬皆不知其在國共兩黨之間來回搖晃,整天折騰了些什麼。〔18〕
就是這樣一個神秘兮兮、見首不見尾的人物,於1957年中國大陸山雨欲來、引蛇出洞,「反右」天羅地網即將全面撒開的明媚春天裏,突然有些神經質地致信胡適「勸降」。據胡適3月16日記載: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此信大意是說他去年秋間曾到北京、上海去了「兩次」,「看到了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國,等先生看了之後再下斷語何如?」
他說他「願意陪着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養病的胡適,自然知道這個「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對他統戰的布袋戲。對此,胡心中生發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隻蒼蠅的感覺,但冷靜一想也就釋然了。凡蒼蠅或其他諸如螳螂、蛤蟆之類的弱小的動物,為了生存,必然要呈張牙舞爪狀,以壯聲勢,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噓叫嚷一番,拉個大旗,扯個滿身佈滿疙瘩的假虎皮,甚或與樹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鱷套套近乎,亦屬天下政客,特別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慣用的伎倆,不足為奇。於是,胡適在曹氏來信的信封上批了 「不作復」三字,繼而派人將信轉交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作為「匪情」研究資料予以處置。
剛把曹氏的陰影在腦海中蒸發,3月24日,仍在床上休養調治的胡適又收到小兒子胡思杜發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從郵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是7年來第一封信。信是寫給『媽媽』的,信凡4頁,末後說,爸爸那邊,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沒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寫信給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為已寄出了,所以偷寫這信給媽媽。殊不知中共已改變計劃了,不要他出面寫信,另叫別人(如曹聚仁之流)寫信。」〔20〕胡適乃一介儒生,但畢竟又在政治場面上混跡了多年,對中國人下愚上詐、不講信用,以及政客們慣用的陰謀或陽謀等種種政治手腕還算有較深刻的了解。儘管一直沒有發現可靠資料證明他此次的猜測是否正確,但就那時的政治形勢推斷,當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給胡發信,或許正是這個計劃改變之後的另一種行動。
遙想八年前北平那個圍城之日,吃慣了洋麵包的胡適,想過一種「麵包與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決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國時代的魏延,腦後長了反骨,堅決不按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針辦,在撤退的問題上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胡思杜舊戲重演,同樣不按胡適的既定方針辦,自作主張留在即將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時。如果世間真有上帝,胡小三這個抉擇,當是上帝之手於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適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中,上帝為其設立的最大、最令人牽心扯肺的一「難」,是「開五百年文化新運的一位大師、老祖胡適」(唐德剛語),在「得道」路上最為辛辣痛苦的心靈煎熬,而這個煎熬隨着時間的推移與政治演變越發嚴峻與不堪忍受。
1958 年3月,胡適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東方學術座談會」,偶爾從「泛亞社」香港來電獲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職下放勞動。此時的胡適心中雖犯嘀咕,但並沒有向最壞處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這個不幸的兒子。到了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灣作關於五四運動的廣播講話,「泛亞社」香港來電傳出胡思杜於「去年八月自縊身死」的消息。胡適先是一驚,差點一頭栽於地下。待鎮定下來又將信將疑,且從心理上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適致他的學生蘇雪林信中說:「承問及小兒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這個去年八月自殺的消息是一種有惡意的謠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間尚得友人間接傳出思杜被送東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謠言,當日即用長途電話告知內人,叫他不要輕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對於胡思杜的自殺,胡適仍是疑多於信。而事實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個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確切年頭是1957年9月,但死於那一日和具體死亡細節一直未搞清弄明。據耿雲志所撰《胡適年譜》,世人看到的是下列幾句簡單的記載:
九月廿一日,次子思杜因被定為右派,遭到批判而自殺(時在唐山鐵道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任教)。死前寫有遺書給他的一位堂兄。這遺書只剩下殘存的一角,那上面還可以看到這樣的話,(希望他們努力)「工作,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還有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給你們」的話。署的日期是九月廿一日。〔21〕
1950年9月,因胡思杜以「大義滅親」 的方式痛罵「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有功,一度受到學校領導的表揚,並於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結束後,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教研室)出任歷史教師。此時的胡思杜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一不小心成了「狗」的父親「贖罪」,同時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是組織上一直處於考驗之中,加之全國上下正在批胡適的反動思想,使他受到連累,夢想遲遲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幾年。到了1957年,全國興起了「反右」運動,不明就裏的胡思杜開始積極、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領導提教學改革建議,學院領導見一個「走狗」的兒子竟然犯上作亂,於佛頭抹糞,盛怒之中立即決定施以顏色,打擊胡思杜的囂張氣焰。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評》為題,發表「本報訊」,報道該校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教師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文中特別註明內容是「胡適的兒子」胡思杜所說。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隨着「反右」運動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來示眾並接受革命群眾批鬥,未久又被學院定為「向党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突遭重創的胡思杜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佈和父親劃清了界線,為何此時又把自己與這位「人民的敵人」捆綁在一起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精神崩潰,約於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殺,年僅37歲。
此前在政治上受胡適這個「人民的敵人」牽連,胡思杜一直沒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條,算是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落了個《紅樓夢》結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在自殺前,胡思杜留了一封遺書在枕頭底下,因大陸已無直系親人,遺書指名寫給當時在北京鐵道部印刷廠一位叫胡思孟的遠房堂兄。胡死後,單位人員發現遺書,便打電話把胡思孟叫到學院處理後事。胡思孟到達時,看到學院貼滿了批判胡適和胡思杜的大字報,學院領導告訴胡思孟,說你這位不爭氣的阿鬥式堂弟胡小三兒,腦後確實又像魏延一樣長着反骨,他的做法屬於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至於畏的什麼罪,自殺的具體時間以及死前死後的具體細節,學院領導沒有說。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間小黑屋裏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許多蒼蠅在飛舞,棺材裏有一白布,揭開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變得烏青的屍體,看樣子已死去好幾天了。胡思杜遺書的內容大意是: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我一定不在了。你不要難過,我的一點錢和公債券留給你,供給你的孩子上學,一塊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吧。〔22〕
因胡思杜屬於「自絕於人民」 的反動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學院領導追問具體細節,只好懷着悲痛與學院的打雜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個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拿了遺書上面說的錢物,另外還有一件舊皮襖、一件呢子衣服,外加一些書刊回到北京。「文革」爆發後,紅衛兵抄家,胡思孟怕受胡氏父子的牽連,將胡思杜的書刊大部分燒掉,遺書也撕毀,只有一個邊角壓在箱底沒撕掉。許多年後,胡思孟在清理箱子時發現了遺書邊角,交給了胡適家鄉安徽省績溪縣政協副主席顏振吾。後來,正在編寫《胡適年譜》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耿雲志聽說此事,找到顏振吾,把殘片上的文字抄錄下來,編入了《胡適年譜》。再後來,據耿雲志和前往胡思孟家中訪問的南京大學教授、胡適研究專家沈衛威共同估計,胡思杜自殺的具體時間,應是在9月21日寫完遺書之後,但詳細日期難以弄清,只能暫定遺書上這個日子作為胡思杜死亡之日。〔23〕
1942年1月6日,胡適因想念離開在美國求學的兒子胡思杜,特別在日記中寫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頗想念他,用毛筆寫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綏遠大同時在火車上作的一首打油詩寄給他:父子打蒼蠅,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兒,不作自了漢。」〔24〕
想不到十五年之後,胡思杜一根繩子作了自了漢,算是一了百了了。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和荒誕,將胡適的自由主義大旗扔進了雖有前仆但無後繼的悲觀黑洞裏。據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江澤涵回憶說:「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後期,大約是1974—1975年前後,從美國給我們寫信,我們作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長時間與他失去了聯繫。」「他信的內容主要是了解我們的近況,同時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聽到關於思杜自殺的消息了。因為胡適遺囑上說到他們兄弟倆分財產的事,他想證實思杜是否還在人世。當時,我們全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幾十年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惹出禍端來,就把這封信交給學校的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結果沒有回答我們。我們也不敢隨便、輕易寫回復祖望的信。直到 1976年以後,中國的情況發生了大的變化,我們才與祖望恢復了聯繫。」〔25〕也就是說,直到這個時候,胡祖望才總算證實了弟弟已經去世的消息,此時距胡思杜自殺已19年矣。
江澤涵說的胡適遺囑,是指1957年經歷了半夜大吐血、胃潰瘍切除手術、曹聚仁致信勸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來信等一連串惡性和奇里古怪的事件之後,胡適覺得自己身體極度虛弱,精神鬱悶至極,可能將不久於人世,遂於6月4日在紐約州紐約市第十七區雷辛頓大道四二○號諾林傑、李格曼、班尼塔與查尼律師事務所,在律師和證人劉鍇、游建文、Harold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場證明並簽字的情況下,立下了最後一份遺囑。該遺囑共分八條,其中:
第二條確信中國北平北京大學有恢復學術自由的一天,我將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離開北平時所留下的請該大學圖書館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內全部我的書籍和文件交付並遺贈給該大學。
第三條我把在紐約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書籍交付並遺贈給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並請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與台灣大學的毛子水教授兩人中的存在者依他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與文件的保管、編輯與出版。
第四條我把我的財產,無論動產或不動產,無論存在於何處,所有其他部分,餘剩部分,遺留部分,交付並遺贈給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後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則給我的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兩兒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額即歸這子息;但如任何一兒先我而去世,而無子息,他的份額即歸我的另一兒,而如他那時已去世,即歸他的子息。〔26〕
胡適立畢這份遺囑三個多月,胡思杜懸樑自盡,再也不需要他的遺產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書、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馬分屍,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 年12月15日,胡適倉皇離開北平之前,只揀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認為最重要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頭記》帶在身邊飛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貴藏書和手稿、書信、日記、照片等個人資料幾乎全部存於北平東廠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這批「貨物」被弄進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隨着批胡運動展開,胡適留下的書信、日記等資料,正好成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彈。到了1954年,這批珍藏作為胡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層指示下,於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覺地經歷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殘暴的割裂。除損毀散失遭竊外,胡適藏書、手稿、日記等珍藏從此「身首三處」,即北大圖書館存有部分胡適藏書中的普通書籍;劫後餘存的105種善本古籍由北京圖書館佔有;其他15000餘件胡適書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則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搶先佔據。正是由於胡適秘籍的流散,使許多與這批書信、文件有關聯而留在大陸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受到牽連而為此倒了大霉。後來官至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因早年與胡適的私人通信被發現,「文革」中這批書信成為擲向吳氏的投槍,直至令吳走上死亡的祭壇。在一連串的批吳鬥爭中,儘管「革命者」認為吳晗的信是「投靠胡適的鐵證」,胡、吳二人是「反動的政治關係」,走的「是一條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吳是「美國奴才的奴才」等。〔27〕但在胡適留在大陸的幾個最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一個至死沒有佛頭抹糞——寫批胡文章的就是吳晗。這一點,是當年的胡適沒有想到,也是許多人為之不解的。至於胡適的遺囑,儘管後來傳到大陸之後一度引起北京大學的注意和呼應,但其命運與路邊飄零的一張包油條和煎餅果子的廢紙沒什麼兩樣,誰還把一個死去的胡適和留下的一張上寫 「遺囑」的廢紙當回事呢?
與胡適遺囑命運相似的是,1949年,江澤涵由瑞士蘇黎世國立高工數學研究所歸國,順便取道台灣拜訪了台大校長傅斯年,傅特地叮囑道:「我在北京有些書沒運出來,你回去告訴鄧廣銘,這些書全部送給他了。」據鄧廣銘回憶說:「江先生回國後,不敢說曾去過台灣,當然也不敢說這件事。後來他私下告訴了我,我說:『我怎麼敢要他的書呢?他的書只能由科學院沒收或如何處理。』」〔28〕
傅斯年的藏書究竟如何處理,下落何處,似乎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唯能說得清楚的是胡適與傅斯年這兩枚「過河卒子」,真可謂是一對可愛的書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飄零孤島之時,還認為故國神州「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還天真地以為自己的那一堆書信文件,仍屬於私有財產,並受到國際公法和中國法律的保護,理應安然無羔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裏,書的主人雖流落天之崖、海之角,仍具有處理這批藏品的權利。豈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裏還有私有財產與什麼國際公法、人間道義的保護?真可謂書生意氣,煳塗得可以了。胡、傅兩位飽學之士可能至死都不會明白,他們那一堆書信、文件、書籍,在佔領者一方看來理應成為任意處置的囊中之物,而這些個人私產除了為打擊自己以及親朋好友、弟子門生的炮彈外,其他所謂權利與公法在新生的政權之下自是化為烏有,最多給後世史家平添一聲嘆息而已。這一現實正應了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Spenglar)所言:「我們只允許在勝利與毀滅之間進行選擇,而不允許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選擇,勝利的犧牲品是屬於勝利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