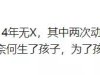不敢想像,一個大四酒吧女的私秘日記
辭掉黃老闆的家教以後,我真的不想再打零工了。可是我的一位在報社工作的表姐卻建議我去做「酒小姐」。她說,在大學裏閒着也是閒着,還不如找點事做,一來「酒小姐」收入高,二來挺能鍛煉人的。
「『酒小姐』!陪人喝酒?這不就是坐枱小姐嗎?我不干1我心想,表姐這不是把我往火坑裏推嗎?
表姐顯然知道我誤會了「酒小姐」這項工作,她急忙給我解釋:酒小姐是酒類企業為與顧客建立密切的關係,不斷研究對酒類製品的口味及購買習慣的變換,以便及時調整市場戰略,並成功地拓展市場而設立的;酒小姐是代表企業形象推銷酒的,絕不是陪人喝酒的小姐,而且,酒小姐相對要求素質較高,並不是隨便一個人就能幹得了的。表姐說她採訪過幾個公司的酒小姐,大部分是打工的大學生。
表姐給我聯繫的就是這家「中原怡人」酒吧,為境外一家葡萄酒公司推銷葡萄酒。於是每天傍晚,我會準時趕到酒吧工作。
領班小姐專門對我們這批新來的進行培訓。比如很多人想喝葡萄酒但不了解,必須記住告訴食客:經實踐證明,吃魚用白葡萄酒,吃肉用紅葡萄酒,不但可以突出菜餚的美味,還可以調節餐桌上的氣氛,餐前飲用可以開胃,餐後飲用可以助消化;白葡萄酒在氣溫攝氏4至5度時飲用為佳,紅葡萄酒在氣溫攝氏15至18度時飲用為佳等等。說穿了,飲葡萄酒事實上也代表了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比較高雅的文化。
公司給我們的保底工資是600元,但每銷一瓶可以提10元,領班小姐講,干好了,一個月掙幾千元沒問題,這就看每個人的實際表現了。她還告訴我們怎樣輕柔溫婉地與人說話,怎樣謙恭友好地向客人推銷各種各樣的洋酒,並且怎樣達到自己的目的。她在講「實際表現」、「達到目的」的時候,並沒有詳細說,但我注意到她眼底那種閃閃爍爍的東西,那種東西有一種曖昧的光澤,使人不由想抓住卻又擔心燒着自己的手。
培訓結束時,領班小姐又調教我們怎樣穿露大腿的旗袍,怎樣描眉畫眼塗口紅。我發現自己化妝後特別好看,兩隻眼睛水水的,黑得像望不到底的深潭,只有我自己知道那裏潛伏着無數的欲望。
化妝使我覺得自己從一個一身書卷氣的學生娃變成了一個風騷的女人,但我內心裏特喜歡這種風騷的感覺。平時,我走在街上也常用一種欣賞的眼光打量那些化了妝的女孩,不是為別人,是為自己。當然,我是一個潔身自好、行為檢點的女孩子。
「中原怡人」的老闆重視酒吧的品位和氛圍,那種講究讓我也覺得自己置身其中有些陶醉,有些飄飄然。
我是個適應能力很強的女孩子,只不過三天工作的時間,我已改變得像個頗有經驗的老手一樣,優雅地穿着又尖又高的高跟鞋,噴灑領班小姐送給我的CD香水,輕推着裝滿紅酒的小車走到客人身邊,態度友好地向客人推銷。
工作時間,我是謹慎小心的,因為培訓時就被告知,公司的主管隨時可能在餐館的外面,透過玻璃窗窺視着酒小姐的一舉一動,一旦有違公司的規定,公司將隨時辭退。領班小姐也將因此受到牽連,她的壓力也很大,每天虎視眈眈地盯着我們。
在一個明月朗照的日子,幾位客人來喝酒,我服務態度極好地為客人們推薦各種品牌的紅酒,其中一位客人要我每介紹一種酒都要自己先嘗試一下。我為難地看了一眼領班小姐,因為我知道公司規定「酒小姐」是不能與客人喝酒的,而且我根本沒有酒量。領班小姐只管洋酒的效益,絲毫不顧我心中的體會,向我遞了一個眼色,示意我每推薦一種紅酒都先嘗試一遍給客人看。那晚,我喝得有些微微醉了。走出飯店,有一股酸澀的滋味往胸口涌,走路有些趔趄,眼神有些迷離,有人扶我坐進車裏說送我回去。坐進去我費力睜開眼終於看清楚,司機是那位要我喝酒的客人。我把手伸進嘴裏,在車裏吐了。客人皺着眉頭走了一段,終於停下車,把我甩在了半路,我趕緊到路邊一個公用廁所洗了把臉,打出租回到了學校。
11月15日吧女的尊嚴
領班小姐曖昧地問我昨天晚上怎麼樣,我斜了她一眼沒有說話,但隨後微笑中透露出那種平靜的眼神讓她覺到了沒趣。「中原怡人」的老闆聽說了,對我說你別當酒小姐了,來我這兒當吧女算了,我道上的朋友多,可以給你撐腰,況且吧女收入也未必比酒小姐低。我微笑着說了聲謝謝,但還是穿上那件紫色超短裙。我知道吧女的小費多數確實比酒小姐的提成高,但我知道,小費里有汗水,更多的是淚水,甚至還有那種殷紅的東西。
後來那位客人又來了,還帶來一個模樣一般但打扮花哨的女孩。他一見到我,眼光里頓時流露出一種得意的神色,示威似地抓緊那女孩的手在自己颳得泛青的胡茬兒上狠勁兒蹭,一副虐待狂的樣子。為了避免他無事生非,我只好裝做看不見,內心卻為那女孩擔憂。
擔憂着的我臉上仍然始終掛着微笑。我工作時幾乎總是微笑着,微笑是女性動人的一份溫暖,但我知道微笑中也有着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峻。
一個中年客人進來,看樣子是一個機關領導。我推着小車過去,把幾種紅酒介紹給他,他很爽快地要了一瓶。我給他擰開木塞倒酒時,他說要加點兒雪碧。我輕聲解釋說喝紅酒時最好不要對雪碧飲料,因為飲料中的糖分會掩蓋酒應有的輕微苦澀味,失去了品紅酒的意義。那個人看了我一眼,皺着眉頭說就喜歡喝甜的。我只好到總台拿了一聽雪碧。端過去的時候,我看着那人說了句:「對不起,讓您久等了。」他示意我坐下。我說:「我還要照顧其他客人。」那人問了我幾句話,當聽說我是打工的大學生,而且今年就要畢業時,他用手指蘸着酒在桌子上寫道:你畢業後想留在北京嗎?我心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但我嘴上卻什麼也沒說,只微笑着。那人又寫道:我可以給你想辦法。寫完,兩眼定定地看着我。我看見了那個人眼底的得意與貪婪,立即又微笑着說了聲:「謝謝,為您服務是我的職責。」
我知道自己來自偏僻的地方,所以格外珍惜自己身上的每一處值得珍愛的東西。我並不是一個思想封建的女孩子,而是覺得不要隨便地為了得到什麼就用自己去做交換,身邊的女孩有做過3次人流的,結果如何呢?永遠的心痛!
我也最見不得一些女孩子在有錢人面前的媚態了。我親眼看見一個女孩一身媚氣,但卻讓一個手段拙劣的小騙子給耍弄了。他們來的時候要了一瓶紅酒和半桌子零食小點。那個男的頭髮亮得螞蟻上去都要拄拐棍兒,那女孩一臉幸福地將頭靠在男的身上,時不時還用自己塗滿艷紅色唇膏的嘴巴一下一下地啄那男的戴着鑽戒的手背。我就在心裏惡狠狠地罵道:賤骨頭!
款爺喝完了酒說出去用一下衛生間,誰知他這一走就真的走了。老闆扣下女孩子不讓走。女孩哭訴着說他們就是幾個小時前在迪廳認識的,跳到半場的時候,男的說請她喝飲料,就到這裏來了。老闆扣下女孩的BP機,讓她拿錢來換。我在心裏說了一句「活該1
那女孩子第二天又來了,抽出幾張紙幣來往櫃枱上一拍,說話時青紫色的嘴唇跳着幾粒白森森的牙就像一個小丑,出門時還挑釁似地故意把身子以屁股為中心扭成了大波浪。我看見,那女孩子在一輛菲亞特小車旁有意停了一下,看了看四周,才不緊不慢地鑽進車裏。
這樣的女孩子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長期以來幾乎已是一種定勢,我在學校的時候,經常憑空地這樣想一切出入酒吧的女孩。後來,我當了酒小姐,把自己排除了,把大多數的酒小姐排除了,以至對吧女也充滿了好感。印象中的酒吧和現實中的酒吧不一樣,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一個坐枱小姐曾經讓我心裏堵得慌,那是一個有着大而有神的眼、蒼白的臉、微翹的嘴巴、一頭金黃的頭髮,名叫亞珍的女孩。領班小姐曾不屑地說亞珍是一個白粉女。我的心裏曾經也不屑。後來,一個吧女姐妹說亞珍是和一個客人出台時被強迫注射的,幾天後被放回來,已有了癮。她家在農村,窮得要命,她掙錢要供兩個弟弟上學,還要給病中的父親買藥,真叫可憐。聽到事情的真相後,我心中有些同情亞珍。
幾個樣子都很斯文的小伙子來到酒吧,先向我要了幾瓶紅酒,言語間聽出他們是搞軟件設計的,剛完成一個頂目,來酒吧放鬆的。酒喝到半截他們就下台,便擁到碟房唱歌,後來又跳舞。我看到,亞珍被那個被人稱為經理的年輕人擁到懷裏。
音樂停下後,他們又坐下來喝酒,還指手畫腳點評着跳舞的幾位小姐。買單時,那個經理摸了一個褲兜,又拉開馬夾,又搜上衣口袋。經理的臉色有些漲紅,把亞珍從舞池裏拉了出來。
「什麼?我偷了你的錢?把我當小偷1亞珍蒼白的臉一下有了血色,聲音尖厲地說。
「別廢話1
「先生您清醒一下,我怎麼能偷人家的錢,何況是客人。」
「少裝蒜!錢給我,不然,我不客氣了1
「你這個人,想是沒錢結賬了。找什麼碴兒,跟我說一聲,我替你墊上。」
經理抓住亞珍的胳膊,但亞珍不動,臉又變得毫無血色。這時,總台旁圍了好幾圈人。有人提醒經理搜搜襯衣口袋。經理的手伸進襯衣口袋後,臉色驟然間也變得蒼白。
經理沖亞珍一抱拳,說了聲:「很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這時,亞珍才轉過身去,雙手捧着臉「嗚嗚」地哭出聲來。
經理抽了兩張百元鈔票遞給亞珍,亞珍怨懟地盯了經理一眼,用手一推,跑開了。
幾分鐘後,我隨幾個瘋也似的女孩衝進亞珍的房間,驚呆了:亞珍割脈了,刀片還提在手裏,人躺在床上,血流了一大片。
我白天獨自帶一大把用滿天星呵護着的康乃馨到醫院看望亞珍時,亞珍問:「被人採摘過的花也是有心的,你說是嗎?」
「當然。」我使勁兒點了點頭。我看見亞珍的淚無聲地從眼角溢出來,而我自己也覺得眼睛被一種濕濕的東西浸潤着。
而我又覺得,被浸潤着的不僅是雙眸,更有心底那柔軟、脆弱,叫做尊嚴的東西,也被一種濕濕的東西浸潤着,並在這種浸潤中益發堅硬起來。
我意識到,一個人在生活中堅守的最底線應該是那種叫尊嚴的東西,無論男人,無論女人,只要把握住尊嚴,弱者的腰也能挺起來。
責任編輯: 陳柏聖 來源:搜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07/1205/66214.html
相關新聞
 真正靠譜的人,做事必有這3個特點
真正靠譜的人,做事必有這3個特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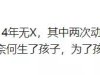













 《蔣介石日記》完整記錄西安事變全過程(未刪節版)
《蔣介石日記》完整記錄西安事變全過程(未刪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