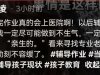楊麗娟的精神世界是個謎

母親陶菊英:「我覺得來這世上是白來了一趟,老天爺把我們這家人懲罰得夠厲害的。」
一片走向蕭條的土地一個走向封閉的家庭
3月26日,楊麗娟的父親因女兒沒能單獨見上明星劉德華,跳海自盡。
當日,劉德華在日記中寫道:你不會懂得我傷悲。
同樣,人們似乎也難以懂得楊家的傷悲。
如果一件事情無法解釋,那麼一定有你所不知道的事實存在。
父親、母親、女兒,這一家三口,各自經歷了怎樣的心理軌跡,彼此又在怎樣地影響糾纏?
這是本報記者的觀察:一個掩藏着脆弱、敏感、絕望和固執的故事。
死在香港,活在香港
楊麗娟不顧曾經答應媒體絕不再找劉德華的承諾,一到香港就在劉德華居住的別墅區挨家挨戶找劉德華。
楊麗娟已經十多天沒有換衣服了,也沒洗過澡。她脫掉黑紅色的皮鞋,坐在床沿上,低頭摳着腳趾,努力想摳掉大腳趾上殘留的紅色指甲油。「爸爸走了,我身上不應該有紅色的東西,這個指甲油是以前塗的,質量不好,老是摳不掉。」
楊麗娟十分清楚自己現在有多「紅」,每次接起電話,她都會以「我現在真的不能接受訪問」開頭,跟對方聊上半個小時———從這個記者嘴裏聽來的話,她經常會放到跟下個記者的聊天中解釋,讓每家媒體都有「獨家專訪」。
「我從不會說蘭州話。」楊麗娟的普通話里,有些上海味道。跟她對話你完全想像不到她只有初二文化水平。她是一個心思縝密的人,在媒體的包圍中,警惕地絕口不提「從前」、父女關係、母女關係、輟學生活……
「如果我們不見劉德華,爸爸是不是不會死?」楊麗娟偶爾會低聲自語,繼而會轉入對劉德華的譴責,最後沉浸在崩潰中,大喊:「爸爸爸爸,你怎麼就拋下我走了啊。我該怎麼辦啊。」
她每天都會崩潰幾次。
她並不像傳說中的有「潔癖」,雖然每次翻完黃頁,都會跑去洗手消毒,但進出她的房門還算容易,人人都來這裏坐過—— 除了她媽媽陶菊英。陶菊英住在另外一個房間,她不知道女兒住在哪個房間,女兒甚至不會跟她出現在同一輛的士上。她自我安慰說女兒很愛她,只是父親去世給她的打擊太大。
楊家母女回蘭州的幾天,一日兩餐都是媒體買的。一天記者們吃完飯,把沒吃完的打包帶上來,吃了幾口,楊麗娟發現土豆絲下面還有玉米、花生和其他幾樣食物——跟以前一盒土豆絲一盒青椒肉絲的狀態不同,知道不是單鍋小炒,她遲疑了一下,沒有表露出任何不滿,拉着記者,把盒飯拿給媽媽吃。此前她很少過問媽媽的飲食。送完飯盒,楊麗娟悄悄給別的記者打電話,讓他們帶個盒飯上來。
陶菊英一輩子都沒咽下這口氣,楊勤冀長得不好,沒有錢,又沒有地位,幫孩子見個劉德華還見得這麼窩囊,「我覺得來這世上是白來了一趟,我自己沒過好,她爸也沒過好,孩子也沒過好,老天爺把我們這家人懲罰得夠厲害的」。
3月26日,楊麗娟的父親因女兒沒能單獨見上劉德華,跳海自盡。繼去年「父親賣腎助女追星」之後,事情達到的最高潮至今仍沒有平息的跡象:歌手楊臣剛資助母女二人去香港料理父親後事;楊麗娟不顧曾經答應媒體,絕不再找劉德華的承諾,一到香港就在劉德華居住的別墅區挨家挨戶找劉德華。
他們到底想得到什麼?這個被逼問了無數遍的問題,在楊勤冀跳海之前,回答永遠如一面鐵甲:「女兒為他付出了13年的青春,他一定要見。」在楊勤冀跳海之後,回答永遠如另一面鐵甲:「這是她爸的遺願,他一定要見。」
如今這對母女的最新期待是,死活都要待在香港。
她們再也不願意回到蘭州,更不願意回到阿干鎮。
楊麗娟說:「媽媽說,我們不能回去,回去你沒辦法面對。」
阿干鎮,寂靜嶺
楊麗娟和母親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鎮,生活在這裏的人在外人看來格外「脆弱、敏感、絕望」。
「阿干鎮出楊麗娟這樣的怪人,一點也不出奇。」邴哲說。他是蘭州的一名警察,用業餘時間去阿干鎮拍攝紀錄片,已經拍了兩年。「不出奇」的原因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在外人看來格外「脆弱、敏感、絕望」。
楊麗娟和母親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鎮,父親楊勤冀在阿干鎮教書,直到1995年提前退休。
阿干鎮雖然離蘭州市區不過二十多公里,但道路崎嶇,汽車要開近一個小時。「阿干」的名字出自《爾雅。釋地》:大陵曰阿,干為水畔。阿干河從南向北穿鎮而過,河兩邊是密不透風的荒山。阿干鎮形成於北宋,之前是絲綢之路上中國內陸部分頗為重要的一站。
1950年代,阿干鎮成為蘭州工業用煤和民用燃料的主要生產基地之一。當地流傳着「先有阿干煤坑坑,後有蘭州城窩窩」的說法。「1950年代,在阿干鎮上班的人都是很驕傲的。而現在,說一個人很土,蘭州人會說『你是阿干鎮來的吧』。」張磊和他的夥伴正在招商拍攝另一部紀錄片《影像阿干鎮》。
如今的阿干鎮,建築仍以蘇式居民樓和辦公樓為主。玻璃很多已經破碎,還有大量空出來的宿舍樓,當地居民誰願意搬進去就搬進去。惟一的電影院已經改成了塑料製品加工廠,跨進院子,迎面三個斑駁的大字「觀人子」——它的前身是「觀眾您好」,這裏已經二十多年沒有放過電影了。最繁華的街道鐵冶街粗看上去家家關門閉戶,走近你就會發現,其實每扇窗戶後面都有人在打量。偶爾出現在街上的人,沒有多少表情,嘴角向下耷着。
邴哲說,阿干鎮的人大多可以預測自己的命運:男人不是因為事故在礦上傷殘亡故,就是患上這樣那樣的職業病;女人在家裏默默守候着活一天是一天的丈夫和在教學質量不怎麼高的學校里念書的孩子;小孩沉默地行走在煤塵撲面的街道上,或者被狹窄道路上奔馳的運煤車撞傷。
1990年代初,阿干鎮人口開始大量遷移,不到5年時間,阿干鎮從最初將近10萬人,減到現在2萬多人。楊志彬是《蘭州晚報》記者,前後11次去阿干鎮採訪,在他看來,阿干鎮是甘肅這類城鎮的代表:資源枯竭、千瘡百孔,百姓居無定所,背井離鄉是他們最大的願望。
「煤礦的破產和減少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嚴重地影響了阿干地區的穩定和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蘭州市委外宣辦在新華網甘肅頻道上,2005年發表的《阿干鎮》一文中這樣寫道。
楊麗娟的母親陶菊英是煤礦工人的後代。她的青春期,正是阿干鎮的輝煌期,但那些「輝煌」,從沒有降臨到她身上。像生活在鎮上的任何一個人一樣,她最熟悉兩種車:運煤車和警車——礦工們不下井的時候,喜歡喝酒,酗酒是發泄壓抑的好方法,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讓他們兵刃相見,警車常常來此抓人。
陶菊英的父親是煤礦工人,生了7個孩子,母親常年有病,全家人靠父親的工資養活。「有一天爸爸直到8點半都沒有回來,一些人衝進家裏,說爸爸出事了。」陶菊英深刻地記得那個早上,煤礦出事,父親的腿被壓斷了。父親出院後再次下井,又遇到瓦斯爆炸,這次出來,只能在地面做些雜事,一家生活更加拮据。
1976年,23歲的陶菊英在31中當臨時工,給學校刷圍牆,37歲的楊勤冀路過,打量了很久,主動幫着她幹活。
楊勤冀不是阿干鎮人,1973年,他從蘭州市裏的20中調到位於阿干鎮的31中。他祖籍河北,長在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西北師大的老師,大哥和三弟也都是教書的,但他並不比陶菊英幸福。
「他們家發生過很不好的事情。」陶菊英始終迴避這件「不好的事」:楊勤冀的弟弟親手砍死了他們的母親。
「這件事在1950年代的蘭州,還是很轟動的。」蘭州20中的同事對此還有印象。弟弟為什麼砍死母親,沒有人能說清,楊勤冀同事們比較相信的版本是,「跟楊勤冀有些關係」:楊勤冀個子不高,其貌不揚,幾次交女友未果。一天弟弟興致勃勃地把自己女友帶回家來,母親看了,試探着問:「你哥哥還沒女朋友呢,不如把這個女孩讓他?」弟弟的女友很生氣,甩了弟弟。弟弟想不通,砍死了母親,最後被鑑定為精神病———也就是外界一直流傳的「楊家精神病史」。
陶菊英從來不掩飾自己嫁給楊勤冀的不甘。「我一直都看不上他,比我老那麼多。」後來這個「大14歲」一直給陶菊英帶來很大壓力:「走出去別人都問我,這是不是你爸爸,這是不是你爺爺。」陶菊英欣賞的是她父親那樣的男人:個子很高,一米七八,走路利索,外表乾淨,做事麻利。這些楊勤冀都沒有。
這是為生計所迫的婚姻,「我爸爸說,他是個老實人,好歹有個正經工作,還有城市戶口。」
第二年生下楊麗娟,中年得子的楊勤冀非常興奮。
1981年,楊麗娟3歲,一家人跟着有城市戶口的楊勤冀住到了他父親在蘭州的家裏。陶菊英終於離開了阿干鎮;楊勤冀則每天坐通勤車往返阿干鎮和蘭州,早上搭一小時車上班,晚上搭一小時車回家。
女兒心,海底針
楊麗娟當時所說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寫好了作業,同學拿去就抄,借作業時笑臉相迎,抄完之後就不理她了。
「我不願意提阿干鎮!你們要真的想幫我,就不要再問我為什麼輟學,這跟我要見劉德華沒有任何關係!」為什麼初二輟學,是楊麗娟接受採訪時最不願意回答的問題之一。
時隔15年,楊麗娟的中學班主任齊老師(化名)很努力地回憶着楊麗娟:個子不高,比較羞澀,喜歡唱歌,但不敢上台表演;成績不錯,文科好過理科,有一次還得了第一名;有些要好的女同學;關心集體,每天很早就來打掃清潔,有同學推選她當學生幹部。
1992年夏天,初二快結束的時候,楊勤冀到學校跟齊老師說,女兒不想再讀書了。齊老師非常震驚:她從來沒覺察到楊麗娟不想上學了;她想不出楊麗娟有什麼理由輟學;輟學的事情居然是孩子的父親來告訴她的,這個父親自己也是中學老師。
齊老師多次登門規勸———她清楚地記得,當時,楊麗娟家裏,還沒有任何劉德華的海報。
當時楊勤冀喃喃自語地回答:「有什麼辦法,孩子不想讀了。」他擔保會看好讓她乖乖待在家裏。「九年制義務教育」似乎並不怎麼被看重,即使對楊勤冀來說,輟學也不是一件新鮮事,他任教的31中,每年都有學生因為貧困而輟學,媽媽陶菊英也沒上過學。
在陶菊英的回憶中,是楊麗娟央求了半年,他們才同意讓她不上學的。女兒的理由是:學費太高,一學期80元;多一點時間陪母親;自己在學校里總是被同學利用。
[next]
陶菊英說,一聽到「利用」二字,她心就軟了:「我們這家一輩子都在被人利用,我被人利用,她爸爸也被人利用。」陶菊英覺得被人利用,是鄰居看她不上班,常常把孩子甩給她帶,每個月象徵性給25元;至於楊勤冀,陶菊英總是埋怨他,比他年輕的人不是當了校長,就是當了教導主任,自己到最後只是一個「高級教師」———雖然整個31中只有一個高級教師。現在「利用」一詞還掛在母女嘴邊,她們最怕被媒體利用:採訪了一圈回去,他們漲了工資,自己還是見不上劉德華。
楊麗娟當時所說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寫好了作業,同學拿去就抄,借作業時笑臉相迎,抄完之後就不理她了。
去年有媒體找到楊麗娟的同學,帶去跟楊麗娟相見,她很不高興:「怎麼早不跟我聯繫?現在媒體報道了,都來了。」這個同學回憶說,自己結婚的時候,楊麗娟好像打過電話,當時自己忙着籌備婚事,沒怎麼跟她聊天,可能那時覺得受到了冷落。
關於輟學,還有一個說法,楊麗娟喜歡上了一個老師。「那個老師在阿干鎮中學教書,還是有老婆孩子的。」這是萬龍(化名)當年從陶菊英那裏聽來的,萬龍是陶菊英的「相好」。
幾個鄰居和楊勤冀的同事也都表示,曾經從陶菊英那裏聽到過這件事:楊勤冀帶着女兒回阿干鎮31中玩,女兒看上了父親的同事,給對方寫「情書」,對方不知如何應對,把信轉給了楊勤冀。楊勤冀也不知如何是好,把信又交回給了女兒。
「估計小女孩面子上掛不住,我不知道楊麗娟是不是因為這個不去上學了。」
萬龍說。輟學之後,楊麗娟並沒有馬上「夢到」劉德華。她每天確實是乖乖待在家裏,做兩件事情:看電視,洗頭。
偉大的母親,穿梭的妻子
「這麼多年,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的家,沒有離開過我的女兒。我可以說我是偉大的母親,偉大的妻子。」陶菊英說。
輟學兩年之後的1994年,楊家發生了兩件大事:楊勤冀和陶菊英離婚;女兒楊麗娟「夢」到劉德華。
陶菊英自己解釋,跟楊勤冀是用假離婚來多分房子。
「陶菊英跟我說,生完孩子後他們就沒過過夫妻生活。」萬龍說。
離婚之後,陶菊英跟過好幾個男人,第一個是工人,對她不錯。陶菊英經常是在工人的家住幾天,再回楊家住幾天———幫着父女倆洗衣服。
萬龍是一個退休的國家幹部,瘦但不弱,西裝筆挺,襯衣雪白,跟陶菊英在老年歌舞廳認識的,當時的陶菊英「白白胖胖,長得還算不錯」。
當過兵的老錢也是在老年歌舞廳被陶菊英看上的,他身板硬朗,說話做事乾淨、利索。他也跟楊勤冀見過,老錢曾提出跟陶菊英保持「同志般的友誼」,因為陶比他小17歲,「年齡差距太大」。
陶菊英跟萬龍糾纏了一段時間,萬龍跟原來的妻子離婚,陶菊英正式搬來跟萬龍住。還是老規矩:萬家住幾天,楊家住幾天。
兩家保持着特殊而親密的關係:陶菊英經常回家給楊家父女做飯洗衣,楊勤冀也經常帶着女兒過來萬家串門。
「陶菊英是捨不得她女兒。」萬龍說他很理解陶菊英,對她住在哪裏也不介意。
萬龍最欣賞陶菊英的勤快,也一直很心疼她:陶菊英跟第一個工人相好在一起的時候,曾經懷上過一個孩子,懷孕期間堅持回楊家洗衣服,結果流產。「楊勤冀都沒有送她去醫院,還是她的弟弟打電話讓那個工人來送去醫院的。」還有一次陶菊英遇到車禍,在家養傷,「楊勤冀和他女兒就在樓上都不下來看看她」。
「這麼多年,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的家,沒有離開過我的女兒。我可以說我是偉大的母親,偉大的妻子,沒有我這麼多年來操持家務,也就沒有她爸爸得的那麼多獎狀。」陶菊英不斷重複着這句話。
萬龍最終沒有跟陶菊英結婚:陶菊英太大手大腳,脾氣也那麼不好。
陶菊英很注重自己的儀態,「她最在意口紅,每天都要畫一個小時」。萬龍說,他帶着陶菊英逛街,「買條裙子都是800元,衣服鞋子全是名牌」。陶菊英出手慷慨,路上給乞丐錢都是2元起。蒸好饅頭,大部分給了鄰居。「她跟我在一起,花了我有好幾萬吧。」
陶菊英脾氣不好,經常打女兒,「兩母女好的時候很好,不好的時候,打得特別厲害。有一次拿着濕毛巾打女兒,把她臉上的皮都給打下來了。」萬龍對此記憶猶新。
楊家三口誰打誰的問題,鄰居和朋友說法不一:有的說,陶菊英很強勢,經常打罵父女;有的說女兒很厲害,常常打罵父母;有的說,母女對打,父親在中間勸架;也有很少的人說,楊勤冀打陶菊英。無論一家三口誰打了誰,從沒有任何人或者機構來調解、干預。
跟着父親過日子的楊麗娟,一天起床,給父親講了自己關於劉德華的「夢」,楊勤冀聽完對女兒說,他也做了一模一樣的「夢」。
沒有人在意「夢」是真是假,萬龍只是覺得,楊勤冀對女兒「順從」得太過分了。「你說可能嗎?父女同一晚做同一個夢?我要是她爸爸,就算我做了,也不會跟女兒講。」
1995年,楊勤冀從31中提前退休,這時距他正式退休還有4年。作為31中惟一的高級教師,楊勤冀拿的退休金是最高的,每月2050元——稍微有點規劃,在蘭州供3個人過小日子,本該綽綽有餘。不過後來他們總是缺錢。
「老楊跟學校說,是為了照顧他爸爸退休的,其實是為了照顧女兒。」陶菊英說。
世界越來越小,爸爸越來越親
「長這麼大,最多爸爸加班開會兩天不在家,其他時候一直都在我身邊。」楊麗娟願意談的父女關係,到此為止。
楊麗娟很少說「劉德華」,一般會用「他」代替,生氣的時候,通常使用「姓劉的」。「我只是不斷做他的夢,這麼多年已經把他當成親人了。」
那個「不約而同的夢」非常簡單:「牆壁上有一張畫,畫像上的人頭兩邊寫着:你特別走近我,你與我真情相遇。」
按照楊麗娟跟各路記者的講述,後來「劉德華夢」基本有兩個主題:緣分,純情。比較典型的有,楊麗娟在玩沙包,劉德華走過來,深沉而熟悉地看着她;劉德華在山頂遇到楊麗娟,不由分說拉着她跑到小河邊,含情脈脈地說:你都已經跑過我了,還跑什麼;楊麗娟走進一個黑房子,裏面放着一盤磁帶,上面寫着:你是我的女人。
楊麗娟一直在強化「夢」的戲劇感:一次同學給她看了一張海報,她才知道,自己一直「夢」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劉德華。
楊麗娟足不出戶,世界越來越小,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劉德華」。她越來越堅信,只要劉德華見到她,聽她說完「夢」,也會有「感應」。
楊勤冀退了休,躲避了單位對他跟妻子關係的指指點點,卻躲避不了鄰居的議論,他也開始足不出戶,陪着女兒夢劉德華。
楊勤冀對女兒有求必應,極度溺愛,任何家務都不讓她做。萬龍說:「陶菊英告訴我,楊麗娟二十多歲了,還都是爸爸給她洗澡擦身,他們一家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
「我跟其他孩子比,跟爸爸更親,一天不見都會想他。長這麼大,最多爸爸加班開會兩天不在家,其他時候一直都在我身邊。現在爸爸真的走了,我真的感覺沒有什麼依靠了。」楊麗娟願意談的父女關係,到此為止。
「只要女兒高興,他做什麼都行。」楊勤冀的舊同事老賈(化名)氣憤地回憶,有一次女兒要喝紅牛飲料,楊勤冀沒錢了,就去商店偷,第二次偷的時候被人抓住,「幸虧是國營單位,教育了一下,給放了」。
伴着「夢華之旅」,楊勤冀還開始了搬家之旅,此時他有了一項「新躲」,躲避鄰居對女兒追劉德華的嘲笑。
一個鄰居跟楊勤冀開玩笑,問他是不是還在等劉德華,就這一句話,楊勤冀馬上打110報警抓人。越是開不起這些玩笑,鄰居們議論得越厲害,楊家也就越怕跟人接觸,鄰里關係陷入了惡性循環。傳聞從陶菊英「偷人」到楊勤冀給女兒頭頂洗腳水,再到母女虐打楊勤冀,真真假假難辨真偽。
2005年,陶菊英因為一次煤氣中毒,被重物砸壞了腿,楊勤冀將陶菊英接回家裏。陶菊英這次徹底留在了這個家,而這個家早已經只有一個目標:劉德華。
「我把那些雜誌都撕了,把磁帶也給砸了。」陶菊英說自己從1996年開始,每年不斷砸磁帶、撕雜誌,這些舉動在去年 3月那輪「父親賣腎助女追星」的報道中,被解釋為:家長一開始也反對女兒追星。但時隔一年,陶菊英說自己生氣的原因,不是女兒「追星」,而是劉德華一直不回信。
總之,團圓之後,一家三口徹底擰成了一股繩———「只要見到劉德華,我們一家就能好好生活了」。
一家三口?一家四口?
「她希望跟劉德華一見鍾情,她曾經當着我的面,跟父母說,你們現在不管我,到時候我跟了劉德華,也不會管你們的。」記者陸納說。
「只要見到劉德華,我們一家就能好好生活了」就像一個魔咒。
北京電視台《每日文化播報》欄目的陸納覺得這句話有兩重完全不同的理解:見到劉德華,楊麗娟心願了了,一家三口好好過日子;見到劉德華,楊麗娟跟劉德華「美夢成真」,一家四口好好過日子。
賣腎新聞沒有達到目的,劉德華在媒體上公開回應:「要爸爸賣房賣腎來見我,這就是不忠不孝。」
正在楊家一籌莫展的時候,天上掉下了陸納。他是後來楊勤冀多封譴責信的主角之一,譴責點是:利用楊家創造收視率,甚至用假劉德華愚弄和欺騙他們。
「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台有實力,一定能幫孩子見到劉德華。」楊家對此充滿了希望。
來採訪的陸納的確答應聯繫劉德華:「我初到楊家,第一直覺是同情。」同情的內容包括貧窮和父母對孩子的苦心。因此他也「天真」地認為,也許幫楊麗娟見上劉德華,他們家就能正常地生活了。
陸納說自己也確實聯繫了劉德華的經紀公司:「一個男的,聽了之後告訴我,對這件事情,不提倡、不回應、不見面。」
陸納第二次去楊家採訪,隱隱覺得這家人不像第一次那麼「值得同情」:「楊麗娟的爸爸在家裏是從屬地位,言行都會受到母女的監視和盤問。」他把「惟一可以對話」的楊勤冀偷偷叫到賓館,委婉地告訴他,劉德華不會見他們了。
「我當時真的很想幫他們。」陸納說,他的幫忙還包括:帶去了兩個心理醫生;教楊麗娟上網、唱卡拉OK.
這種幫忙是徒勞的,楊麗娟根本不見醫生。陸納說:「楊麗娟是希望跟劉德華一見鍾情,她曾經當着我的面,跟父母說,你們現在不管我,到時候我跟了劉德華,也不會管你們的。」
第三次陸納帶來了「劉德華」———跟劉德華長得很像的吳可。吳可以模仿劉德華為職業,覺得「自己長得像劉德華,也許可以勸勸她」,《每日文化播報》跟拍。
「楊麗娟根本不像其他歌迷。」吳可說,因為他長得像劉德華,不時會遇到瘋狂的歌迷,但楊麗娟對他的長相沒有任何反應。
陸納和吳可覺得當時氣氛很融洽,而楊家對此事非常憤怒,說:「他們還拿假劉德華來欺騙我們。」吳可也沒有料到這個家庭對信息的選擇性理解。「楊麗娟根本不像其他歌迷」的評語,給楊麗娟帶來了相當大的鼓舞,她後來接受採訪時,也都用這句話來把自己跟「追星族」撇清。
2006年10月,楊勤冀一家三口進京。這次雙方都不像以前那麼「友好」,一向老實的楊勤冀大鬧電視台,要通過鏡頭公開譴責劉德華的「無恥」行為,雙方起了一些爭執。
陸納說,他被纏得沒有辦法,就私下自己掏錢買了兩張票,帶楊麗娟去了《墨攻》首映式,「坐在第一排」。陸納說自己很緊張:萬一楊麗娟出現什麼狀況,他需要負責;另一方面,他還是抱有幻想,見了劉德華,也許楊麗娟真能「迷途知返」。
北京見面之旅的結局是,北京電視台以欄目組的名義,給了楊家2000元做路費。
提起這2000元,陶菊英氣不打一處來,她當時就把楊勤冀罵了一頓:「我跟她爸說,別要他的錢,就是兩萬也別要,這是貶低人格,好像我們為他的錢似的。」
三箱寶貝,七頁遺書
是舉家奔赴幸福生活,還是心力交瘁安排後事,現在看來,無論如何這都是楊勤冀的最後一搏了。
女兒的沮喪,妻子的惱怒,加上見劉德華希望的再次破滅,讓楊勤冀徹底變了一個人。
小周(化名)說,楊勤冀從北京回到蘭州,「神情恍惚,牙也掉了,很憔悴」。
小周是楊勤冀最信任的領導的兒子,也是最後楊家三口去香港的借款人。今年春節前,楊勤冀來找他借11000元。「我沒有那麼多錢,我也知道他是拿去給女兒追星的。」此後楊勤冀又來了3次,說自己借了一圈,實在沒有辦法了。
小周不止一次勸他,不要再跟着女兒一起瘋了,楊勤冀坐在他家沙發旁的板凳上,不斷重複一句話:「我真的希望劉德華能見見娟娟,聽她把夢說了,我們一家人回來好好過日子。」
誰們「一家人」?好好過什麼「日子」?誰也不知道。至少在楊勤冀前同事老沈的妻子看來,楊勤冀已經「腦子越來越不清楚了」。「楊勤冀來找我們借錢,跟我們說,他們在香港好得很,李嘉誠的房子也讓他隨便住。」
跟大部分人一樣,老沈的妻子不想跟楊家扯上任何關係。
楊勤冀和陶菊英這幾年把能借的都借遍了,從侄兒到鄰居,從同事到領導,甚至陶菊英的幾個「相好」,都借給了數量不等的錢。楊勤冀有一個賬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記載着借錢人、借錢數目和歸還時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名人名言」:現在辦事靠,1.人際關係;2.經濟實力。
蘭州的冬天天寒地凍,近70歲的楊勤冀站在樓下等,小周不忍心,通過朋友找到一個經理,挪用了11000元———也就是傳說中的「高利貸」。
「我告訴楊老師,錢我是借給他的,不管他用來幹什麼,我都不管了,我跟他擊掌相約,一定要在蘭州再見一面。他這是跟我失約!」小周后來知道楊勤冀跳海的消息,在家裏捶胸頓足。當時他已經隱隱覺得有些不對勁。
2007年3月4日,楊勤冀來拿錢,帶來了三箱「寶貝」:戶口本、女兒小時候的照片、獎狀、學生名冊;自己的所有獎狀;上了鎖的留給女兒的東西。
楊勤冀解釋說,出遠門,放在招待所怕丟———他們已經無家可歸,住在一個便宜的招待所幾個月了。
是舉家奔赴幸福生活,還是心力交瘁安排後事,現在看來,無論如何這都是楊勤冀的最後一搏了。
3月25日,楊麗娟在劉德華歌迷會上第一次真正見到了劉德華。她沒有得到陳述「夢境」、激發「感應」、改變命運的10分鐘。
3月26日凌晨,楊勤冀留下早已寫好的7頁遺書,跳海自盡。
3月26日,劉德華受此事影響,工作處於半停滯狀態。劉德華在日記上寫道:「你不會懂得我傷悲」。其後不斷有歌迷有樣學樣,以死相逼要跟劉德華見面。
(文中化名皆為被訪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