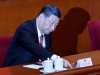抗戰八年,學生們一邊躲敵機轟炸一邊上課;難道和平年代的孩子們因為沒有城市戶口,連做學生也沒資格?——筆者
我回收使用這個標題,是因為孩子是我的至痛點。第一次用這個標題作文是兩年前,成都有個中學生墜樓,繼而引起我對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幾千個孩子的緬懷。
發生在邯鄲的孩子謀殺案,被殺死的不是一個孩子,而是四個孩子。三個孩子兇手,在兇殘殺了他們的夥伴小光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殺死了他們作為人類成員所必有的人性。他們也殺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為即便法律免除他們一死,長時間的服刑也必將重寫他們的命運。
應該說,人生來有別,人性中的善惡比例也有別,但像那三個小兇手的惡毒比值,如此之超標,全日蝕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讓我震驚、驚恐。難道真應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對打人抄家的紅衛兵的感嘆:「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來人間是討債的。」但這三個來人間討了血債命債的偷生鬼到底是為了什麼「鬼性」發作?為謀小光手機里一百來塊錢的財?或者,以欺負弱勢同伴來彰顯自己的強勢?抑或,校園裏霸凌的慣性延續到了校園外,而沒了校園的束縛霸凌失控?也許,他們僅僅是對生命——這最體現唯一性和不可複製性的存在——的無感和漠視,讓他們像撕碎一張廢紙一樣弒殺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殘害手段之殘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藥,才能使剁向小光肉體的一杴一杴從那六條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長發育的手臂中發射出去?這三個小兇手,對他們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厲鬼更殘忍?!
那麼,好好的孩子,一樣在母親溫柔的子宮裏十月胎孕,長着長着,怎麼就長成了「厲鬼」?他們的人性,是怎樣變質的?從何時病變到無救?據媒體報道,四個孩子都是留守兒童,被進城打工的父母丟在身後,由祖父母養大。與其叫「養」,不如說「放」,祖父母們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鴨,不餓着,不丟失,即責任完成。「養」字本帶「教」,我們說的學養,修養,便是這個「養」。留守兒童早已成社會隱疾,是社會在賺取的同時丟失的財富。而中國當今社會,只認賺取,不計丟失。所有可視價值的賺得,掩蓋着不可視價值的虧損。而不可視的價值,往往倍加珍貴,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寧靜平和,人之間的信賴與感恩。沒有道德,便沒有恥辱感,那麼也就失去了人之為人所必有的美感,對人在兇悍、殘忍時的醜惡無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時彰顯的極致醜惡,被認為是美——強者嘛,當然是美的。課本里魯迅的文章大概是學了,但魯迅對強、弱者的定義從來記不住,那定義是:強者向更強者抽刀,弱者則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會,是成年人社會的預科,他們以成人社會為範本來實習社會生活。那麼,這些年,我們所謂發展、富裕起來的中國成人社會都提供了怎樣的範本?無論黑貓白貓,逮着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你怎樣去達到目的,但達不到目的就提頭來見。人們只問結果,不問手段;只要目的,不論路徑;只慶祝收穫,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現以下邏輯:只要那教學樓看去光鮮雄偉,不管它多麼粗製濫造以至於地震時垮塌壓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餡兒有皮兒有折兒,不管內里的假肉是否會吃死人;只要假文憑沒人揭發,那就像真文憑一樣好使;只要那奶粉看着乳白聞着乳香,不管它是否會慢性毒殺寶寶,那就能混成優質產品,就能獲獎,就能上市,就能讓資本家身家億萬。於是,人們處處找捷徑,能偷工減料則偷工減料,羨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獲得利益最大的人士。於是一有把這種人士拉下馬當落水狗痛打的機會,一定不放過。人們只見賊吃,不見賊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視、音樂明星落馬,追打的人群擠都擠不動。1949年之後,土改使最貧窮階級正義化對地主、富農的羨慕嫉妒恨,正義化到可以將打擊對象遊街、吊打、槍斃。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時髦,敢打是小將,現在小將們老了,一輩子最提勁的經歷就是自己的拳腳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員或某國家領導身上,而那些領導和偉大人物們翻過身來,恢復了人權,也沒有向他們討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無痕對接,對錯從未釐清,就這樣發展「富裕」起來的人們,能指望孩子的預習社會中,得到什麼範本?
從報道中看,事發地屬於比較貧窮的地區。難不成被殺害的小光就因為他比那三個小兇犯富裕一百幾十塊錢,而被三人「劫富濟貧」了?那麼更貧窮的山區,更偏遠的邊疆,就該向叢林社會退化嗎?真不敢想像。城市化的建設,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勳建設者——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們受到戶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離,因為學校的教育只提供給有城市戶口的孩子們。難道不該是哪兒有孩子,哪兒就有教育嗎?抗戰八年,學生們一邊躲敵機轟炸一邊上課,一邊忍飢挨餓,一邊學習,難道和平年代的孩子們因為沒有城市戶口,就連做學生也沒資格?
其實我當年也是個留守兒童。父親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牛棚,母親被下放在另一個城市的工廠,我是外婆外公養大的。所幸外婆家規嚴明,極具常識,禮數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認為善良是為人的最高美德。雖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濟更困窘的鄰居或上門的逃荒者,她從不吝惜。外婆不識字,不能教我讀書,卻以身教給我做了做人的範本。可惜那樣的老輩人已經早已消失,現在的老輩人往往倒地都沒人敢攙扶,那麼就不難想像,當小光被殺之後,他的長輩寒夜詢問那個小首犯家長時,如何遭遇那兩個多小時的閉門羹。
從邯鄲大案發生,我們看到基本處於野蠻生長的留守兒童們的未來多麼叵測,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的未來作用是多麼叵測。難道我們沒人會略帶不祥感思忖,他們將是建設力量,還是破壞力量?他們將來對於成年人社會,是回饋,還是報復?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