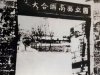一九九八年,紐約藍燈書屋負責編選世界文學經典的「現代文庫」編委會選出二十世紀最佳英語小說一百部,高居榜首的是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劃時代巨著Ulysses(《尤里西斯》),其次便是美國小說家弗‧斯各脫‧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所著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美國二十世紀小說中,《蓋茨比》自然就是首選了。《蓋茨比》篇幅不長,與《尤里西斯》相比,仿佛是個「侏儒」,膺此殊榮,自然引起評論界議論紛紛,為諸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叫屈。好在自由世界文學評論中,歷來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代文庫」的評論,並非「一花獨放」,從此確立了這一百部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定位。但是,這至少不失為一家之言,而且也並非「空穴來風」。
《蓋茨比》一九二五年四月在紐約出版。那個期間,德萊塞已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長篇巨著,同年又推出了他的代表作《美國的悲劇》。著名詩人兼文學評論家艾略特卻立即宣稱《蓋茨比》為「美國小說自亨利‧詹姆斯以來邁出的第一步」。海明威也給予極高的評價。但是,這部傑作並沒有給作者帶來他追求的名和利。直到一九四零年,他貧病交迫、溘然長逝後,《蓋茨比》才逐漸成為美國大學和中學英文課的必讀書,今日則更是家喻戶曉的美國文學經典了。
我不禁自問,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哪一部是和《蓋茨比》旗鼓相當的首選?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挑肥揀瘦,我就認定了沈從文的《邊城》。
《邊城》於一九三四年出版,篇幅不長,和同時代的長篇巨著諸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駱駝祥子》相比,也只能算個「侏儒」。這個「侏儒」卻激怒了一些搞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史的大人物。他們大張撻伐。怒斥《邊城》沒有寫階級鬥爭,「掏空了人物的階級屬性」,它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脫離現實生活。及至階級鬥爭成為中國人民靈和肉的主宰,《邊城》和它的作者也就都從中國文壇和現代中國文學史消失了。沈從文全部著作的紙型都被出版社銷毀,存書也都化作了紙漿。
無獨有偶,《了不起的蓋茨比》受我連累在「新中國」竟也有類似的命運。一九五一年夏,我從美國應聘回國到燕京大學任教,行囊中有那部小說的一個簡裝本,到校後被班上一個學生借去了。時隔不久,趕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輪到我檢討挨批時,沒料到這竟成了我「販賣腐朽美帝黃色作品,腐蝕新中國青年」的罪行。這個黑鍋我背了整整三十年。
我是在六十年前初識《邊城》和它的作者的。當時抗日烽火連天,我作為流亡學生進入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沈老師是中文系教授,我是外文系的新生,從未上過他的課。也許是緣份吧,我們終究相識了。我愛上了《邊城》,也許真的是在其中找到了「世外桃源」,可以暫時逃避痛苦的現實吧。我愛上了它的作者,他那淳樸的湖南口音仿佛和那邊城的溪流一樣清澈見底。可是,《邊城》真正進入我的人生卻是十多年以後的事,一九五八年我中了「陽謀」的暗算,遠戍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在眾多的難友之中,有一個姓鄧的青年人曾在北京師大受教於沈公,而且囚囊中還帶有幾本他的著作,我真是喜出望外。從此,在累得直不起腰來的修築導流堤工程中,在攝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鄧邊幹活邊談論沈從文的作品,特別是《邊城》,有時竟然忘了飢餓和疲勞。每逢歇兩、三周一次的「大禮拜」,難友們有的蒙頭大睡,有的打撲克,小鄧和我往往帶上他那本又破又黑的《邊城》,到小興凱湖畔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一章接一章朗讀。我終於明白了沈從文那淳樸的聲音為什麼那樣動人。此時此地,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使兩個家山萬里的囚徒時而樂而忘憂,時而「作橫海揚帆的美夢」,時而也免不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一條小溪的渡口、一隻方頭渡船、一座白色小塔、一間茅屋,這便是翠翠和爺爺的整個世界。這裏沒有「大觀園」令人眼花繚亂的榮華富貴、珠光寶氣,但有的是湘西的山光水色和大自然的兒女:翠翠在風日裏長養着,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和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
這個無父無母的孤雛唯性靈是從,她的愛情像家門口溪水一樣的純淨,不含任何世俗利害的渣滓。小說寫的不僅是翠翠對二老的鐘情,也寫了翠翠和爺爺之間相依為命、生死不渝的愛心,寫了大老和二老兄弟倆對翠翠的情愛,寫了老船夫死後楊馬兵和船總順順不顧喪子之痛對孤苦伶仃的翠翠的關愛。貫穿小說的是這個小城的小人物對人、對生活、對美的淳樸的熱愛。風雪北大荒,我更愛《邊城》了。它塑造的並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它譜寫的並不是一篇牧歌式的「鄉土文學」。它寫的不過是幾個小而又小的人物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它那充滿人性溫暖的世界和眼前掏空了人性的荒原相比,何止天壤之別!
一九三四年一月湘行途中,沈從文在給年青的妻子的一封家書里含淚寫道:我因為天氣太好了一點,故站在船後艙看了許久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中得到了許多智慧。……我心中似乎毫無什麼渣滓,透明燭照,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同船,皆那麼愛着,十分溫暖地愛着!……我看了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鷺鷥向下流緩緩划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我希望活得長一點,同時把生活完全發展到我這份工作上來。我會用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與透入些!……我覺得惆悵得很,我總像看得太深太遠,對於我自己,便成為受難者了,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
《邊城》是在同年四月十九日完成的,作者對世界、對人類的無限深情正是這部小說的靈魂。一九八零年,我作為「改正右派」重返京城任教,《邊城》和它的作者也成了「出土文物」。更令人啞然失笑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麾下的《世界文學》偏偏找到我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事隔多年,九八年秋回國,見到坊間竟有京、滬、寧三家出版社重印的我的舊譯!在沈師母家中,也見到台灣新出版的裝幀精美的《邊城》。看來偉大作品「涓涓細流」的聲音是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的。
重讀《邊城》不禁驚嘆它的總體結構典範地實現了作者的創作理想:這世界上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建築。這廟裏供奉的是「人性」。《邊城》正是這樣一座希臘小廟,與《了不起的蓋茨比》不謀而合,不過《蓋茨比》歌唱的是「美國夢」經久不衰的魅力,而《邊城》最完整地體現了作者要表現的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邊城》所寫的那種生活並不是小說家的虛構,而是確確實實存在過,後來雖然幾乎不復存在,但是我們並沒有理由唾棄這種順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邊城》用牧歌式的素材譜寫了這一美好人生形式的《田園交響樂》,永遠以它那獨特的節奏和音樂激勵着一切善良的人們對美和愛的渴求。
著名文藝理論批評家朱光潛在一九八二年為沈從文選集《鳳凰》所作的序文中說:「從文不是一個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學史上終會有他的一席地。」美國的沈從文研究專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在其所著《沈從文傳》中寫道:「總有一天會對沈從文作出公正評價:把沈從文、福樓拜、斯特恩、普魯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選自巫寧坤著《孤琴》,允晨文化出版,200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