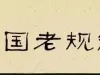對於死後世界的思考,是催生宗教的源頭。各種宗教,無一不產生於對於死後世界的超越關懷。天堂、地獄、人間,前世、今生、來世,都是宗教的觀念。(本文節編自歷史學者李開元所著《楚亡》)
在佛教傳來以前,古老的中國缺少對於死後的關懷,諸子百家關注生,迴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續,逃避生命的終結,古老的中國文化,成為一種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
因此之故,古老的中國,有哲學而沒有宗教,有天而沒有神,有追求而沒有信仰,關注興盛的延續而忽視衰亡的新生……
我讀《論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智慧的孔子,以應當致力於人事的理由,迴避了對於神事的傾注,以應當關注生的理由,迴避了對於死的追問。
以孔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在生與死之間選擇了生,在神與人之間選擇了人,創造了廣及宇宙自然、道德倫理、政治軍事的東方理性文化,卻與宗教失之交臂,留下了精神的空白。
古來中國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歷史填補,千百年來,歷史成了中國人的宗教。
我們沒有聖經而有古典;我們沒有神殿而有宗廟;我們沒有神的教諭而有歷史的教訓;我們沒有最後的審判而有歷史的裁決;我們沒有永遭懲罰的地獄,而有遺臭萬年的歷史恥辱柱;我們沒有進入天堂的永恆至福,而有寫入青史的千古留名。
孔子說:「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歷史的殿堂中接受審判獲得位置,成了中國人的來世追求。

唐代詩人陳子昂寫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面對久遠的歷史、無限的空間,詩人感嘆生命的短暫、認識的有限。
而歷史學家面對此情此景,則另有感悟,「前不見古人,歷史可以復活;後不見來者,歷史可以預測;念天地之悠悠,歷史綿延不絕;獨愴然而涕下,歷史慰藉心靈」。
如果說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歷史學家就是祭司。
司馬遷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遠古的史官,正是上觀天文、下察人事的卜師,也是溝通神與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先知。史官如實地記錄人事,虔誠地上達神明,謙虛地傾聽天聲,忠實地下達人間,如此得到神意,作為行動指南。
不真實的記錄,不忠實的傳達,無異於欺騙神明,必將遭受災難懲罰。歷史學家的秉筆直書,植根於正確預測未來的期待,來源於人類對於神明的敬畏。
多少年來,耳邊都是無神論,喧囂着人定勝天、人是萬物之靈、人是自然的主人,如今看來都是虛妄之心、狂放之言,顛倒了主客、倒置了本末。
花草一季,樹木百年,千萬年的河山,永恆的星空,人何以堪?在偉大的自然面前,人類渺小如同螻蟻蟪蛄,短暫如同雪花飄落。
也並非天人合一,而是天主人客。人與自然,不是對等,而是主客。自然是永恆的主人,人類是短暫的過客。人來做客要感恩,人來做客要知足,乾乾淨淨地來,乾乾淨淨地去,保持清潔的環境,留給後來的新客。
自然是超越人類的存在,不管是在時間的永恆,還是在空間的無限;自然是君臨人類的神明,不管是在未知的無限,還是在力量的無窮。自然是人類應當感恩的主,自然是人類應當敬畏的神。
我讀《聖經》,了解人類的原罪。我讀佛經,知曉人慾的虛妄。
我讀《周易》,明了福禍天降。我讀《老子》,體會萬物自然。
我讀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宗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心領神會,鑄為心中的模範豐碑,奉為史家的最高境界。
中國自殷周革命以來,天取代鬼神成了心靈的皈依和精神的敬畏。天是自然化的神明,天是規律化的主宰,天是歷史理性化的本源。運行的天道,主宰着宇宙萬物,主宰着歷史和人類、國家和個人的命運。
歷史學家遊走在星空和大地之間,在天道和人道之間求索,觀望星宿的移動,推演大地的分野,觀察天道的變化,預測人世的變遷。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中國文化中歷史意識的覺醒,也在殷周之際。殷滅夏,正是周滅商的鏡鑒。以水為鏡,可以知容顏;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自己看不見自己,需要藉助於鏡子;當代不能認識當代,需要藉助於歷史。
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已經參透了今藉助於古,當代藉助於歷史以自我認識的奧妙。

司馬遷生於後戰國時代,列國並立,諸子百家的流風遺韻尚存,他繼承家風遺訓,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觀望歷史變遷,體察興盛衰亡,成就一家之言。
他是孔子的繼承者,他引孔子之言自述心志:「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他著《史記》,是延續孔子整理《周易》《春秋》《詩》《書》《禮》《樂》的傳統,寓義理於歷史,五百年後自成一家。
兩千年來,《史記》堪稱中國歷史敘事的峰巔,其敘事之良美有據,思想之微露深藏,堪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諸子之別家。
司馬遷的人格風格,特立獨行而堅韌高潔,起伏曲折而獨領風騷。他體察生死有不同價值:「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相信生的價值要到死後才能確定:「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偉大的司馬遷,他將生命注入歷史,在著述立言中求得永生,歷史是他的宗教,他是歷史的祭司。
2010年7月,我送父親的骨灰到青城後山墓地與母親合葬。祭祀之餘,環視群山,仰望雲天,空谷絕響中,再次聽到父親的訓誡:「人生無常,萬物有主,慎之敬之,留名於世。」小子須臾不敢忘。
古聖先賢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經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小子無德無功,唯立言以不辱先人。
叔本華說,立言者的天空,有流星、行星和恆星。流星閃爍,轉瞬即逝;行星借光,與時並行;唯有恆星,矢志不渝地放射自身的光芒,因其高遠,需要多年才能抵達地球人間。
承先父遺訓,有幸學史的我,已將立言的價值交由時間審量。悵望無垠的星空,能留下幾絲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