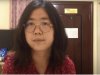張思之(截自聯經思想空間網)
(《中國:歷史與未來》編輯說明:去歲,聞名中外,在當代中國法治實踐的歷史中註定要佔有一輝煌地位的大律師張思之先生去世,作家野夫先生寫下此文以為追悼。該文先曾在網上流傳,但僅數日,便遭全網刪除,難覓痕蹤。本網站為維繫網絡時代刊載的嚴肅性,立有隻刊首發文章的規定,鑑於此特殊情況,為歷史留證,經作者授權託付,再發此文,也一併向張思之先生致敬。)
一
八年前的冬天,我在蒼山下的風聲鶴唳中,悄悄地寫《甲午飄零紀事》。那一年的初夏,因為難以釋懷的一些事,我們一群人小聚了一下。之後接踵而至的便是失蹤、監居、邊控和流亡……
遙遠的北方那時遍地腥雲冽雪,我的手機忽地悸動起來。來電顯示是張思之,已經很少有電話的我,急忙按下了接聽鍵。電話那頭一個略顯疲憊的聲音問我:你是誰啊?
我心想您打給我的,您不知道我是誰啊。以為老爺子又在跟我惡作劇,趕緊說我是野夫啊,您不記得了嗎?
老爺子依舊像辦案一樣嚴肅地審問:野夫?嗯,那我是誰啊?
我哈哈大笑,我說您不就是老爺子,張思之先生嗎?
嗯,嘿嘿,我看你沒說錯。我再考考你,我們怎麼認識的啊?
我聽他一本正經地提審,只好把十幾年來忘年之交的來龍去脈,簡單地匯報。他似乎終於驗明正身了,有點慚愧地傻笑說:我當然記得你,你還好嗎?你們這些傻小子,哎,那個哈兒,還在裏頭。你,沒事了吧?再出事,只怕沒得人撈你們喲……他開始跟我說川話,平常就喜歡用方言和我聊天。他對我們輕身躁進的責怪,仿佛一個愛恨交加的慈父,我忽然有些鼻頭酸脹。
那時我早就知道,八十八歲的他為了營救哈兒浦,最後一次披掛上陣做律師,暑熱中奔波於探監之途,終於腦梗倒下。我把我們通話的事告訴了經常照顧他的鄰居王瑛大姐,瑛姐說——剛剛痊癒,行走不便之外,就是部分失憶。他每天翻着自己的電話簿,在一個個小心翼翼地探尋,他要努力找回自己的記憶……
二
老爺子與我父親同庚,十足的長輩;我仰慕他很早,但認識他已晚,那時他已經八十開外了。記得是章詒和大姐請客,銀髮飄瀟的他堅決不肯坐上位,非要跟我和衛方這些酒徒坐一起。
他是那種一見面你就會喜歡的老頭,那把年紀了,依舊腰直背挺,隨時穿着整潔的白襯衣,緊繫着袖扣。西褲帶着燙好的褲線,皮鞋從來都是鋥亮的。多數人到這歲數,難免眼睛渾濁,他卻向來藏着精光,如一閃而過的飛鏢。他的五官刀削斧劈,非常的男人,當年一定俊朗周正,迷倒過眾生。
多數時候他都是愛笑的,且愛開玩笑,沒大沒小如一個忘情的頑童。可能是長年庭辯的積習,他的逗樂都是急智的,字正腔圓地插科打諢,能頓時打消晚輩們對他的敬畏,把你變成一見如故的哥們。當然,一旦真有嚴肅問題要跟你討論時,他又會馬上法相莊嚴。
他是那種真正見過大世面,也因為職業而涉獵過太多秘辛的老炮。他對人對事都有某種老吏斷獄的深刻和精準,但是修養、積德與操守,又使得他守口不言,很少去臧否人物。但這並不等於他已世故圓滑,他內心的定力和定見,常有刀鋒般的銳利,只是不欲輕易示人而已。他曾經看過我的判決書,老辣地笑道:你這個前警察,難道還不明白那頭熊的身份。我說我當然後來才清楚,你們那一輩老文人中,不是也多這樣的安插嗎?
一生都在辦案查卷的他,讀文章和讀人,對他都像是閱卷,認真、銳利且老道。當年渝州薄督當紅之時,強判了律師。我為素昧平生的律師叫屈,在老爺子創辦、孫國棟兄主編的《律師文摘》上,發表了卷首語《當小莊遇見坐莊》。老爺子看見後,把我叫去酒後說——文章很好,當我們律師界都需要你們作家來喊冤時,這真是我們的悲哀。不過我還想告訴你一句,他在庭上的應對和表現是欠妥的。一個律師該堅持的原則本該威武不屈,豈能用一些抖機靈的方法心存僥倖。
還有一次和我們晚輩酒聚,座上多是那一代學案的過來人。說起往事,難免也有人會自陳當年的英勇。老爺子頓杯笑曰:你們外地的我不知道,至少北京的案卷我看過不少。要說大勇擔當,唯軍濤一人。某些學領對他的無端指控,他都笑納,且謂一切皆以他人所說為據。
滿座一時無語,都知道他是那年頂風領案的當事律師,深諳許多內情。平生起人不白之冤,更不會白口誣人。至於是哪些個體的不堪,他卻又懷抱恕道而守口如瓶,不再多一分言語。
三
麥克阿瑟當年卸職演講時說——老兵永不死,只是漸隱淪。
這句話,用在老爺子身上,我看是唯一適配的。他是抗戰時真正的青年遠征軍之一,在史迪威孫立人這些名將麾下駐紮過印度。那一批萬里赴戎機的學生,要麼戰死沙場,要麼敗退台灣,留在大陸而能逃過各種運動劫難,且還成為人中龍鳳的,他幾乎是碩果僅存的標本。
因為在國軍序列服役於特務連,難免在新政作為"特嫌"而被反覆審查。又因民國學堂從軍,人格人品尚屬民國薰陶,風習所致,難免心直口快,於是被打成右派。右派二十幾年是怎麼過來的,他很少說那些往事,我只能從許多長輩的遭遇中,去想見其中的屈辱了。他是那種打不死的程咬金,百年甘苦一杯酒,回頭笑看時,都是雲淡風輕的樣子。
堂堂共和國,建政幾十年而沒有律師,可謂世界奇觀。到了1980年代要操辦皇后大案時,為了不礙中外觀感,這才想起要裝模作樣地恢復律師制度。老爺子年輕時做過法官,有幸被選中成為"兩案"的辯護律師。那時他已經五十開外了,至此才開始他功德無量的名山事業。
事實上,由兩案肇始的紅朝律師制度,從其起點就註定了中國律師的轉圜空間向來逼仄。尤其是只要事關政治的案子,公檢法都無權拍板,遑論律師。黨委定性,三家聯辦,律師輕則成為門面裝飾,重則禍及自身。這樣的潛規則,註定了老爺子後半生的征戰,多是在西西弗斯和唐吉坷德之間的徒勞。
於是一國之中,律師多數時候視所謂"謀逆大案"為畏途,敢於問津者幾稀。萬箭之下,只有老爺子皓首蒼顏,獨自在那披掛奔走。熟悉當代歷史的,我只要隨便歷數幾個名字——魏京生,鮑彤,王軍濤,高瑜,劉荻,冉雲飛,浦志強等,就知道老爺子曾經有過怎樣的大仁大勇和擔當。
他基於法理和良知,都知道這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無罪。但他又是那種深知國情的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要竭盡心力去為每個人脫罪,這就是古書所贊的那種狂者,那種肝腦相托的義人。劉荻這樣的小女生,因為網絡言論而"煽顛"系獄,他終於讓此案免於刑責而"取保候審"。多數人為此慶幸,只有他依舊認為是自己的敗績——因為這不是他主張的無罪判決,而只是免於刑事處分。他所追求的不是一人一事的營救打撈,而是要徹底廢除因言獲罪的制度性突破。
然而,這幾乎絕無可能。也因此他作為律師的半生,自認為是完全失敗的一生。他酒局上經常自嘲的一句話就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我在老爺子身上,看見的正是這樣的士之精神和追求。
四
海外茉莉花開的那一年,此國當局唯恐生變;為了殺雞嚇猴,無端動手先在各地抓捕一批刺頭。艾未未、滕彪和冉雲飛等,分別於各地下獄。雲飛系我多年兄弟,同出武陵山地巴人遺孑。我趕去蓉城探看其家屬,徵得同意,決定北上面乞張老爺子援手相救。
我那時不知此前已有沙老(流沙河先生)電請他出馬,他對冉君事跡素無了解,見我同求,遂避席向我問詢雲飛案詳情,以及為人品性等。我一一紹介,告以有司陷罪原委。我拿出五萬相托,說這是訂金,我只有這點菲儀,不足之資容我在朋友間募集。老爺子呵呵謝絕,對我說你如此願意相救的人,定是可交之友。該幫的人不在錢,不值一幫的人,給錢也不受。
數月之後,川省當局同樣以取保候審方式釋放冉兄。老爺子給我電話說,由於密偵階段,律師無緣介入,但是好奇雲飛其人,還是想去蓉城看看這小子。另外幾十年沒有回綿陽三台故地,也想順便回家看看,囑我安排一下,同行者還有門生夏霖夏楠和李瑾等青年律師。
我那時忙於生計無暇作陪,急忙懇請成都龔平兄安排全程吃住行。老爺子一行與雲飛酒聚,當夜給我電話用川方言調侃——你娃很有面子喔,我八十幾歲終於住進了總統套房啊,你讓我手足無措呢。明天我終於可以回到三台了,那是我當兵出征的地方,我竟然還能活着回去啊。
聽得出來,那夜他一定酒興甚好,與雲飛相談甚歡。古來征戰幾人回,他能如此垂老還鄉,榮歸故里,心中一定有無限悲欣。
次年,我們一群同仁設立的公和基金會,決定將"年度公和人物"的榮譽頒授給他。我邀請他再度入川,在金沙劇場的舞台上,我和耿瀟男主持儀式。掌聲喧譁中,老爺子一身正裝登台,按他一以貫之的禮數,在台角先給我們晚輩鞠躬。我們豈敢受之,急忙扶着他來到聚光燈下。我們高聲邀請唯一當得起給他頒獎的嘉賓——他的同輩神交流沙河先生登台宣讀授獎詞。兩個白髮蒼蒼的老右派,顫顫巍巍的劫後餘生,彼此執手擁抱,無言良久。
我們這個純粹來自民間江湖的榮譽,算是對他一生仗義行法的至高敬禮。老爺子在即興感言的演講中,幽默苦澀地調侃自己平生護法的征程。座無虛席的台下,隨着他抑揚頓挫的冷嘲熱嘆,不時爆發出雷動掌聲。那一刻,我仿佛重新看見他在那些往日的無數法庭上,正氣充沛大聲疾呼的身影。我甚至隱約還能聽見那些庭上的法官,氣急敗壞敲着法槌高喊"不許鼓掌"的惡聲。
那一天的花絮是,老爺子出口成章的感言之後,忽然話鋒一轉,一臉嚴肅地補白"我還要說幾句"。然後他開始指着我"大罵"——野夫,你小子還有使命,不能成天酗酒成癮,自暴自棄……他一本正經地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在台上像父親一般數落我這個滿臉尬笑的主持人,惹得聽眾似乎同仇敵愾而前仰後合。
送下老爺子之後,我接着主持說:其實,老爺子是老鴰嫌豬黑,自己不覺得。我年紀輕輕喝一點,那叫武松說的——一分酒一分氣力。您老八十幾歲,還每天貪杯,有您這樣開一代風氣,還指望我們戒酒,那只怕是想都留給您獨享啊……
五
一個政體稱為共和的國家,繼續以"革命"的方式執政,因此需要簡單快捷的方式奪人性命,用以固化專政的根基。於是早在民國之初即有的律師,卻在新政之初便廢除。從土改到文革,三十年的各種運動,人民法庭加群眾審判,紅旗開處,但見黑血塗地。無數無辜生靈,多以"反革命"之罪名填溝轉壑。
事實上,直到1976年北京變政的四年後,司法部才發出通知,宣佈恢復律師制度;但只有人大通過的《律師暫行條例》,成為中國律師的執業依據。次年,高法組建特別法庭,要對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公開審判,這才想起任命剛剛結束15年改造的張思之,出任"兩案"的辯護小組組長。
史稱"世紀審判"的這一宮廷大案,用今天的法律眼光來看,其實充滿各種荒誕。但在剛剛結束浩劫的背景下,將各種極左橫禍一併卸罪於這兩個原本衝突的所謂集團,當然一時大快人心,可以起到收拾民意的作用。1981年的首都,全世界首次窺見了中國律師張思之等前輩的身影,仿佛看到中國法治終於將要走向正軌。張思之先生被譽為"中國律師第一人",也因此案而名滿天下。
那時的律師,其實並非國際標準的"辯護士",而只是政府機構司法局下屬的法律顧問。直到1984年,司法部才正式將全國的"法律顧問處"易名為"律師事務所"。更要遲至1996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才正式頒佈。也就是說,張思之先生首次出庭兩案時,本質上只是中央委派來顯擺正義的政治犯顧問。我曾經好奇地問過他庭辯內幕,他苦笑道辯護小組隨時要傳達天庭指示,每一個辯護思路和方向,都需要向頂層匯報,反覆討論通過之後才能開庭。看似他們幫那些欽命要犯辯脫了幾宗罪名,但所有的刑罰結果卻是中常委議定的。
那麼,這意味着中國律師的第一步,開始踏入的就是一個進退失據的荊谷。沒有真正的司法獨立,在政法委的統一領導協調下捕人審案判決,律師在其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有無可能發揮一些作用?尤其是從"反革命"到"煽顛"和"顛覆",以及"尋釁滋事"或"泄密"甚至"間諜"之類謀逆大案,似乎從來沒有一例律師用無罪辯護而勝訴。
尤其是八九以來,但凡事關政治的所謂要案,偵檢乃至法庭,皆不希望嫌犯自主延聘律師,而是希望由他們指派。我當年就是這樣的當事人,也曾被他們指派的律師敷衍,對這樣的強奪人權深惡痛絕。可是即便對今日之法制現狀深知乃至絕望的那些良心犯,臨庭之際,絕大多數依舊還是希望有自己的律師,難道律師真的還能憑藉良知和專業,為覆盆之冤略有騰挪和昭雪嗎?
這才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囚徒困境",是我感同身受完整經歷過的兩難。內心否定他們的律法,卻寄望於附麗這個法律的正直律師,並妄想他們為自己脫罪。這就是代復一代的政治犯家屬,都還要奔走祈告於張思之先生的原因。殘酷地說,這也是張思之們大律師帶給我們這個時代的虛妄。他們拼盡了良知,耗盡了心血,甚而至於被驅逐出庭,被連帶入罪,最終卻基本無濟於事。
但我們——所有基於天良還在言說的人們,依舊還是需要他們——以張思之先生為代表的人權律師的存在。他們無力拯救我們於深牢大獄,卻可以閱卷見證羅網是如何織就,旁證那些不屈的頭顱是怎樣在這個時代挺立。在嚴刑苛法的無間獄土上,他們就是迅翁筆下那些"敢於撫哭叛徒的弔客",是一息尚存還在城頭摘顱的收屍人。
在這個和平盛世中,我這樣一個自說自話的寫作者,也曾膽戰心驚地預備過我的律師,以備無妄之災的隨時降臨。第一個受我委託的是浦志強,結果他卻先我陷獄,以可笑的幾宗罪處以緩刑,剝奪了他平生愛好的律師資格。還連帶他的恩師張思之先生病倒,從此再也無法奔走於義路。我趕緊委託我的第二個律師夏霖,未幾他又因為搭救郭玉閃而開罪有司,以其他的罪名重判十餘年。
這兩位都算是張思之先生的愛徒,油盡燈枯的老爺子,彼時已經困在輪椅上,面對孩兒輩的輪番陷落,再也愛莫能助了。我去探望他時,推着他到對門的瑛姐家聚餐,我為了鼓舞他而戲說——我下一個律師,只好請他們的師父您下山了。老爺子看着我兩手一攤苦笑道:百無一用是律師啊。
國中一代最牛逼的律師,一生為追求法治進步而百戰生還的老卒,白髮江湖憶舊遊時,卻是對自己平生功業的否定。這究竟是他的悲哀,還是吾土吾民的大悲大哀呢?
六
哈兒浦緩刑釋放後的那個冬天,他在終於被摘除了用於監控的定位手環之後,我趕去北方,只為互道一聲劫後重逢的珍重。我們在電話里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一起去看看老爺子吧。
我們各自拎着一點手信,相約在老爺子的樓下聚首。我先到,獨自躲在門外抽煙,寒風卷着我吐納的煙氣,迅疾消散在那僻靜的街巷。一會哈兒來了,依舊高大粗壯如半扇被風颳來的老門。我們簡單地寒暄,好像並未經歷前年玄幻驚險的生離死別。然後他說他自由後,立馬就來看望了老爺子。我知道他是知恩的人,從此將以兒子事父的孝純,來報答老爺子的深情。
按響門禁之後,保姆下樓來帶我們上去。一向健步的老爺子,蜷縮在客廳正中的圈椅上,下半身覆蓋着一床薄被。他明顯蒼老了,滿頭霜雪如窗外的瓦楞;笑容卻還是明淨的,還是帶着他那慣有的狡黠和調皮。他笑說老夫就不站起來行禮了吧。哈兒跟他百無禁忌地調侃——您有本事站起來給我看一個。
於是我們就大笑,嘻皮涎臉一點正經都沒有的樣子。他轉頭問我:你那瓶酒,還幫我存着沒有?我急忙點頭說當然當然,一定要存到那一天,我們幾爺子一起暢飲的。那是幾年前的一次酒局,我給他帶去一瓶二十年的茅台。結果他饞得當場就要開喝,被章詒和大姐強行攔下。大姐怕他高齡濫飲,非要我拿回去,說一定要等到河清海晏的那一天,再一起大醉。
老爺子是真的愛酒之人,尤其是陳年老茅,過眼而不得痛飲,絕對是如鯁在喉的念念不忘。浦哈兒告訴我,就在他這次最後入院的前一個月,他的癌症已經讓他艱於飲食。哈兒去看他,老爺子非要堅持喝一杯,絕不吃飯。哈兒和瑛姐發氣說:你要還想活着等那一場大酒,那就還是喝湯吃點軟食。老爺子略一沉思,還是採納了他們的建議——他已經95歲了,內心深處卻還在幻想雲開日出啊。
那天我和哈兒走的時候,幫老爺子紮好被角。空空蕩蕩的客廳,留下他和圈椅融為一體的孤獨身影。他惜別的眼神被一聲門響所阻斷,我多少有些預感,這可能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了。我沒想到在那之後,他又堅持活過了幾年,但是終於還是沒有活到我們預約的開酒狂慶的那一天。
而我獨自遠去了他鄉,也在等着歸去之日,帶着那瓶更加陳烈的酒,去酹祭在他的墓前。此刻,我只能萬里之遙,寄一副輓聯,博他九霄雲外的一笑——
法治衛士,定有千秋書戰史;
律辯宗師,竟無一案是贏家。
2022年7月11日於清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