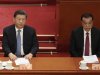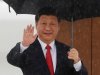|
剖析國家,透視權力
――試論中國政治研究在中國的創建和發展
吳國光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
一、大國奇觀:中國政治研究在中國的缺位
二、思考國家與權力:建設中文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學科
三、規範和發展自身:中國政治研究的學科建設
【注釋】
一、大國奇觀:中國政治研究在中國的缺位 
中國是一個政治大國,但卻是一個沒有政治學的國家;中國是一個不斷「突出政治」、「講政治」的國度,但卻是一個沒有「中國政治研究」這門學問的國家。經常被民族主義劫持的當代中國政治本身,以及本質上依附政治的當代中國知識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戀的癖好,但對於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對於中國政治的科學研究卻最不感興趣。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大國奇觀:政治學研究在中國極度落後,關於中國政治的學術研究在中國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說,在學界的努力下,在國際學術潮流的激盪下,近年來,中國的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經稍有起色;關於中國政治的學術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說是一片空白了。但是,這些仍然零散和初級的研究的出現,尚未從根本上改變前述基本狀況。而且,開始在中國初呈熱鬧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屬於政治科學的公共行政、國際政治、對外關係等分支;對比之下,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淺陋與落後,就顯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是,一個大國(甚至不那麼大的國家)的政治學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國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主要基地所發展起來的當代政治科學,在美國所呈現的基本分支學科劃分,不外乎政治理論、美國政治、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四大領域。其中,美國政治這一領域,相較於其他幾個領域,無論就學術的發展水準而言,還是就實際的社會影響而言,往往獨領風騷。當然,這一領域,在其他的國度,就為那一國的本國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說,在英國,那就是英國政治;在加拿大,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亞,那就是澳大利亞政治。[1]同樣,在那些國度,本國政治的研究往往也是政治科學最為重要的分支和最為熱門的領域。在大學裏,研究本國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學系人數最多的一組;講授本國政治及其研究的課程,總是政治學系名列第一的基礎課程和必修課程。一所大學,但凡有政治學系(事實上,在比如美國這樣的國家,所有大學都有政治學系,雖然一些規模較小的大學會把政治學和社會學、歷史或其他學科合為一系),哪怕規模極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學專家缺位,但卻絕對不會沒有研究本國政治的教授。極而言之,如果某個美國(或者英國、加拿大)大學的政治系,規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懷疑的是,這位教授的專業,一定是美國(或英國、加拿大)政治研究。
同樣號稱大國,但卻唯獨中國不然。中國的大學,在很長的時間裏,根本不開設「中國政治」這樣一門課。當然,「政治課」一直是有的,曾經包括「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等,近年還出現了一些比如「毛概」、「毛鄧三」之類的課程。[2]在這樣的教育氛圍中成長,於是,許多國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以為「政治」就是這些東西。於是,在了解到美英大學有政治系的時候,他們常常有兩種訝異。第一,他們訝異西方國家居然也在大學中教授「政治」;第二,他們訝異「政治」竟然還有什麼「學」。總而言之,他們把「政治」理解為中國大學裏在「政治課」名目下宣講的那一套東西了。
的確,政治無學,是中國的長期現實;對於中國政治的科學研究,為對於政治領導人講話和政府文件的學習所取代,這也是中國的長期現實。然而,與其說這是一種合理的現實,毋寧說是可悲的中國現實。形成這種現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無疑在於政治專制。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還不是一般的政治專制。比如說,不是中國古代皇朝那種類型的政治專制,也不是大多數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那類政治專制,而是具有全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又做「極權主義」)特徵(在毛的時代)或具有其殘餘特徵(在所謂改革時代)的政治專制。[3]這種全權主義專制政治的一大特點,在於其總是有一套高度發展的官方意識形態,不僅解釋政治,甚至解釋整個宇宙。而且,政治權威與意識形態權威,如同在中古時代的政教合一制度下,總是合一的。因此,政治領導人的論述,就是一切科學的最高指針,甚至包括自然科學,更不要說政治科學,如果政治科學居然存在的話。事實上,除了這些論述,也並不需要對於政治有另外的研究。政治就是政治學,政治領導人就是政治學家——這也等於說,除了政治,並不存在政治學;除了政治領導人,並不存在政治學家。
在其他形態的政治專制主義下,一般不是這種狀況。比如說,就中國傳統而言,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思想大家、文章大家、或者說公共知識分子,都是首先乃至主要研究中國的本國政治。孟子、賈誼、韓愈、王夫之,直到康有為、黃遵憲、梁啓超,都是這樣的例子。就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在軍人專政的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則生發出了當代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學派,即「依賴發展學派」(Dependent Development, 或Dependencia),那也是立足拉丁美洲國家本身的政治研究而形成的。[4]這就是說,一般的政治專制,雖然並不保障科學研究特別是政治研究的發展和繁榮,但也並不一定排斥和扼殺科學研究,包括政治科學的研究。只有那種凌駕於一切之上、當然也凌駕於科學之上的全權主義專制政治,具有濃重意識形態色彩的專制政治,政治權力和思想權力合為一體的專制政治,最具有毀滅一切科學的殘暴性質。而在這一切科學之中,首遭毀滅、也最為忌諱的學科,首先就是關於這種政治本身的學術研究。
因此,這就不難理解,實行所謂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已經深深捲入全球化的中國,不斷鼓吹提高創新能力、尋求科學技術領先地位的中國,幾乎在任何方面(包括在曾經深深忌諱的行政、外交乃至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已經或多或少地與世界接軌的中國,卻偏偏在一個方面成為世界奇觀,那就是在中國本土基本上不能進行有關中國政治的科學研究和發表相關成果。不僅中國人自己不能進行這樣的研究,外國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基本上不能在中國公佈。中國是世界上翻譯、出版外文書籍最多的國家之一,最近30年來更是大量翻譯、出版了有關中國文化、歷史等的西方研究成果,但卻幾乎從來不翻譯出版國外、特別是西方有關中國政治研究的著作。以至於,在不少學養堪稱深厚的中國學者那裏,一提起西方的中國研究,就是文化、思想、歷史方面的研究,對於如今已經佔據西方的中國研究的重頭的中國政治研究卻甚為隔膜。對於中國人來說,整個世界上,也像中國一樣,好像根本不存在中國政治研究這樣一種東西。
不是沒有替代品。在一個充斥假冒偽劣的國度,科學研究一樣有假冒偽劣。如前所述,「政治學習」好像就是政治研究了——英文也是「political studies」,更增加了魚目混珠的可能。可是,對於稍有科學常識的人來說,判斷科學研究和非科學的東西的標準,其實非常簡單明了:科學研究的所有結論都是可以討論、可以批評、可以爭辯、可以證偽的;如果不允許討論,不允許批評,不允許爭辯,「真理」已經在手,「學習」就是「洗腦」的話,那肯定不是研究,不是科學。「政治學習」是不是政治研究,應該很明白了;中國大學(包括中學)的政治課是不是政治科學的課程,也應該很明白了。
中國的政治,可以討論嗎?可以批評嗎?可以爭辯嗎?這種起碼的科學態度、也是起碼的文明準則,在中國本土,顯然還不能廣泛地應用到有關國家、政府和政治權力的思考之中。既然不能,那就很難有什麼關於中國政治的科學研究。不管是不是講什麼「科學發展觀」,不管「政治文明」的說辭多麼動聽,不能研究和爭論的東西,那叫什麼「科學」?不能研究和討論的政治,那叫什麼「文明的政治」?
得不到科學研究的東西,也就很難得到改進和提高。誰都明白政治在中國的重要性。可是,偏偏這樣一個重要的領域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不能成為批判性思考的對象,則中國人知識和思維的提高就遇到嚴重的障礙,中國政治的發展和進步也缺少相應科學的知識和思維支持。從認識論的角度說,中國政治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的重要性,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就政治科學作為一門學科而言,不研究中國政治,對於人類政治現象的認識就缺少了極大、極重要、極獨特的一塊;就中國研究而言,如果不了解中國政治,那等於沒有摸到了解中國的門徑。[5]從實踐論的角度說,如果中華民族要實現現代化,要構建所謂政治文明,要提高所謂科學研究水準,一個不可迴避的重大科學任務,就是要在中國本土開創、發展和繁榮政治科學的研究,特別是關於中國政治本身的科學研究。在目前中國本土的言論控制仍然非常不利於這種研究的狀況下,退一步說,也要堅持在大陸中國之外的邊緣漢語世界進行這樣的努力。由邊緣而中心,由起步而發展,以期有關中國政治的科學研究的漢語成果,能和包括英語等其他語種的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成果一起,逐漸影響中國本土,促生本土的這類科學研究,直至使漢語成為中國政治研究的第一語言,使中國本土成為漢語世界乃至全世界有關中國政治的科學研究的中心。
二、思考國家與權力:建設中文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學科 
要在大陸中國之外的邊緣漢語世界進行中國政治研究,有種種困難,談何容易。然而,基地設在美國普林斯頓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十幾年來,蓽路藍縷,開闢草萊,一直都在堅持不懈地做這樣的努力。當然,這是一本綜合性的社會、人文科學刊物,並不單單發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如前所述,政治研究在中國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而在漢語世界裏,要發表有關中國政治研究的成果又相當困難。《當代中國研究》因此貢獻了很大的篇幅來發表這樣的成果,經年累月也就積累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刊物不在中國大陸出版,因此沒有政治上的禁忌;但是,作者卻絕大多數具備中國大陸生活的背景。特別是近年來在程曉農主編的努力下,更大量地發表直接來自那些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學者的研究成果。
應《當代中國研究》和程曉農主編之邀,在共同編選這些文章成集的時候,我感到,這類文章使《當代中國研究》這份刊物具備了一個獨特的優勢,溝通了中國本土與外部世界之間使用漢語研究中國政治的努力,為開創漢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這些文章的啟發下,這裏,不惴譾陋,我也打算就如何建設和發展漢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從兩個方面提出一些粗略的想法。一個方面是有關研究內容的,即中國政治研究作為政治科學,應該注重研究什麼東西;另一個方面則是相關的研究條件的問題,即要在中文世界建設中國政治研究這門學科,需要着重那些要素的發展。這些想法無疑都是很有局限、乃至不乏偏見的;這裏大膽提出來,用意更多地在於引發批評和討論。
在這一節,我們先來展開有關研究內容的方面。
首先,我感到要創建和發展漢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我們必須特別注重有關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政治變遷的研究。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這可以使政治研究具有歷史的、動態的優勢。我們知道,美國式的政治學往往十分當代化;但是這並不表示政治研究可以排除歷史的縱深。美國政治研究本身,就十分關注美國的政治發展,包括歷史的發展。英國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英國政治學的傳統就是以歷史為主流的政治研究。[6]在一般(而非專業)的英文書店裏,政治研究也往往都是放在「歷史」欄中的。而從可行性的角度來說,則可以發揮中國傳統治學以史為主的優勢,藉助源遠流長、積累深厚、近年正處在復興之中的中國歷史研究來為中國政治研究注入力量。我們看到,近年來,《當代中國研究》在這方面很下功夫,大量刊發了研究當代中國歷史的文章,已經並且準備出版多種專輯,也多次提出要「解構虛假的歷史」、「還原被扭曲的集體記憶」、「突破意識形態專政建構的集體記憶」。[7]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書沒有收錄這方面的文章。不過,這不等於說,這樣的研究在中國政治研究中不重要。恰恰相反,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從政治研究的角度着眼,重點必須放在當代史。換句話說,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竊以為應以40年代中後期為開端。研究中,間或必須追溯到更早的歷史時期。但是此前的時段,包括那些時段上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應該主要屬於歷史研究。粗略地講,中國政治研究所要注重的當代史,應該包括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制度的起源與肇始、毛時代的政治,以及毛後時代的政治這樣幾個大的階段。當然,這些階段的劃分,本身就是中國政治研究中必須展開探討和爭辯的課題。比如說,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時段,究竟是3年,還是10年,不同學者的看法,就包含了對於那一階段中國政治的不同觀點。與此相類似,對於所謂「改革時代」,也可以有不同的時段劃分。本人在2004年提出的「兩個改革」的論斷,和更早些時候認為中國的改革時代已經結束的論斷[8],也引起了批評和討論[9]。有這種討論,科學研究才能繁榮。目前看,似乎更多地還是歷史學家們在進行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往往紮實、深厚,對中國政治研究無疑是寶貴的智慧財產。但是這不等於說,就不需要從政治學的角度展開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了。恰恰相反,政治學家應該一方面向歷史學家學習,一方面從政治學的學科特點和學科要求出發,來展開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
政治學的學科特點和學科要求的一個中心點,就是關注權力,特別是關注國家權力,研究權力的構成、運作和特點。英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從一開始就具備這一特點,在50年代曾經就此出版了大量專著。隨着研究對象本身在不斷變化及發展,也隨着學術研究的深入和展開,這種關注在不斷調整角度,拓寬視野,開掘縱深,並形成新的概念和理解,但這種關注並沒有消失。在這個意義上,整個英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就是聚焦權力運作而追蹤中國政治發展所展開的智慧產品。不過,英語世界這樣的研究,並不能代替漢語世界的相關研究。一方面,這裏有研究議程的不同。比如說,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議程,體現美國學者對於中國的關注角度;而中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議程,應該體現對於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的觀照和反省。另一方面,這裏也有資訊、方法等的不同。中國當代政治基本上是以封閉為特點的政治,從外面進行觀照尤其不易,加上語言、文化、時間、財力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國外的研究對於中國政治其實有太多的忽略、曲解和誤讀。中國的研究者,身在其中,有其展開研究的優勢。當然,這本身也可以是劣勢。「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說的都是這樣的劣勢。以為身在其中就必定更明白,這本身就是一種認識誤區。只有通過反觀自身的科學研究,才有可能克服這樣的誤區和劣勢,發揮身在其中的信息優勢。因此,中國政治研究對於中國人來說才十分必要。
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刊發的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當中,不少是着眼權力及其運作所展開的。選取這些文章的精華並結集於此,就構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從這些文章中,我們看到,植根於中國本土、以獨立的學術觀點來分析權力運作的中國政治研究已經開始萌芽。他們有的涉及中國政治運作的一些基本特點,有的分析某種政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如政黨、軍隊或立法體系等)及其在中國的運作特性,有的深入到地方和鄉村政治層面,有的聚焦於比如運動、會議、英模塑造等深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活動、儀式和方法。還有更多的類似文章,也很精彩,但篇幅所限,編選集子的時候只能割愛。這些文章絕大多數出自目前身在中國大陸的學者之手,一般都具有材料紮實、細緻、分析深入等優點,並且往往具有深切和明確的現實關懷,既具備學術價值,也蘊含現實意義。這些文章都試圖遵循國際學術界相通的學術規範,並在不同程度上為在中文世界實踐和發展這些規範提供了範本。有些文章的質量,比起國際學術界領先的有關中國研究的英文學術刊物上刊發的相類文章,可說毫不遜色。
當然,不足也是明顯的。在我看來,有這樣幾個方面,似乎特別值得注意。首先是對於國際學術界有關中國政治研究的已有成果掌握不夠,因此起點相對較低。比如說,關於中國政治中所謂「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研究,在英文學術世界頗有歷史和成果[10],應該會對本集所收的相關研究有所助益,但實際上卻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如前所述,這有其客觀的原因,因為中文世界基本上不介紹外部世界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成果,而身在中國大陸也往往缺少機會直接閱讀其他語言的相關著作。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中國在全球化中的捲入是畸形的;單就知識、精神、文化而言,中國在比如娛樂資訊方面無疑已經和世界接軌,但在嚴肅的思考層面則似乎仍然相當與世隔絕,在有關中國及其命運本身的思考方面尤其如此。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那些正面但往往膚淺的評論,可能會為中國輿論所熱炒;認真、負責、平實、並具備「批判性思考」(即critical thinking--順便提一句,也許是廢話:這種「批判性思考」是國際學術界、至少是社會人文學界的基本思維方式)的研究成果, 則不僅向隅,而且往往被視為「反華」之作。[11]《當代中國研究》的作者們已經用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他們是在嚴肅地思考,認真地研究,在上述畸形現象下難能可貴地保持了學者的品格和追求。我所說的,不是他們的責任,而是他們的無奈。據我所知,在同是中文世界的香港和台灣,雖然具有出版自由,但也極少翻譯出版嚴肅的學術著作(倒是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做得更好,除了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著作之外)。一方面,這裏有市場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據我了解,他們的大學相關課程往往直接使用英文著作作為閱讀材料。[12]另外,儘管中國高校教師的收入已經普遍大幅度增長,但是,要他們個人購買外國出版的學術著作,恐怕也還力有未逮。至於個人閱讀能力的限制,也不能不說還是一個問題,雖然中國學者的外文水平、首先是英文水平,這些年有明顯的、普遍的提高。可以設想,身在中國大陸的學者,如果能夠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關於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術成果,對此進行批判的「接軌」,憑藉他們的其他優勢,則可以從較高的起點上發展漢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那會做出何等的優秀成果。
第二,則是研究視野還不夠開闊、深入、細緻。當然,我的了解有限;單憑選入本書的文章也並不能看到中文世界中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全貌。[13]但是,即使我的看法是片面的、錯誤的,說出來供大家批評,應該對學科建設僅有好處而無壞處。就現在的了解來看,一些十分重要的論題,在中文世界裏正在開始浮現的中國政治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視。比如說,官僚體系(bureaucracy)在國家體系和政治運作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關於官僚的研究在政治學當中也可以說源遠流長;而古代中國則常常被認為是完備官僚制度的一個典範,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那麼,在中國一黨專制的現制度下,中國官僚扮演什麼腳色、具備什麼特點呢?[14]在以所謂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為特點的毛後改革時代當中,按照韋伯(Max Weber)的看法,應該是與理性化密切相關的官僚體系有沒有發生變化?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如何解釋這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又對國家體系、政治權力運作產生了什麼影響?更具體一些,也可以追問,在幹部選拔的機制和標準、幹部的教育和構成、幹部的待遇和出路等等都出現了重大變化的改革年代,這些東西對於官僚體系的變化有沒有影響呢?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類似的題目很多。小的課題,就更多了,但學術的價值一樣可以很大。英文世界裏可以做,但在中文世界裏做起來可以有一定的優勢,也可以有更大的意義。比如說,北京奧運會前夕,有報道說,那種被稱為「小腳偵緝隊」的胡同大媽們又活躍起來,到處盤查陌生人,成為北京維持所謂「平安奧運」的一種手段。[15]這種「小腳偵緝隊」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一直就沒有見到有專門的研究;在目前這樣一個號稱全球化、市場化、實行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重現並活躍,就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了。在我看來,這個課題可以從國家對社會控制的角度探討,也可以深入到基層「治理」與「社區」政治文化的層面去;其中豐富的「中國特色」,經過比較政治和政治理論的稜鏡,不是不可能分析出某些深具理論意涵的結論。類似這樣的現象,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是很多的,都應該進入政治學研究的視野。
相關研究的第三個不足,是這些研究成果就「概念化」、理論化而言,普遍還相當薄弱。這裏的所謂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指從事實中抽象出概念,與目前中文語境中一般所使用的具有貶義的「概念化」是非常不同的。只有通過這樣的概念化,學術研究才不是就事論事,而是以小觀大,從具體探知一般,因此成其為與敘事、描寫或對策分析等有根本區別的所謂學術研究。[16]在英文世界裏,中國政治研究的理論水平,與政治科學的其他分支相比而言也好,與同屬比較政治學科的關於其他地區的研究相比也好,也都是相當低的。僅就後一種相比來說,關於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就曾經向主流政治學貢獻了諸如「新權威主義」(New Autho -ritarianism)、[17]「依賴發展」等風行一時的概念和理論;關於農民的研究,則僅從東南亞地區的相關研究中,就發展出了對立的兩種學說,即「理性農民論」(Rational Peasants)和「道德經濟學」(The Moral Economy),都對比較政治研究形成了重大貢獻。[18]中國是一個農民大國,但關於中國農民的研究並沒有形成什麼有影響的理論。英文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這種相對落後的理論水平,原因是什麼,沒有見到有說服力的分析;但是,我相信,這決不意味着中國政治的研究就不能為人類對於一般政治現象的理解提供普遍的助益,也不意味着生活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們不可能為主流政治學作出理論上的貢獻。如前所說,用西班牙文寫作的一些拉丁美洲學者,其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在被翻譯為英文出版之後,曾經在英文學術世界開山立派,極有影響。我相信,中國學者用中文出版的研究中國政治的著作,在某一天,也可以達到乃至超過這樣的水準。
上面提出的這些問題,也許都未免苛求。不過,在我看來,學術的進步,基本上就是一種「苛求」的過程:已有的研究、概念、理論,本來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學者們不滿足,未免苛求,於是有進一步的研究,有新的發現和理論。說到這裏,也許應該指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界近年儘管有長足進步,但是那種「二分法思維」和非學術的治學方法似乎仍然相當流行。所謂「二分法思維」,我這裏主要不是指政治觀點上的非黑即白而言,而是就認識論的真理與謬誤和學術探討上的批判與繼承而言。在這種思維下,不是全部有道理的說法,就被認為完全沒有道理;有一些道理的觀點,可以被認為怎樣都是有道理的。其實,不是全部有道理的東西,就等於有一些道理;如果說有真理,它似乎總是以「部分」面目示人。只有確認這樣的認識論前提,不斷繼承而又不斷發展的科學研究才成其為可能。[19]本書所選關於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其觀點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但顯然也不是關於那一議題的全部「真理」。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即國家和權力,是不可能壟斷全部「真理」的;關於它們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學本身,則必須在探索、辯論、批判和繼承之中不斷積累對於「真理」的認知和發現,才有可能幫助人們增加對於中國政治的了解和理解。
三、規範和發展自身:中國政治研究的學科建設 
至於所謂「非學術的治學方法」,屬於比較技術層面的問題,但是並非不重要。因為它關係到反思和剖析國家、權力等重大問題的中國政治研究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學科如何規範和發展自己——這也是本文這一部分試圖討論的主題。在英語世界,中國政治的研究遵循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規範,這方面沒有什麼問題;在中文世界,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由於1949年之後長期以來的反社會科學的那種心態,致使社會科學缺少相應的科學規範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以至於在實行改革開放30年之後的今天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走上軌道。也許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在這方面還稍好一些,中國政治的研究因為其整體的落後而在科學規範方面尤其不甚令人滿意。事實上,這樣兩個方面,即規範自身和學科發展,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不可能截然分開的。換句話說,唯有遵循學術規範,才能求得學術發展;正是在研究的深入之中,研究的規範才建立和普及開來。因此,在這一節當中,我們的討論會超越純粹的技術規範,涉及到中國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學科建設問題。
首先從技術層面要建立基本的學術規範這個問題談起。常常有人誤解,認為文章中加幾個注釋,就算遵循學術規範了。這個理解當然失之淺薄,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注釋的意義不可低估。[20]注釋不僅使得論說言之有據,持之有故,而且保證了知識發展的繼承性——如前所述,只有在繼承和發展之中,知識才能積累和進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妨說,忽略研究著作的注釋,也就意味着不重視知識的積累。目前這一代正當盛年的中國學者(包括筆者),在毛的時代成長,讀「兩報一刊」文章長大,缺少社會科學的基本訓練;及壯,先後遭遇改革年代的激情和商品年代的庸俗,非專業的社會承認似乎總是壓倒專業標準。至今還不少見這樣的所謂學者,在引用別人觀點的時候,不習慣註明出處;在闡述自己觀點的時候,則好像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有人涉及此一議題。所幸,比較年輕一代的學者,普遍有着更好的學術訓練,也比較自覺地遵循學術規範,這從本書所編選的文章可以看得出來。這些文章,基本上都能中規中矩地按照學術規範展示論點、提供論據、形成結論,為中文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創建了初步的技術規範。
要推廣這樣的規範,則還需要學界的進一步努力。而具有專業精神乃至專業水準的刊物,是匯集這種努力的基本平台。在這方面,程曉農主編所主持的《當代中國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的刊物,在中國內地也開始出現,雖然由於政治環境的限制,他們的專業努力更多地似乎體現在並非中國政治研究的其他有關中國研究的領域。在這方面,英文世界有一系列多年行之有效(當然也有其弊)的制度和做法,包括匿名評審制度、研究基金制度等等,值得我們在中文世界發展中國政治研究的時候借鑑。值得高興的是,《當代中國研究》在這些方面都做出了努力並有長足進步。具有專業水準的書評,也是促進學科交流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在這方面中文世界也應該努力。[21]
當然,類似學術規範、刊物出版等很多這樣的問題,在中文世界,特別是中國大陸,並不單是中國政治的研究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的問題,也不光是政治科學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科學所面臨的問題。但是,中國政治研究,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大國,可以起帶頭和示範作用。對中國人來說,不管此人是什麼階層、職業,中國政治無疑都是一個重要的領域;這無疑也是一個比較容易牽動情感的領域。如果國人對於自己的政治的研究上了科學的軌道,則整個民族的思維素質和水準,可望有比較實質和重要的改進與提高。換句話說,對政治這樣一個容易牽扯自身利益、容易激發諸種情感、人人似乎都有發言權的題目,能夠進行比較合乎科學規範的討論,則對於其他題目的科學認知也就應該比較具有至少基本態度上的科學性了。而科學規範的建設,將會幫助實現這一目的。反過來,由於政治因素的介入,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實現科學化、規範化,也有更多的困難。就此而言,我認為,了解並借鑑外部世界(比如英語世界)的相關做法,對於開創和發展漢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這裏,我們不妨管中窺豹,圍繞四個問題,從借鑑的目的着眼,由學科建設和基本方法的角度着手,談幾點對於英語世界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的看法。
首先一個問題是,誰在進行並主導英語世界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答案是,從事研究者主要是不依附於任何政治權力機關的大學教授。當然,在政策研究界或者說「智庫」機構,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人員。不過,這些人數量比較少,其中多數人主要是進行政策研究,而不是學術研究。一般來說,政策研究成果不太得到學界重視。[22]這種以大學為中心的政治科學研究,與那種由政黨或政府的政策研究機關主導相關研究的制度設置,有根本上的區別;而區別的要點,在於前一類研究者(大學教授)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學術自由。源於13世紀的意大利和法國、如今主導人類高等教育的西方大學制度[23],本身提供了包括制度保障在內的各種條件,加上學者們所作出的鬥爭與努力,使得學者得以具備這種獨立(首先是獨立於政府、政黨等政治力量,但也同時獨立於其他社會力量)、自由的超然地位,可以進行探索、辯論和創新。中國雖然已經引進大學制度約一百年,但由於多種原因,特別是由於中共政治制度的原因,迄今並未在精神和制度上得到西方大學理念的精髓,在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此。這一點,近年有識之士多有指出並討論。[24]從本文的角度來看,可以說,什麼時候中國本土的政治研究是由具備獨立、自由精神的大學所主導,而不是政黨或政府的研究機構所主導,什麼時候中國本土的政治研究才有可能具有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制度特徵。
其次,為什麼進行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答案是,上述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首先具有純粹學術的意義,而不是為了服務政府決策或經濟利益。就我的了解,改革開放30年來,在中國形成了一種對國外(比如說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嚴重誤解,其中包括對於中國政治研究的誤解,那就是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與政府決策密切關聯,常常是為政府決策服務的。1980年代,一些具有濃重改革色彩、學政兩棲的中國知識分子,鼓吹「軟科學」和所謂「決策科學化」,即強調科學研究與政府決策之間的密切結合;19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進一步靠攏政府,追求仕途,於是藉助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所謂「旋轉門」現象的介紹,強調學者與官員之間的身份互通和互換。從政治傾向上看,上述兩種現象有很大差別,前者試圖改革中國封閉、愚昧的官僚決策體系,後者則主要是尋求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之間的利益同盟;但是,兩者都誤讀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這類誤讀並非完全沒有理由,但仍然是誤讀,因為他們把某些個別現象普遍化了,猶如盲人摸象。不錯,拿美國來說,一般外界認為學界與政府之間的交流比較密切,而從事政治科學研究的某些學者,好像也有較多的機會在某一階段出任政府的某種職務。但是,從總體上說,這樣的現象,就人數而言,很少;就時間而言,甚短(一般不會超過兩年);就個人「好處」而言,政府資歷對於學界資歷一般並不具備加分作用;就觀點交流而言,則往往是通過這種渠道,學界影響政府更多,而政府影響學界較少。當然,在政策研究界,這種所謂「旋轉門」現象,即官員下野作研究、研究者出山做官員,相當普遍。但是,如前所述,政策研究界與學術界之間,還存在着體制、文化等多方面的區隔。這些情況,都是超乎中國研究領域的一般現象,但是也適用於中國研究領域。
社會科學研究,包括政治研究,也如同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其首要目的是認識論的,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說的「格物致知」。反過來,如同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可以推動技術進步、造福人類一樣,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當然也可以推動社會進步,政治科學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用來改善政治。但是,這種應用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的、急功近利的;政治科學的學術研究,和關於公共政策的研究、關於公共事務的評論,其主要區別之一,就在於這種研究其本身的自足性。所謂「象牙之塔」,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回到中國的語境,也可以說,什麼時候政治學不是為了當前的政治需要(不管是與什麼樣的政治價值聯繫在一起的需要)而展開,什麼時候政治學才有可能真正成為社會科學。
再次,怎樣進行中國政治的研究?簡單的答案是:它必須遵循一般意義上的科學研究方法。在英語世界,中國政治研究屬於政治科學中的「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領域,具備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切要素。這就是說,這是一個充滿探索、討論、辯駁和創新的研究領域,是一個通過對於事實的調查(Empirical Investigation),來展開對於權力、國家等等主題的概念思考(Conceptualization)的社會科學領域。當然,如前所述,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與主流政治學相比,與其他相關學科比如中國歷史研究相比,一般認為,其學術水平還比較低(如何評價學術研究的水平,我們下面很快就會談到)。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政治研究就不遵循、或者不合乎科學研究的基本規範,不必具備科學研究的基本要素。中國本土的社會科學研究,水平也不高,往往尚不具備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素,也常常不合乎科學研究的基本規範。這個「水平不高」,與外部世界(在本人有限的了解中,首先是英語世界)相關研究的「水平不高」,可以說是兩個範疇的問題。打一個比方,一個參加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比賽但沒有得到名次的運動員,可以說水平不高;一個從來沒有取得過參加任何運動會的比賽資格的體育愛好者,也可以說是水平不高,但兩個「水平不高」不是一回事。也許中國很多方面的科學研究是領先世界的,但是,就政治學研究而言,則如本文開頭所判斷的,可以說尚未入門;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政治研究,基本上尚不存在。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並不存在遵循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方法的中國政治研究。
最後,誰來評價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不是政府或者政黨,這在強調學術自由、大學獨立的制度下是很容易理解的;也不是企業或者公司,雖然西方社會是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儘管企業可能通過提供資助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科學研究的選題和方向。那麼,是不是社會大眾呢?不是。因為學術不存在所謂民主;專家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由外行來評判的。民眾可以是一本流行政治讀物是否成功的評判者,但不可能是一本政治學術著作是否出色的裁判員。同理,公共媒體、大眾輿論,在這裏也無緣置喙。是不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管理者呢?準確地說,也不是。因為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管理者可能並非學者;即使是學者擔任管理者,學術上隔行如隔山,少數管理者也不具備評判多種多樣的研究成果的能力。那麼,究竟誰來評價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呢?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同行。換句話說,只有同一領域的研究者,才具備評價相關研究的資格與能力。
以上四條,如前所述,其實不是中國政治研究的特殊現象,而是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整個科學研究的普遍情況。不過,在中國的語境中,以此來理解自然科學的研究似乎比較容易,以此來理解那些比較不「敏感」的社會、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似乎也還比較容易,以此來理解政治研究好像就比較困難一些。政治研究的這種特殊性,在某些人那裏是如此強烈,以至一些在西方經受了政治科學訓練、目前回到華人社會(主要是香港、台灣)的華人學者,也要特意強調中國政治研究的所謂「本土化」。試問,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有什麼本土化問題嗎?電腦科技有什麼本土化問題嗎?顯然都沒有。即使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國歷史的研究、中國語言的研究,似乎也沒有聽到什麼「本土化」的呼聲。我不是說,政治學研究可以像物理學研究一樣超越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制約;我恰恰是說,社會、文化等因素,甚至很可能還包括政治因素本身,往往很容易對政治研究構成干擾,使其難以具備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要素,難以實現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規範。在尚不具備這些要素和規範的情況下,「本土化」可能無助於中國政治研究在本土的起步和發展。托克維爾的美國政治研究[25],對美國人來說,似乎並沒有什麼需要本土化的問題,而是奉為經典,是不是美國人對於美國政治的研究較之中國人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水平就差很多呢?中國本土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不發達,水準也不高,是不是因為這類研究有被「殖民化」的問題、因為他們為西方的(首先是美國的)有關中國政治研究的選題、態度、理論和方法所主導呢?如果有這樣的問題,當然不好,需要糾正;如果事實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則「本土化」再好,恐怕也是並不對症的藥方。
在我看來,為了建設和發展漢語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我們應該強調一種不妨稱之為「開放的自主研究」的態度。所謂「自主」,就是研究的立場不受非學術因素的左右,首先是不受政治力量的左右;所謂「開放」,就是研究的思路不為非學術因素所羈絆,包括不為民族的、意識形態的因素所羈絆。政治是我們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我們的研究指引;民族文化可能提供我們實施研究的獨特視角,但不應該取代科學研究的基本規範。怎樣才有可能以「開放的自主研究」這樣一種態度來建設中文世界的中國政治研究,這是一個巨大的題目,是需要同行們的集體努力、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夠找到答案的。在一定程度上,本書是一個小小的開始。
(本文是即將出版的《透視中國政治》一書的序言。此書由吳國光、程曉農編輯,博大出版社出版。)
【注釋】 
[1] 我這裏主要列舉了英語國家。由於語言能力的限制,我對非英語國家(和非中文國家)的政治研究狀況不甚了解。不過,根據我有限的了解,英語國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學研究中居於領先地位,英語也已經成為政治學研究成果發表的主 要語言。
[2] 「毛概」即「毛澤東思想概論」;「毛鄧三」則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課的簡稱。
[3] 關於全權主義(或極權主義,即totalitarianism)政治的特點,以及其與權威主義(或威權主義,即authoritarianism)政治之間的區別,Juan Linz 有系統的論述。見: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4] 當然,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成果,是來自拉丁美洲的學者在美國形成和發表的。但是,其中許多學者,也同時在拉丁美洲的本國任職並進行研究和發表成果。例見: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5] 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在中國本土之外,特別是在非漢語世界,相當繁榮。據不完全的估算,主要使用英語發表對於中國政治研究成果的學者,當今不下5百人。當然,這個概念相當含糊。比如說,本人刻下正在寫作中文討論中國政治研究,但是,卻無疑也屬於這5百人之列。大體上,這個數字是根據兩項指標來界定和估算的,即:1)一位學者是否使用英語作為研究成果的主要發表語言;2)這些出版品是否構成對其專業資格評價的主要衡量尺度。根據這樣的指標,這5百人主要分佈在英語國家,但也有不小的部分生活在非英語國家。比如說,在荷蘭、德國、法國、台灣、南韓等非英語國家和地區,學者們也在越來越多地使用英語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對於他們的專業資格評價也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這還不包括相鄰學科如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甚至文學等那些涉及中國政治問題的學者。在英語國家,幾乎每個稍具規模的大學,目前大都開設中國政治的課程;重要的大學的政治系,至少有一名、甚至兩名專研中國政治的專家。在中國之外的非英語世界,特別是日本、俄國、法國、德國等國家,中國研究,包括中國政治的研究,本來就有相當的根底,近年也在迅速的發展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各國的中國研究,其根底本來主要是漢學(Sinology),即在人文科學領域展開中國研究,但近年來也漸次把研究重點轉到了社會科學方面,特別是政治學方面,從而與北美洲和大洋洲一樣形成了以當代政治為重心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領域。
[6] 順便說一句,歷史學,至少在英文世界,是一門蔚為大觀的學問。美國大學本科,文科各系往往以歷史學係為最大,教授和學生的數量在文科各系中往往都是最多的。
[7]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宋永毅主持的「21世紀中國基金會」也在這個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迭有成果出版。最近的相關著作有宋永毅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和丁抒主編的《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2007)。在這方面,國內外華人學者的個體的中文論著更多,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舉。
[8] 吳國光,「試論改革與『二次改革』」,《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吳國光,「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二十一世紀》,2002年6月號。
[9] 例見:肖濱,「改革的停滯與自由主義的兩種調子」,《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王俊秀,「改革已死,憲政當立」,http://www..com/Article/gd/200803/20080305215021.html, posted March 5, 2008, accessed March 8, 2008.
[10] 這方面較新的研究成果,可見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更大範圍的相關研究,參見: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S. Lee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國對外政策」一課時,使用包括Harry Harding, David Lampton, Kenneth Lieberthal, Robert Ross, David Shambaugh 等美國學者的論著為讀物,曾經引起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的不滿;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反華學者」。我並不準備從這樣的個別例子推出任何普遍結論;但是,這至少幫助我感性地了解了兩個重要的情況:第一,中國大陸的學生,在相關中國的問題上,對於國外的研究成果,究竟隔膜到什麼程度;第二,按照這些學生被教給的那種思考方法,他們是如何界定什麼樣的研究是「反華」的。
[12] 中國大陸的一些高校,好像也在開始這麼做了。不過,普遍程度如何,閱讀哪些著作,學生反應怎樣,我尚未有系統的了解。
[13] 僅《當代中國研究》近年發表的論文,就政治論題的覆蓋面來說,也遠遠超出本書所能收集的範圍。比如說,中國當代的政治傳播和媒體運作,政府腐敗與社會監督,民間反抗與社會運動,就是近年《當代中國研究》非常關注的方面,就此發表了不少精彩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篇幅所限,本書沒有選收這些方面的內容。至於更為廣闊的相關研究方向,比如對於中國改革和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都應該屬於中國政治研究這一領域。也僅僅是因為本書篇幅的限制,我們沒有涵蓋這些方面。
[14] 英文文獻中有這樣的研究,例見: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Zhuang Pinghui, 「Gimlet-eyed grannies watch for the unusu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6, 2008, p.A2.
[16] 當然,對某些社會人文學科和某些學派來說,「敘事」(narrative)可以成為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不過,一則這種方法至少迄今並未普遍為政治科學學科所接受,二則,在我看來,這種「敘事」是包含概念化在內的,僅是形成、呈現和論證概念的方式比較獨特。
[17] 這與中國在1980年代末期出現的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主張不是一回事。較有代表性的論著,例見: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1979);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8] 兩種學說的代表作分別為: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 韋伯(Max Weber)最為強調科學研究的這種「不完整性」(incompleteness)。參見:Raymond Aron,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Vol. 2: Durkheim, Pareto, Weber, tr. by Richard Howard and Helen Weav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9), pp.224-225.
[20] 所以,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專門寫了一本甚受關注的書,來研究注釋的起源、形成和發展。見: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中國大陸書評刊物不少,但是似乎都是屬於所謂「公共知識」領域的;海外中文刊物本來就很少,立足學術的更少,專注社會科學的則少之又少,要在分工細緻的社會科學之不同領域都發展出專業水平的書評,實屬不易。
[22] 事情當然總有例外。立足智庫機構、但依然堅持學術研究、其成果仍然在學界很有影響的中國政治學者,並不乏人。比如說,當年供職布魯金斯學會的Harry Harding,和目前在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任職的裴敏欣,都不僅在政策分析上出類拔萃,而且在學術研究上也廣為學界同行所敬重。
[23] 關於大學的起源和特點,參見: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2).
[24] 例見:丁學良,《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1990) |
|
 程曉農:中國中產階層的貧富真相(圖)
程曉農:中國中產階層的貧富真相(圖)

 顏純鈎:習近平的又一條絞索:援俄是死,棄俄也是死
顏純鈎:習近平的又一條絞索:援俄是死,棄俄也是死
 吳國光:習近平逆轉型 中國將和平變革還是流血革命?
吳國光:習近平逆轉型 中國將和平變革還是流血革命?





 國事光析:「孫悟空」代表什麼樣的中共外交?(圖)
國事光析:「孫悟空」代表什麼樣的中共外交?(圖)
 國事光析:習近平為什麼訪問美國?
國事光析:習近平為什麼訪問美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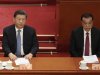
 吳國光:獨裁與惡政的螺旋效應:再談「斯大林邏輯」
吳國光:獨裁與惡政的螺旋效應:再談「斯大林邏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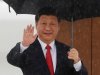
 吳國光:反間諜法的奧妙:隨心所欲抓敵人
吳國光:反間諜法的奧妙:隨心所欲抓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