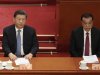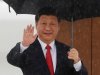冬日噴薄的早上
-- 一九七七年歲尾私事
![]()
吳國光(加拿大)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大陸改革三十周年,中共拿它大做文章,包括炒作高考三十周年的事,妄圖把近二、三十年間投身改革事業的一大批讀書人,緊緊拴在它的戰車上,企圖賺取合法性資源。
1.早班喇叭
印象中,那個初冬的早上陽光燦爛。這個印象也許不準確,因為心情會影響記憶的。
那天正趕上我上早班,也就是白天的正常班。騎車去廠子的路上,兩旁各家機關和工廠的高音喇叭,照例在七點三十分,準時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時隔三十年,我現在還能準確地記得,我那天走到了什麼地點,正聽到喇叭里播出了那條消息。
消息說,大學要恢復考試招生。這本來是天下大學的第一通例,然而,對於我和我的同輩人來說,卻成了恩從天降的稀世綸音。幾分鐘之後,我紮下自行車,換上破爛油污的工作服,進了轟鳴的車間。這天,我完全聽不到幾百台織布機的咔咔梭聲,我沉浸在自己內心的轟鳴之中。
班上,我寫了一首七言長詩。記這詩的那個小本,前些年我還在收拾雜物的時候看見過,現在卻一時找不到了。
2.七分學星
恰滿二十歲的我,早以為自己的學業到了盡頭。我的高中班主任、語文老師王兆軍,已經三十歲了,更是這麼想。
一九六六年的夏季,王兆軍行將在臨沂一中高中畢業,正躊躇滿志地準備報考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要做建築工程師。一場政治風暴驟起,大學史無前例地關門大吉,他只好回家種地。後來,當了代課教師,來到那間在田野中孤零零地佇立兩排房子的朱隆中學,也就是我高中求學的地方。
大學關門的時間,其實沒有那麼長。一九七零年,在三年的文革高潮過去之後,毛澤東發話,『大學還是要辦的』。不過,學生是從工農兵中招收,辦法是『群眾推薦,領導批准』。『群眾』怎麼推薦,領導按什麼標準批准,我們無從得知。兆軍和他高中時代最要好的同學楊文法一起,聽一個瞎子算過命。那瞎子說:你們都文才很好,不過命中注定七分學星,不到十分的。他們二人的解讀是:『十分學星』就是大學生,咱們這輩子上不了大學了。
我還曾經看到一絲光亮。那大約是一九七三年年初,有傳言說,以後中學校長也可以推薦個別學習成績突出的高中畢業生,直接參加大學招生考試。朱隆中學的校長姓鄭,一天在校園裏把我叫住。我正緊張,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小伙子,好好學,明年我推薦你去考大學。在當年的形勢下,聽了這話雖不敢認真,但總抱幾分嚮往。與王老師談起來,居然師生之間會暢想到屆時選擇什麼專業。老師當然推薦自己當年的第一志願,還是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啦。
那年夏天出了個張鐵生。這樣一來,不要說高中畢業生直接升大學了,連文化考試也差不多廢了。偏偏,上級要求認真學習張鐵生的事跡,學生們奉命就此作文,論述這一『反潮流』壯舉的偉大意義。我中學時代的作文,數這一篇最短、最差,二百字一頁的方格稿紙,不知道怎麼湊滿了一頁零幾行。
以後,當農民,進工廠,儘管天天燈下苦讀,但卻從來沒敢做過上大學的夢。我的青年時代,那是沒有夢想的。能搜羅到隨便一本什麼書看看,已經樂趣無窮,已經夢境逍遙了。真的是隨便什麼書:從農家萬年曆,到《歷代法家文選》,從村里大嬸針線筐底那舊黃紙的《十世姻緣》,到幹部手中為了學習所謂『馬列六本書』而下發的《反杜林論》。走在路上,風颳來一張半是糞污的《參考消息》,我一定蹲下,找一根樹枝撥着,兩面看完。我母親教書的那間學校的舊同事,都不奇怪,路老師家的大小子,為什麼會走着走着突然蹲下,在冷風中,聚精會神地對着地面,數分鐘如痴如呆。
3.不懂『漢語』
記得當時可以填報四個志願。其實只有三個,聽說最後一個志願一定要寫上『服從組織分配』,否則說明政治品質有問題,是沒有被錄取的希望的。我姐姐聽她廠子裏幾個有文化的人這麼說了,回家鄭重其事地叮囑我這個。
三個志願的選擇也太多,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應該填寫什麼。經過三年的農村和工廠生活,我的志趣完全聚焦到和文字相關的東西上來了。父母當然不願意我們學文科,誰都知道那是有政治風險的。可是,他們知道我早就有很強的獨立意志,也了解我這些年在文字上的努力和追求,我去學文科已經天經地義了。與同樣準備報考的王老師商量,答案一樣自然而現成:要麼中文系,要麼新聞系,反正是干寫文章的行當。
問題是,我在報名處讀遍相關材料,沒有發現哪怕一個中文系在招生。新聞系有一個,是上海的復旦大學。可是,我嚮往北京。躊躇之下,選擇了北京廣播學院的新聞採編專業為第一志願,復旦新聞作為第二。第三就選家鄉的大學,山東大學;專業嘛,沒有中文和新聞,就選哲學吧。
不料想,交表的時候,工作人員對我的填報發生了疑問。那是一個中年男人,他說:你不是報文科嗎?北京廣播學院是理科。事實上,廣播學院有一些科系是理工,有一些則是文科,這『新聞採編』當然是文科。我解釋了兩句,那人卻不由分說,要我改一下。好不容易找出這三個志願,再改改成什麼?這般犯難之下,免不了斜眼瞅瞅別人是怎麼寫的。旁邊幾個青年男女,個個第一志願都是北京大學。那時候,我幾乎完全不懂這所那所學校的所謂好和差,但卻知道北京大學是有名的。看人家那筆字,也敢報考北大,我為什麼不行?沒有中文和新聞專業,那就和對待山大的策略一樣,選哲學了。
後來見到王老師,知道他報的是復旦中文、復旦新聞、和山大中文。為什麼他可以報中文系呢?原來,招生資料上的專業名稱,『中文』無一例外寫的是『漢語言文學』。我以為那是『漢代的語言與文學』的意思,居然不懂得『漢語』就是中文。
4.嚮往考試
考試的那幾天,趕上我上夜班。向我所在的乙班班長請假,不准。其實,那時候工作紀律不嚴。一邊是什麼『大干快上』,另一邊卻是常常鬧電荒,八個小時的班,有一半時間幹活就不錯了。這倒騰出一些時間複習功課。可是,班長大約是看人讀書就有氣,也許覺得小青工要考大學是異想天開。這類見人讀書來氣的領導,我那幾年見多了。對不起,只好曠工了。
工廠一年,是我讀書較多的一年。畢竟,和農村相比,這裏沒有生計的憂愁和煩惱。領了那每月二十一塊錢的工資,換了飯票進食堂吃飯。不像在村裏的時候,為沒得吃發急還不說,幾個大小伙子一起過日子,更頓頓愁着怎麼把糧食變成熟飯。這裏,周圍有文化的人也多了。一起進廠的小韓,大名躍進,喜歡交朋友,口口聲聲叫我『大哥』,時不時帶兩本比如默林的《馬克思傳》這樣的書給我。哪兒來的呢?他說,人家都知道我有個大哥喜歡看書,借我讓我給你看的。慢慢地,我也確切知道了一些書的來源。那些與我並不相識但卻讚賞我讀書的同事,從家裏或朋友那裏搜羅來這些書,特意托小韓轉借給我。我們那是個大廠,兩千多人。還有一些女孩子,我即使知道了是她們幫我借的書,也因為青年男女之間的羞澀,從來沒有當面向人家道謝一聲,都是小韓把書拿回去還她們了。今天多半已是中年下崗職工的她們,生活也許仍然艱辛,很難想像她們會有機會讀到這篇文章。遠隔重洋的我,對這些善良的人有一如既往的由衷感激,希望這不會因為言語的笨拙和表達的遲到而失色吧。
終於,考試了。十年來中國第一次的大學入學考試開始了。能坐進考場,這就是人生最大的機遇。坦白地說,我一生嚮往考試,尊重考試,熱愛考試。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個這樣不公平的世界,考試該說是相對最公平的了。我常說,如果人生就像考試一樣,那該多麼美好。這決非矯情,更沒有炫耀,如果你了解我們是歷經多少艱難乃至絕望之後才有了參加考試的機會。
監考的老師似乎也很興奮。他背着手,在教室里走來走去。在我的桌旁,他站了好長一段時間。第一場,記得好像是政治。考完出來,樓道里充塞着興奮、疲憊、懊惱和好奇。這位老師穿過人群離去的時候,看見了我,停下來,問了一句話:報北大了嗎?我回答:報了。他微笑着點點頭,挾着我們的考捲走了。
5.《斯巴達克》
在焦慮中等待的日子,最難打發,也最為空虛。這時,來了個生人。
那天我正在上班,這人到班上找我。他高高大大,看年紀比我大一些,自我介紹叫作徐平,是我們廠子對門那家針織廠的附屬學校的老師。他說是教師進修學院的錢老師要他來找我,並且邀我去拜訪錢老師。
我有些朦里懵懂,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不好意思問,徐平也不解釋。我們去了,錢老師問了我一些日常讀書學習的情況。聽說我讀書作筆記的,他要我拿一些筆記給他看看。我那些筆記,都是用一面油印了各種宣傳材料的紙張的背面作的,主要是抄書,當然抄的時候有些歸納整理,也把一些自己對內容的註解或相關的想法等等寫在旁邊。對於古典着作,往往是整本整本的抄,一本下來就很厚,用紙捻子裝訂起來。那些紙張是各處湊的,規格先不整齊;紙的質量很差,油印水平也差,油墨往往都滲到背面也就是我寫字的這面了。反正這些筆記甚不美觀,我也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撿了外觀稍好一點的幾本呈上。
當時的談話情景和內容,現在都忘記了,腦海中只有一個鏡頭十分清晰:有一天,錢老師很興奮,哆哆嗦嗦地(他的右臂有些不便,動作的時候給人這個感覺),打開書桌腳櫥的鎖,從最底層抽出一本書來,向我們展示他細心收藏的寶貝。書名叫做《斯巴達克斯》。我現在手頭有這書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本,但那個時候,除了《青年近衛軍》、《鐵流》和幾本高爾基等蘇聯文學作品之外,我幾乎沒有讀過外國小說。很想讀它,但不好意思張口。錢老師接着就把它鎖好了。
至於錢老師對我的筆記是什麼看法,那是後來我從父母口中知道的。認識錢老師之後,直到後來好多年,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也常到我父母那裏做客。父母轉述,錢老師看到我連帶注釋一併抄了整本《李賀詩集》的那本筆記上,對書上的一條注釋提了點兒不同的看法,他很讚賞,認為這年輕人『不簡單』。至於那是條什麼注釋什麼意見,父母說不上所以然來。而我的所有那些筆記,包括至少有一麻袋的剪報,是剪貼在一本一本的《紅旗》雜誌上的有關國際知識、科學知識、歷史知識之類的東西,在父母多次搬家過程中,也不知丟到哪裏去了。
錢老師叫錢勤來,上海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九六五屆畢業生。
6.長河浪花
當時錢老師應該告訴了我,他剛剛參加了高考語文閱卷回來。但是,他不談閱卷的情況。為什麼托徐平找我?他說是聽說了這麼個年輕人。
我有位好朋友,朱瑞璽,是純粹的農民子弟,高中比我高一級,但比我大不少歲,那時已經師範畢業在縣城的一所中學當語文教師了。我也常到他那裏借書,畢竟有個中學圖書館做依靠。這天,在他們校園裏,一見到我,他就興奮地說:今年高考的作文,水平真棒。原來,據說是全省第一名的作文,已經傳出來了,他有抄的一份。我說,你拿給我看看。他迫不及待,一邊走一邊說:我都背下來了,先背開頭給你聽聽。
『歷史的長河,有多少翻湧的浪花……』
『這是我寫的呀!』不等他第二句出口,我就跳了起來。他停住腳步,側過臉來,驚訝而認真地看着我:『真的?』
我接着背了第二句,問他:『是這樣的嘛?』
我們兩個幾乎要歡呼起來。
興奮沖昏了頭腦,接下來的事情我就不大記得清楚了。等到發榜之後,錢老師告訴了我們一些語文閱卷的內情。他說,我那篇作文寫得那麼長,有閱卷老師懷疑我是不是事先朦對了題,準備好了這篇《難忘的一天》的現成文章。可是,老師們發現了我試卷草紙上塗抹的提綱,這就可以排除疑問了。而且,作文之外的解詞、古文翻譯等題目,據錢老師說,我的回答比標準答案還詳細許多,看得出有些基本功。他們打算給這份語文試卷九十八分,斟酌之後,怕分數給高了,連帶讓人認為全省語文判卷給分偏高,不如減兩分,於是給了九十六分。
這些事情,也許不該我來轉述。說實話,我這個人常被譏評為『驕傲』,但卻從不自滿,最看不上『得意』二字。那個年代,沒有『高考狀元』這一說,我也不是『高考狀元』。一篇時文,起承轉合,正好對了閱卷老師們的法眼,是我的運氣。今年夏天,回鄉探望臥病的老父,一位中學老同學請吃飯,座中有位原不認識的朋友,也是那年一起參加高考的,現任我當年考場所在那所中學的校長。為了是我,他給面子來吃飯,一見面先說:『你那篇文章,現在看沒什麼了,當年還真是不凡。』我感謝他那後半句的好意,更感謝他那前半句的實話。
7.讀書人生
其實,把高考成功看的多麼得意和了不起,多是如今浮躁、勢利人心的反映。我們那個時代,畢竟還樸實。即使從困苦中一下子考上大學,按我鄉下大爺(當地這樣稱呼伯伯)的話說,就是從此只住樓房了,那周圍人們對你的關注,也還多是有關那孩子是如何學習的。比如說,廠子裏開始傳言我會背《新華字典》和《漢語成語詞典》,大約就認為這是我的學習秘方。說來慚愧,《新華字典》裏很多字,我至今不認識;從這篇文章里,也看得出,至少今天的我,不愛使用成語。考試不是人生,人生比考試艱難、複雜得多。在那之後的很多年裏,我有機會到中外多所着名大學讀書,學位也念了幾個,可是,到今日知天命之年,就人生而言,還不是照樣成績平平?
但是,我愛讀書。這一點,既不必吹噓,也無需謙虛,就是人的一個特點罷了。當然不是壞的特點。一個不給人讀書機會的社會,是荒謬的;一個讓人無心讀書的社會,是墮落的。
一切揭曉的那天,我正巧也是在圖書館裏。縣圖書館很小,我搞不到借書證,但報紙雜誌是開放閱覽的。隔一段時間,我總會來看看那時還為數極少的幾份文學刊物。忽然,楊文法老師來了。我以為正巧遇上他呢,可他說,我到你家裏去了,你媽說你到這裏來了。有什麼事嗎?我問他。他把我拖出閱覽室,一出門就低聲、緊張而又興奮地告訴我:『你考上北大新聞系了!』
我一愣:『不可能吧?我沒有報,再說也沒見北大新聞系在山東有招生名額呀。』
楊老師說:『不會錯。我剛從教育局來,他們的人今天到濟南拿錄取名單去了,到那先打電話回來說的。』
我忙問:『王老師呢?』
『他上了復旦中文系。我們現在告訴他去。』
王兆軍那時調到了縣東幾十里地的俄莊公社做秘書。楊老師和我一路疾踏自行車,記得最後是輾轉在田野里找到了王老師。我們一行三人馬上回城,直奔縣教育局。
已經是接近下班時間了,縣教育局的小院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等候錄取通知書的。局裏的崔西品老師,認識王老師,也認識我——我出生的時候,他父親正在我父母任教的學校當校工呢。他把我們讓到一間僻靜的辦公室里,說晚上去他家吃飯,就趕着出去說服聚集的人群離去。通知書不可能這樣直接發到個人手裏,那要通過單位下發。
等人散盡了,崔老師進的屋來,一臉喜氣,恭喜王老師和我。我們都有些侷促,對自己的命運並沒有把握。終於,崔老師打開了一個大紙袋,撿出兩張錄取通知書給我們看。白紙黑字,我那一張上寫着,我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聞專業普通班錄取。
我不明白『普通班』是什麼意思,心裏有些打鼓。當然,後來明白了,就是不是『進修班』的意思。我也不明白,至今還不明白,我是怎樣被超越志願地錄取到中文系新聞專業的。那年,山東還有濰坊的王廣新同學,也進了北大新聞專業,成為我們班的老大哥。不管有多少不明白,那最最重要的東西,現在反正是明明白白了:我終於有了專心讀書的機會。
8.夜行列車
第二天,當廠辦公室通知我去一趟的時候,我知道,那張紙已經通過正式渠道送達了。
我們廠那年考上十一個大學生。不過,直到二月中旬,我們都還在廠里照常上班。我在織布車間的緯紗室,職責是幫女工們把成袋的緯紗穗子倒進她們的小車,然後她們就推着車子遊走在一列列的織布機之間,把緯紗裝到機上。我這是極簡單的工作,就是用點兒力氣。進廠的時候,大家都爭學技術工種,這件活兒,可以說是全車間最低劣的工種,沒人想干。分到我,就是我吧,好處是沒事的時候隨時可以看書。班長會不時進緯紗室掃一眼,看我在讀書,臉上不快。可是,換緯工們不來裝紗的時候,這位倒紗工,慣例不是睡覺,就是不知到哪兒遛去了,我卻老老實實守在這裏,睜大兩隻眼睛,他還能說什麼?
那幾天,班長不到緯紗室來了。來的經常是一些不認識的人,三三兩兩,在門口往裏看一眼,就跑了。師兄弟們告訴我,那些人是來看看這個念書人什麼樣的。
家裏面,許多親戚、朋友、鄰居、同學、同事,也這樣來看看。這同事,包括父親的同事、母親的同事、姐姐的同事。我自己的同事倒不算多,因為我在這間工廠剛剛一年。我插隊村子裏的老鄉來的不多,進趟縣城對於他們來說是件天大的事情。來了就要留他們吃飯,母親極忙,還要為我置辦行裝。沒有合適的箱子,父母決定把他們結婚時置辦的一件柳條包給我帶上。已經用了大約二十五年的這件行李,煙熏日曬,外觀不大看得出本來的乳白色了。在正月的酷寒中,姐姐用自行車馱它到沂河邊,里里外外洗刷了一遍。一套被褥裝進去,也就差不多滿了。
這已經是一九七八年了。二月二十六日午後,父親、二舅和我一起上路,坐五個小時的長途客運汽車,來到京滬線上的古城兗州。接近半夜時分,我告別父親和舅舅,登上了來自上海的過路列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車。車上沒有空座,一夜站到天津。大站卸客多,我可以坐下了。應該打個瞌睡,可是,我沒有睡意,在朦朧的晨曦中努力兩側急速展開的景觀。清晨,列車抵達北京站。二十七日八點八分,當我走出車站的時候,空氣清寒,人聲鼎沸,一輪金紅的太陽,剛剛在最後的冬天裏噴薄而出。
三十年後,二000七年十二月初
於太平洋另岸,桴浮書屋
配圖:

山東臨沂棉紡織廠一九七七年高考後即將上大學的部分青年與廠領導合影。前排右一為作者。

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七七級同學一九八二年初畢業合影。三排右二為作者。

吳國光參加21世紀中國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