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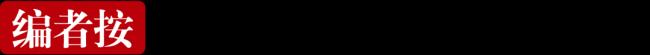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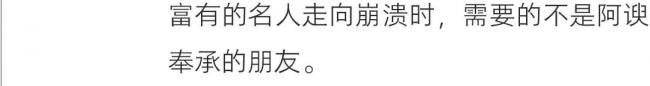
多年以來,我痴迷於同一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通常在很年輕的時候即抵達眾人仰望的成就高地,人們驚嘆於他們的才華,在絕對的才華和實力面前,時運機遇統統可以靠邊站,不再構成平庸者自我開脫的藉口。隨後,仿佛命運開了場不合時宜的玩笑,這些才華橫溢者被酒精、毒品、情感剝削者誘惑、利用,自我放逐,萬劫不復,生命的拋物線在高高揚起後,一個急轉,垂直落下。
音樂界有「永遠的27俱樂部」,傳記作家查爾斯·R·克勞斯寫道:「死時27歲的音樂家的數目,以各種標準看來確實都十分不尋常。(雖然)人可能在各個年齡時去世,27歲時去世的音樂家在統計學上仍是一個高點。」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個圈子以高風險的生活方式聞名,圈內人樂在其中,圈外人漠視縱容,悲劇至多為此按下三分鐘的暫停鍵,公眾普遍願意接受,這就是光鮮背後的陰暗面,至於自毀,某種程度上還為天才的命運蒙上了最後一層傳奇色。
2020年,46歲的天才華裔創業者謝家華(Tony Hsieh)被消防人員從一間濃煙四起的儲藏室中抬出,昏迷不醒九天後,因吸入煙霧引發併發症不治身亡。他的死亡場景令人心悸,謝家華把自己鎖在一個朋友的儲藏室里,讓一名員工給他拿來一氧化二氮、大麻、打火機、披薩和蠟燭。他喝醉了,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下是一張骯髒的毯子,警方稱火災原因不明,並排除了他殺的可能。
本質上,這是又一個關於嗜癮的故事,但謝家華的死引發人們關注矽谷科技繁榮的另一面。
在20世紀90年代,投資者喜歡他們的創始人勇於冒險,有點極端。在那些日子裏,才華橫溢、特立獨行的創始人就是品牌,在小組討論中對着一群過着謹小慎微生活的MBA和富豪發號施令。謝家華完美符合這個標準。安吉爾·歐陽和戴維·金斯在《神奇小子——謝家華、Zappos和矽谷的幸福神話》中指出,「我們的文化縱容精英去濫用藥物。我們的法律規定,未經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很難對他們進行治療。富有的名人走向崩潰時,需要的不是阿諛奉承的人。這是一個醜陋的故事。有很多東西需要為此負責。」
在謝家華身上,我意外發現了另一層共情,來自東亞家庭教育對成功的普遍認知,要學習成績優異,要掌握多門樂器,要從事一份體面的工作,最好是律師和醫生……謝家華終其一生都在試圖跳出規訓,與此同時,他對「自由」和「幸福」表現出異於常人的渴望。這一度是他前進的動力,創業的靈感來源,也在冥冥之中寫好了註定失敗的結局,無論自由還是幸福,本質上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他認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獲得幸福,他一直在建造和獲取,直到最後,他擁有了世界上的一切——但這仍然不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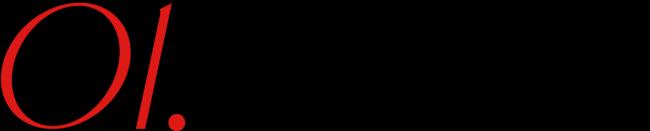
移民二代
謝家華於1973年12月12日出生於伊利諾伊州,父親謝傳剛和母親李小林是來自台灣的移民,他們在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讀研究生時相識。他的父親是化學工程師,母親是社會工作者。
李小林是那種會每天早起為家裏的三個孩子做好早餐並且準備好午餐飯盒的母親。謝家華的同學回憶,飯盒裏的食物「無可挑剔地健康」,「Tony顯然不愛吃,他會用午飯換其他人的巧克力零食。」作為一個母親,她對時間管理也嚴厲到苛刻的程度,這讓謝家華的朋友們感到誠惶誠恐,「我常常覺得自己不是那種可以和Tony一起玩的好學生」。

謝傳剛和李小林是典型的亞裔家長,對孩子寄予很高的期望。在1960年代,他們本科畢業後選擇背井離鄉深造時,伊利諾伊州香檳市只有三家中餐館,一家亞洲超市。彼時,整個社會正在從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的創傷中恢復,種族關係緊張,留給亞裔的空間很小,降低自我存在感成為那一代移民無奈之下選擇的生存策略。
他們希望孩子能夠超越,或者至少複製自己在學業上的成功,無論在學校還是家庭,謝家華很小就意識到自己無時無刻不處在父母劃定的條條框框中,包括但不限於:每個星期只能看1個小時的電視,所有的課程成績都要拿到「A」。父母總是告訴他不要擔心賺錢的事,這樣才可以專心功課。在自傳《三雙鞋》中,他總結道,有三類成就是亞裔父母們最為在意的。
第一類是學術上的成就:得高分,獲獎勵,或者公開表揚,取得優秀的大學入學會考(SAT)成績或成為學校數學隊的成員。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可以進入哪一所大學就讀,而進哈佛是最享有盛譽的殊榮。
第二類是職業上的成就:成為一名醫生或獲得博士學位被看作是最高的成就,因為這意味着你可以從普通的「謝先生」變成受人尊敬的「謝博士」或者「謝醫生」。
第三類是樂器的掌握:幾乎所有的亞裔孩子都被迫學習鋼琴或小提琴,或兩者兼而有之。在每次聚會的晚餐結束後,孩子們必須在所有的家長面前表演。這表面上是為了娛樂大家,實際上卻是家長們互相評比孩子的一種方式。
謝家華也被要求練習樂器,但他一點也不想在不感興趣的事情上浪費時間,於是想出一招矇混過關,把自己彈奏鋼琴的過程用卡帶錄下來,假裝每天1小時的刻苦練習。他擅長並享受「跳出盒子思考」的過程,被規劃、安排、循規蹈矩的優秀,這些在上一代移民眼裏無比政治正確的需求對他來說實在是過於死板和沉悶了。他對賺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總是幻想着能賺很多錢,「因為對我來說,金錢意味着以後我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在未來的某一天擁有屬於自己的公司的創業想法也意味着,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過創造性的生活。」

25歲的億萬富翁
21歲的時候,謝家華和哈佛大學室友一起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了5個月程式設計師。之後,兩人不甘替人打工,召集了一幫朋友,以2萬美元起家,創立了LinkExange公司。這家以廣告交換(中小網站在自己的站點刊登別人的廣告,同時自己的廣告也在其他網站顯示)作為主營業務的小公司,在當年深受青睞。
1997年,著名風投紅杉資本看到其中存在的商機,給這個項目注入了300萬美元。此後LinkExange迅速崛起,成為擁有超過80萬家會員的大型網站。一年後,微軟宣佈以2.6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LinkExange,年僅25歲的謝家華成為了億萬富翁。作為收購條件之一,他需要繼續在公司待上一年,就可以帶着4000萬美元離開,如果中途離職,就必須放棄那筆收入的120%。
待在公司無所事事,這樣的例子在矽谷收購案中十分常見。事實上,還有個專門的詞來形容這樣的創業者,那就是「寧靜收入」。
儘管年紀輕輕就變得非常富有,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悲傷——他突然意識到,他所擁有的還不夠。他坐下來寫下自己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和朋友聊天聊了一整晚,直到太陽升起,這讓我很開心,中學時和一群最親密的朋友一起玩『不給糖就搗蛋』,這讓我很開心。」
謝家華無法忍受自己在微軟浪費時間,當財富變成了一個觸手可及的數字時,他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是成功和幸福,「我覺得我們都被社會和文化輕易地洗腦了,我們停止思考,錯誤地認為金錢代表着成功和幸福,其實,能享受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

那一刻,他決定停止追求金錢,開始追求激情。不久以後,他做出了一個無比大膽的決定,在互聯網商務發展初期,將名下所擁有的一切財產賤賣,將全部身家投入一家叫Zappos(美捷步)的初創企業,不成功,便成仁。
謝家華帶領Zappos挺過了互聯網泡沫破滅,不僅如此,Zappos的銷售額在2000年是160萬美元,到2009年超過了1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鞋類電商網站。Zappos在眾多競爭對手中殺出重圍,絕大部分要歸功於謝家華卓越的商業遠見,他很早就意識到,讓顧客在網上購物時感到舒適和安全是成功和發展的關鍵。


謝家華奉行「無管理」理念,Zappos公司以「亂」著稱,謝家華相信這樣能最大程度發揮員工的創造力。圖片來自 Ronda Churchill
就像學生時代為了逃避練琴而作弊,在商業世界,他依舊是那個「跳出盒子思考」的人。在一次接受採訪時,他打了個比方形容真正的企業家和MBA、職業經理人的區別,「如果你要求他們做一個盤子,MBA和職業經理人們會上網搜索製作步驟,需要的材料,然後按部就班做出一個標準的產品,企業家會環顧四周,把所有盤子都掃一遍,然後琢磨怎麼做出一個不一樣的。」
關於Zappos如何重視客戶體驗,一個他在公眾面前反覆講述的故事是,與市面上所有的電商客服中心追求應答效率和訂單轉化率不同,Zappos反其道而行之,將每一通用戶打來的電話視為「建立情感聯繫」的絕佳機會。事實上,大多數電話都無法帶來實際的銷售收益,有人打來為即將舉行的婚禮詢問時尚建議,也有人打來僅僅是因為孤獨。「我們沒有話術,不考核通話時間、轉化率,最長的一次,通話記錄顯示,我們的一位員工和對方聊了7個半小時,原因是對方的親人剛剛去世了,需要安慰。」
至少從結果看,Zappos「不急功近利」「一心為客戶」的口碑和形象換來了巨大的品牌價值。2008年,伴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謝家華在西雅圖拜訪了亞馬遜董事長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兩家公司文化的相似之處,以及貝佐斯提出的讓Zappos以獨立實體形式運營、保留相同管理團隊的提議打動了他。執掌十多年後,他以超過10億美元的價格將公司出售給了亞馬遜(Amazon.com Inc.)。

傳遞幸福
2010年,謝家華的自傳《傳遞幸福》出版,連續27周登上《紐約時報》十大暢銷書榜單,在書中,這位說話溫和、性格內斂的矽谷新貴用平實、幽默的語言描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兩次創業經歷,他將Zappos的成功歸因於對客戶服務、企業文化、員工培訓和發展的重視,「這些是我們長期戰略中唯一的目標,其他的一切都能而且最終都會被他人複製。」
在Zappos的企業文化中有一條是「創造歡樂及一點點搞怪」,當時,去那裏參觀的訪客很難不對其留下深刻印象。事實上,Zapoos的辦公室更像個遊樂場,有人屁股底下坐着碩大的粉色瑜伽球,有人在大搖KTV鈴,走廊上,扮成蜘蛛俠和鋼鐵俠的同事激戰正酣……這一切都是被允許的,甚至,坐在辦公室正中間工位上的謝家華樂見這一切的發生,他鼓勵員工施展個性,消滅一切官僚作風束縛,他創立了一種經營哲學,其核心理念是,快樂的員工是令客戶滿意、成為回頭客的渠道。
謝家華和幾位Zappos員工一起踏上了全美巡迴宣傳新書的「傳遞幸福」之旅,所到之處,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和崇拜,一夜之間成了「幸福」的傳教士,提到Zappos,人們首先聯想到的不是「賣鞋」,而是謝家華和他的企業幸福理論。巨大的名人效應之下,越來越多的人渴望加入Zappos,想方設法接近這位天才創業者,加入他的核心好友圈。

儘管如此,離他最近的員工看到了謝家華的另一面。他的「生活總監」(life managing director)Holly與另一位助理,人稱「陽光小美女」的Mimi在工作上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後者憑藉資歷以及與老闆的關係更近不斷打壓Holly,減小她的管轄範圍。Holly感到很委屈,在旅途中被同事排擠,但謝家華選擇置之不理,仿佛只要他什麼都不做,危機就會自動解除。
這與Holly起初設想的完全不同。她曾有一份穩定的收入,當謝家華向她主動發出工作邀請時,「傳遞幸福」令她既心動又期待,但她很快意識到,至少對工作人員而言,這趟旅途和「幸福」的關聯不大。「Tony會不停邀請新人加入,為他們摘星星、摘月亮,提供想要的一切,全然不顧周圍人會怎麼想。」Holly後來反思道,「或許是我對這份工作的期待過高了,來了之後才發現,這裏缺乏管理結構、流程,以及面對面的溝通,讓工作變得十分消極——幾乎是『傳遞幸福』的反面。」
表面上,謝家華的世界向所有人敞開,但沒有人可以走進他的內心世界,向他傳遞幸福。Antonia Dodge曾在Zappos擔任性格測評師一職,在他看來,謝家華身上存在某種形式的社交恐懼症,「但他總是把自己投入各種各樣的社交場合,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不讓社交恐懼阻礙自己,這也是為什麼他每天都需要灌入大量伏特加。」
在一次專訪中,主持人問謝家華,「你覺得人們對你最大的誤解是什麼?」他說:」我是個既內向又害羞的人,在人群中話不多,人們容易誤以為我不喜歡他們。」台下的一位聽眾請他給內向的創業者一些建議。「喝點酒吧。」他脫口而出,人群瞬間被笑聲點燃。

上癮
直到他去世,那些在社交網站上追憶他的社會名流仍然不知道這位46歲的創業明星生前經歷了什麼,為何會以這種離奇的方式退場,更不用說那些曾為他的書和Zappos買單的公眾,畢竟他看起來那麼健康又願景充沛。人們猜測,他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沒有公開?他是不是被綁架後撕票了?
Jon Greenman是謝家華哈佛期間的室友,他在畢業後去拉斯維加斯見過老朋友幾次,Greenman回憶,無論晚餐還是聚會,謝家華永遠在一輪又一輪地喝酒,與他過去認識的那個Tony很不一樣。儘管如此,好友的酗酒行為並未引起他的警覺,「他看起來控制得不錯,日常工作沒有受到影響,也沒有因為喝太多酒而變得好鬥、暴力或者癲狂。」
酒精之外,還有毒品,它們頻繁出現在謝家華舉辦的各類會議、活動和慶典中。在《快樂王國:謝家華的Zappos》(The Kingdom of Happiness: Inside Tony Hsieh’s Zapponian Utopia)一書中,作者Aimee Groth回憶有好幾次和謝家華以及他的朋友們一起服用搖頭丸。
謝家華拒絕在公眾場合談論藥物濫用,理由是無論他怎麼說,人們都早有兩極化的結論了。私下裏,他堅持自己不存在嗜癮,「我的理療師說我一切正常,我不可能對任何藥物上癮,因為我不具備癮君子的人格。」好友Michelle聽了之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只能說,他的傲慢又抵達了一個新的高度。」
John Gartner在《輕度躁狂的邊緣》一書中指出,許多美國企業家實際上都患有輕度躁狂症,最普遍的症狀是一種異常的樂觀情緒,對自己、未來以及整個世界充滿信心。
患者通常精力旺盛,思維活躍,在強烈的躁動與雄心壯志驅動下,表現出異於常人的生命能量和創造力。美國過去200年來的商業成功,尤其是新興的IT業,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這些人。
藥物、酒精、性愛共同構成了矽谷的派對文化,局外人看到這種派對都感到不忍直視,但局內人樂在其中。有參會人士稱,通常嘉賓們會先喝點酒,最後藥物才會出場,一般是搖頭丸,這些藥片還會貼上一些科技公司的logo,以便將陌生人變成親密無間的朋友。搖頭丸刺激多巴胺過分分泌,人們開始盡情釋放,或擁抱、或發泄。

謝家華用大把時間思考如何獲得幸福,他相信金錢無法換來幸福,他投入對幸福的科學研究——這是一個已經在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紮下根的理念——並且尋找方法來設計它,諷刺的是,他最終陰差陽錯選擇了一條「捷徑」——上癮。
身體機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嗇。誘發幸福感的神經傳導素分配得非常儉省,而且大都發給對於求生或繁衍後代有益的表現。癮品會矇騙這個發送系統,促使這些誘發快感的神經傳導素暫時增多。這些東西是對抗難堪處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離現實桎梏的新手段。服用癮品不願停止的人,是掉進了以快感為誘餌的陷阱,最終遭其奴役。
到2020年,謝家華每天吸食3到5克氯胺酮。他刻意斷食,體重掉到不足100磅,幾乎不睡覺,故意憋尿,降低身體吸入氧氣的數量,還吸起了能引發缺氧的一氧化二氮(笑氣)。
朋友們表示,謝家華不太適應一對一的環境,而疫情一來,他的許多社交活動都無法開展,他吸毒吸得更厲害了。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他的行為越來越偏執和怪異。他要求把水龍頭打開,好讓他能聽到水聲;他在牆上寫字,在房間點起幾十支蠟燭。他僱用法庭書記員站在一邊,記錄室友們的談話。致幻劑作用下,他聲稱將創立一個新的宗教,突破這個由人工智能控制的世界,解開通往宇宙的逃生密碼,成為新的宇宙主宰者,治癒所有人的身心疾病。
他的一切都在分崩離析。最令人不安的是,人們顯然對謝家華的狀況缺乏關心。他周圍的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一切並沒異常,看上去像是在為他慶祝什麼一樣。

愛心樹
謝家華雖然性格內斂,內心深處卻有想把人聚在一起的熱望,很願意在朋友身上花錢花時間。一名友人曾以兒童文學作家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作品《愛心樹》(The Giving Tree)來形容謝家華。在這本書中,愛心樹把自己的每一部分都送給了它愛的小男孩,不索取任何回報。希爾弗斯坦筆下,男孩過分索取、理所當然和無動於衷,與大樹的無私付出、心甘情願和全心全意,都到了極端的程度。
謝家華的友人和前同事稱,謝家華把個人生活與事業融為一體,尋求與同事的精神統一,更多是為了實現個人夢想,追求新奇的感覺,而不是為了積累財富。他這種對待人生的方式為他帶來了無數財富,吸引了眾多崇拜者,但也造成了他的悲劇結局。
30多歲時,他宣佈了一個3.5億美元的項目(Downtown Project),要把拉斯維加斯市中心改造成一個科技烏托邦,並說服朋友們和他一起搬到一個類似城市公社的地方。他在拉斯維加斯市中心建造了一個不大的房車公園,他就住在其中一輛240平方英尺的清風房車(Airstream)里。他的寵物羊駝馬利常在社區里四處遊蕩。
這筆3.5億美元的投資包括餐館、零售場所和一支2012年創立的科技創業基金,謝家華因此深受當地民眾愛戴。據知情人士稱,他為朋友購置房子、公寓和餐廳。「他為別人建造溫室,讓他們做自己,自由生活。」協助謝家華創作自傳的好友簡·林(Jenn Lim)說。《紐約時報》稱,「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夢:一座城市中的一次西部范兒的豪賭,突然在沙漠中創造出一座『美麗年代』(BelleÉpoque)的巴黎和古羅馬。」
儘管重振社區的理想很豐滿,但這個耗資巨大的項目從一開始就沒有設定任何實際又可量化的目標,也沒有引入任何一位外部投資者,明眼人都能看出,這就是謝家華一個人說了算的「帝國」。在他40歲生日當天,嘉賓們被要求在身上紋一個圈才有資格受邀生日派對,消息傳出去後,拉斯維加斯當地媒體《太陽報》評論道:謝家華的帝國瀰漫着「宗教崇拜」的氣息,不服從就出局。專欄作家John L. Smith諷刺那些謝家華的信徒「仿佛排隊等着坐上聖誕老人膝蓋的孩子們一樣相信他的花言巧語」。

隨着時間的推移,烏托邦世界裏不那麼美好的一面開始逐漸暴露,有資不抵債的創業者選擇自殺,一位謝家華的員工在得知自己突然被裁後,將掛在項目總部牆上的「社區、碰撞、共同學習」(COMMUNITY, COLLISIONS, AND CO-LEARNING)的標語一把扯下。本地媒體毫不留情地將項目形容為「頹廢、貪婪、領導力缺失的縫合怪」。
與此同時,Zappos內部也在經歷震盪,謝家華堅持推行「合弄制」管理模式,向員工發出最後通牒,要麼完全承諾成為合弄制的真正參與者,要麼離開。他們放棄了原來權力集中的金字塔式組織,進入了「沒有職位,沒有經理,沒有等級」的新型組織模式,但謝家華顯然低估了合弄制的難度,大規模的人員離職給Zappos帶來巨大的衝擊,經過三年實驗,2018年,謝家華宣佈放棄合弄制,他本人也宣佈退休。
但謝家華並沒有放棄他的烏托邦夢想,在拉斯維加斯市中心項目和合弄制相繼失敗後,他和一群追隨者搬進了帕克城的一棟豪宅,這群人表面上幫助退休後的他重新物色新項目,但家人和偶爾前去探訪的友人發現,圍繞在謝家華身邊的人背地裏縱容他酗酒吸毒,然後趁他不清醒的時候撈錢。他的毒癮越來越重,身邊的「馬屁精」將他同家人隔絕開,昔日好友和同事無法聯繫到他,就連諮詢師多次上門也被擋在門外。
他揮金如土,給一些「朋友」付雙倍工資,只要項目被他接受,發起人就能獲得10%的佣金,他的「朋友」紛至沓來,都想分一杯羹。民謠歌手Jewel到他家去過一次,她在那兒遇到的每一個人臉上都掛着職業假笑,好像查理家巧克力工廠的接待員,一位帶領Jewel參觀的人說,「Tony是個天才」,「Tony正在做非常偉大的事情」,另一位說。他們充當着謝家華雇來的「群演」和「打手」,作為回報,每個月領着高額的薪水,住着豪宅,享受着一萬美元一天的豪華餐標——魚子醬、帝王蟹輪番登場,卻幾乎什麼也不干。
謝家華的真誠和慷慨沒有換來對等的友情,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對火產生了迷戀。他的房子很髒,數百根蠟燭的蠟滴在家具、地毯和枱面上。謝家華養的小混種梗犬Blizzy的糞便遍佈整棟房子,有的還沾着蠟。
在他的豪宅里,Jewel問周圍的人:「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你們的目的是什麼?」沒有人給出認真的回答。在Jewel離開之前,她與豪宅新任安全主管進行了交談。後者後來在謝家華在康涅狄格州去世前離職。據知情人士稱,這位歌手對安全官員說:「如果他和房子裏的所有人都死於一場大火,你可別說你沒有被警告過。」
****
謝家華身上有很強烈的矛盾點,一方面他承認自己有「社恐」,不擅長和陌生人打交道,另一方面他在創業階段幾乎逼迫自己置身一群人的環境裏,與此同時,他表現出極強的利他動機,比如希望周圍的人都感到快樂、幸福,找到自己真正的激情和追求所在。這些實在過於矛盾,必然會在一個人身上造成分裂和撕扯感,他恐怕需要說服那個格局偏小的「社恐的自己」去適應那個環境更希望他成為的「企業家的自己」,酒精、大麻、一氧化二氮、氯胺酮……接二連三成為了潤滑劑和助推劑,並最終奪去了他的生命。
「成癮」來自拉丁語的addictus,這個詞意味着一個人被奴役。對成癮的主體來說,成癮就是針對精神壓力的解決辦法,不管這個壓力是痛苦、衝突或者興奮,主體都沒有辦法忍受、內化。雖然成癮表現多種多樣,但歸根結底,都來源於內心未被滿足的情感需要,或缺乏親密關係,或缺乏安全感,或逃避內心深處的傷痛與困境,而與一個人是否意志力堅強幾乎無關。比如,一個人在成年後不停更換伴侶,或許是因為童年時期經歷了太多次親人的分離。
人心深不可測,即使一個人與親人的關係一般,渴望從親人那裏獲得的愛與支持並未得到充分滿足,也並不必然導致他需要在踏上社會後報複式地尋求補償,對他人的愛與支持產生無止境的貪婪。但謝家華的悲劇隱藏着一個無比肯定的真相,依靠金錢或者說一個人對他人單方面的不平等的付出與施捨建立的關係是多麼虛偽與脆弱,這種關係哪怕始於個體之間真誠的欣賞與信任,也會逐漸滑坡至另一種畸形的權力寄生關係,
而當一個人周圍只剩下靠他的薪水支付單度日的人時(這和某些老闆的生存境遇類似),他會抵達自大、狂妄、迷失的巔峰,成為寓言裏那個一絲不掛的國王。
謝家華用他的金錢與生命再一次驗證了一場人性貪婪實驗,結局毫無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