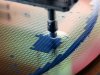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剛過了而立之年,就已顯出蒼老的面孔和略帶佝僂的身軀卻總是會浮到我的眼前來。
一個「油頭滑腦」的老犯人
記得我頭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只覺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瑣的樣子。當時獄警拉開牢門時,他畢恭畢敬地低頭弓背面對牢門,滿臉堆笑,活脫脫一個油頭滑腦的老犯人。
那天我剛剛從北京炮局看守所拉回工廠「被鬥爭」了才拉過來,連東南西北都沒弄清楚。看到他,馬上就想到電影裏見過的那些壞人。因此,當獄警在我身後把牢門哐當一聲鎖上後,摸不清狀況的我完全沒有想要搭理他。
沒想到,獄警的腳步聲剛從門口離開,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幾根光溜溜的半圓木拼成的床鋪上,從我手裏奪過獄警給我的一床薄薄的、裏面的棉絮滿是窟窿的被子,幫我疊好放在床的裏頭。
他告訴我,剛進來肯定還不習慣這個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經習慣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點的中間讓給我睡。同時壓低嗓門一一告訴我牢房裏「政府」——他總是把這兩個字掛在嘴邊上——定的各種規矩。
如平時起床要疊好被子放在床裏頭,犯人不能站在床上或地上,必須要下床面對門坐在床頭;床頭的塑料桶是馬桶,一定要蓋嚴,否則屋裏味道太大;每天上午幾點會放人出去倒馬桶,必須在幾分鐘內抓緊倒淨洗完返回號里,否則會被罰;一周有幾次放風,每次放風會放多長時間,經過樓道下樓時千萬不要停下來,也不要東張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還有一個比我稍小些的犯人。當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4月5日的事件進來的。他是在4月4日當晚下夜班後沒事,陪着師傅到廣場看熱鬧,意外被抓了個現行,抄了進來的,一直關到這個時候。只被審了幾次,就再也沒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師傅和他的家裏人,他就會撲簌簌地掉眼淚。
我剛進來的那些日子,幾乎天天被押去審問。一審就幾個小時。每次被提出牢房後,他們兩人都會偷偷地扒着窗戶,透過油漆剝落的玻璃縫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從一樓側門押着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來,牢門剛一關上,老犯人都會馬上把已經涼了的飯菜遞到我的手上,催着我把飯吃完。
監獄裏的飯千篇一律。每頓一個窩頭(一周會有一次給吃饅頭),一碗菜湯,菜湯麵上會有幾片閃着亮光的明油。我的飯量不大,關在獄裏又不運動,一個饅頭也還湊合。但那個才19歲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進來後發現,幾乎每頓飯,老犯人都會把他的饅頭或窩頭分一半給他。
老犯人在牢房裏最拿手的餘興節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錯,雖然不敢讓獄警聽到,聲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聲哼唱的那些我聽也沒聽過的各種中外歌曲,還是會讓我覺得即使在牢裏,日子有時候過得也還算得上心曠神怡。我也因此從他那裏學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從「書香門第」到「專業小偷」
其實,被關進這裏幾天後,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經歷。先是小犯人告訴我他是小偷,然後是他主動告訴了我他從十幾歲開始,因偷竊,幾次被教養,到被判刑的經過。
說起來,我和父親去幹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門買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車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準備買衣服的錢和積攢了將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對小偷,我曾經十分反感和憤恨。可是,當老犯人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之後,對他我卻無論如何也恨不起來。
我過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窮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書香門第。其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母親還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學的校長。家裏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從小就學過彈琴,會識五線譜,很喜歡音樂,而且看了很多閒書。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只因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連着兩天沒回家,跟一個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東西被抓,母親因為覺得有辱家門,堅持不去領他,後來經父母同意,把他送進了工讀學校。從此他就和更多的壞孩子走在了一起,學了更多的偷竊手法,再也改不掉偷竊的習慣了。
當然,每次被抓到後,他都想過要改掉偷竊的毛病。但他告訴我說,染上這個毛病後,人就像是吸了鴉片上了癮似的,一有機會在眼前手就癢得不得了。終於,他在15歲時被送去勞動了幾年。出來後,因為生活無着,家裏也不理他,再度偷竊,再度被抓,作為屢犯,又超過了法定年齡,因此被判了7年刑。
再出來的時候,他已經將近30歲了,既無工作經歷,又沒有單位接收,城裏幾乎無處立腳,於是街道上一紙報告,把他定為「四類分子」,送去延慶山村里實行管制勞動。
這個時候,我已經大致弄清了關押我的這個地方。這是北京第一監獄看守所,又叫半步橋監獄。
兩次逃跑失敗,被打入「死牢」
1976年7月,我入獄兩三周後的一天半夜,突然間天搖地動,把我們全都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滿樓道里犯人們大呼小叫,砸門哭鬧,恐慌至極。但是,因為監獄把牢房的門統統換了包有厚厚鐵皮的沉重木門,只在齊眉高的地方為方便獄警監視犯人的動靜,從外面開了一扇小鐵窗,必須從外面拉開才能打開。
對外的窗戶,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們幾乎無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況。儘管所有人馬上意識到這是極劇烈的地震,因獄警全無聲息,犯人們聲音再大,也無能為力,只好聽天由命。
我們號里的小犯人喊啞了嗓子,兀自坐在鋪邊哭泣。老犯人雖然摟着小犯人的肩頭未吭一聲,但是牢房每震顫一次,他都會神經質地嘟囔一次「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直到餘震消失。
記得在那個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臉輕鬆相,一聲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發呆。我當時試圖和他講話,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兩聲而已。直到晚上熄燈之後,他才突然在我耳邊小聲地問我:「你想你家裏人嗎?」我記得我應了一聲。又過了一會兒,他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媽今年60歲了。」
整整一個晚上,他把自己的頭包在被子裏面沒有出來。我分明聽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過了一個多月,因為沒有報紙,沒有廣播,除了白天黑夜,我們誰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間聽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續不斷地響起震耳的哀樂聲,我們當即猜測一定是毛去世了。
又過了一周多時間,小犯人意外地被釋放了。那天老犯人也顯得十分激動。……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對我講了實話。原來,他這次並不是因為偷東西進來的,而是因為政治問題。
一個小偷犯了政治問題,這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但卻是真的。
他的變化原因很簡單。他被送去農村管制勞動。作為「四類分子」,在農村中就像麻風病人一樣,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們每天清晨四點鐘就被趕起來打掃村裏的街道,天亮以後再被趕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來,大部分時間都被人看管着。
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爛,經常吃不飽飯,離村還要打報告,節假日別人放假他們照樣要勞動。至於年輕人想娶媳婦,則連門兒也沒有。被管制了幾年之後,他和另外一個年輕的四類分子終於覺得生不如死,下決心逃跑了。
沒想到,兩人沒經驗,以為到城裏找錢容易,想着一路從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卻不料城裏鬥爭的弦繃得更緊,幾天後就給抓了回來。這回更慘,兩個人被接二連三地鬥爭不說,還被吊在房樑上打得死去活來。
此事之後,兩人老實了一段時間。但不知道他們從什麼渠道聽到了台灣的廣播,裏面說得天花亂墜,說是只要給香港某信箱寫信,就可以得到經費。於是,這兩個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為真,想着寫封信就能拿到錢,然後再往境外跑。
老犯人於是自封什麼「燕北支隊參謀長」,然後按照廣播中的地址給香港這個信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自然落到了有關部門的手裏,他們兩人也就成了「現行反革命」……
我在一個月後被換到另一個號子,然後在1977年1月初被無罪釋放,從此很長時間再也沒有聽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佈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紅×的他的名字……
2023-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