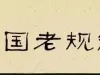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方菲訪談》。
今年是89六四33周年,當年的六四成為一代人不可磨滅的記憶,這其中也包括著名的美國漢學家林培瑞先生。1989年的時候,林培瑞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對華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公室主任。六四屠殺發生後,他曾協助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避往美國駐華大使館。1996年起,林培瑞被中共列入黑名單,迄今仍被禁止入境中國。
今天我們邀請林培瑞教授跟我們談一談,他當年六四期間在北京的經歷,他對今天中國社會時局以及走向的看法。
林教授您好,很高興您上我們的採訪節目。
林培瑞:很高興跟各位談話。
嚮往社會主義到中國,發現共產黨徹底說謊話
主持人:好的,謝謝林教授。好,林教授。我想首先先請您談一談這個問題。您以前在很多採訪中都談到過,說自己早年是個左派青年,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還很嚮往。但是您今天,是美國少數的對中共,可以說不抱任何幻想的中國研究學者之一。
而且從1996年開始,中共就不給您簽發籤證了。那您現在回過頭來來看這個歷程,您覺得造成您對中共認識這樣一個大轉變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林培瑞:這個故事說起來長着呢,只好說我一步一步地認識,從我早年的對社會主義的理想,第一次到中國去73年,旅行了4個城市的時候,稍微看到了一些蛛絲馬跡,知道我心目中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和實際上的中國社會是有缺陷的,是有不同的。
後來79年、80年那一年到中國去做關於文學的研究,我本來是研究文學的。看了許多文學的,上海文學的作品,主要對我影響大的是劉賓雁,比如他的《人妖之間》和其它的文章。
包括我在校園裏頭住,在廣州的中山大學的校園裏頭住,而且會中文能夠跟別人說話。那比較快地認識到,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主義跟社會的生活差距,不但在那兒,而且非常大、非常大。可是徹底破產大概是,不是破產,徹底幻滅,是到這個應該說是89年的1月,在布殊總統,老布殊來訪華的時候的一些經驗。經過了一些跟方勵之赴宴,赴宴會,布殊請的宴會有關的。
然後看到《瞭望雜誌》上和新華社報導的故事,跟實際的情況的差別那麼大,哪怕我已經幻滅了許多,可是到那個時候才認識,才知道,共產黨徹底說謊話,它是歪曲基本事實。它描寫方勵之赴宴,不是改編花邊文學的問題,是完全發明了一個新的故事,我吃了一大驚。還跟方勵之去說,哎,怎麼會那麼寫一篇完全是謊話的文章。
老方就笑了,你認識中國這麼多年,你還那麼天真,我們日子久了,對我們來說這種大謊話是天長地久的事情,你這個還是有點天真,這都是在六四發生以前的事兒。
經歷六四,對共產黨看法徹底幻滅
過幾個月,六四發生,那當然在這個幻滅之上就加了有血、有肉的經驗,應該說是我徹底幻滅的經驗。
主持人:所以聽上去您就是一步步在很多事實的教育下,慢慢認清了。然後您說的這個六四,我想問一下,就算您在六四前對中共已經幻滅了,不抱任何幻想,您有想到他們會開槍嗎?
林培瑞:沒有、沒有。我記得那天,前天晚上我跟我妻子到東城跟朋友去吃了飯,吃了個蒙古飯,我都記得。回來的街上也看得到坦克車,老百姓在那兒送花呀等等,我都看到過。
而且送我們去的司機是個很好的一個小伙子,離開的時候,他拿出來一把刀子,在他的座位底下的一把刀子,拿出來說,今天他要到天安門去幫忙。我還是不相信,你拿了刀子去幫忙,是怎麼回事兒,沒有想到它真的會開槍。
第二天我妻子把我叫醒,我就聽到真實的,我們住在友誼賓館,友誼賓館對面是人民大學。人民大學的門前我去聽了,學生在那兒設了個廣播站,請各位從城市的不同地方回來的學生,說他們所看到過,他們聽到過的經驗,包括自行車的後頭有一些有血跡的衣服,我都看到過。對我是個比較大的一個震撼,我沒想到。
後來我第一個反應是要去聽知識分子朋友的一些反應,騎上了自己的自行車到住的鄰近的一些朋友的家,去問問他們到底怎麼看、怎麼想,而且我都說我能幫忙,你告訴我,我願意幫忙。到周五才到方勵之夫婦公寓去敲了他們的外門。
幫助方勵之到美國使館
主持人:那您當時幫助方勵之,是他們見了您之後,意識到自己有危險,請您幫忙呢?還是怎麼樣?這個過程能簡單說一下。
林培瑞:這過程本來是兩三個禮拜以前,他們的小兒子方哲來找我,問「萬一我父母要保護的話,美國使館能不能幫忙?」我告訴他,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使館的人,我始終沒有在美國政府裏頭工作過。可是答應他會打聽,我去打聽了,回話是最好不要這樣做。但是萬不得已,我們不一定說不,所以我腦子裏有這麼個印象。
到那天中午,六四的中午,到他們家去敲門,是李淑嫻教授,北大教授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她開了門,在那發抖,在我眼前發抖。她說「他們瘋了,真的瘋了」,然後請我進來。
老方坐在他的書桌那裏。他的態度是,「我沒有犯過法,我沒有做過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情,這是我的家,我當然不想離開。」我也不是要勸他們離開,我的態度是說,你們覺得我可以幫忙告訴我,在臨走的時候,我也跟李淑嫻那麼說。
她說,「好,我們要需要你幫忙,我們會打電話請你的孩子過來喝茶。」然後那時候在北京我有兩個孩子,女的8歲,男的4歲,都上中國的學校。
李淑嫻說要請他們過來喝茶,你就會知道我們可以接受你的幫忙。好,到下午大概四五點來了個電話,請我的孩子過去喝茶。
打電話我當然找出租車,那時運氣不錯,友誼賓館門前還有一個出租車,我到他們家去,他們下來了,下來我記得只是手裏帶着一個小包包,不是一個大行李。他的意思,尤其是方的意思是,去離開一兩天看看吧,不是要走,不是要離開他的家。
那是個星期天,美國使館不開門。我把他們帶到香格里拉飯店,也是北京西城的一個豪華旅店,到那去,我用自己的名字租了一個房間,給他們住了一個晚上,包括他們的小兒子方哲3個人住那兒。他們到香格里拉去,我就回到自己的家去。第二天到香格里拉去看看情況。
方勵之離開中國詳情
方還是猶豫,他不知道要不要去。他本來那天恰好是跟李政道,得諾獎的那個中國物理學家李政道,約了跟他吃中飯,他還想保留這個約會。所以你想,可是後來李淑嫻說服了他,他說好吧,我們去問問。
我們走小胡同,大概兩個三個鐘頭才到美國使館去。在詢問了我的資格,進去之後,在裏頭跟兩位比較高級的,是最高級的——那時美國舊的大使溫斯頓羅德,他已經走了,而新的替他的還沒到——所以我們跟他談了一個下午話,是跟二把手和兩三個人。
後來談了兩三個鐘頭以後,一直談到大概5點,方就馬上決定,他突然向我說咱走吧,離開吧。李淑嫻也同意,我們就出來了。出來,我到鄰近的一個也是個豪華旅店,去給他們租了屋子。
後來3天以後,有個美聯社的記者找到我那兒去問,我們聽說方勵之進了美國使館,拿到了政治庇護,你能不能confirm這說法。
我說我不能confirm,我帶他們進去,又把他們帶出來,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
後來他們一年多以後到美國來,我在普林斯頓跟他們見面,才知道那天晚上是怎麼回事。大概12點,夜裏很深的時候,跟我們談了半天,那一個下午的那兩個美國外交官到他們門敲門。
然後跟方勵之、李淑嫻說,我們的喬治‧布殊總統要求你們做自己的客人回到使館來。那時候李淑嫻就說服了方勵之,就是OK。方提了個要求,他說我們去最好保密,不要外傳這個消息,他還是怕共產黨利用這個消息。後來有記者告訴我,他們答應美國,那兩個外交官答應保密,可是第二天就沒保密,沒保密,公開了,這全世界知道方勵之、李淑嫻進了使館。
主持人:所以我覺得您第一次帶他們到使館起了特別關鍵的作用,可以說您營救了在中共黑名單上的方勵之夫婦。但是您當時有沒有擔心說幫助在中共黑名單上的人,自己也會有風險呢?
林培瑞:對我自己有風險,我沒有考慮,我不知道,我沒有想到這問題。而且我不是主動做了什麼英雄,真的沒有。我只是跟李淑嫻那天中午說:你們覺得我可以幫忙,我肯定會幫忙。而且我不覺得這是什麼很特別的事情,我覺得很多人在我那個位置裏頭會說同樣的話。
這當然看見一個人在一個龐大的一個殘忍的一個政府的威脅之下,你說你不幫忙嗎?很多人這是很正常的一個反應,不是個特別的反應。而且那一天我把他們放到旅館回家之後,我一直沒有感覺到危險。
也許我天真,也許應該感覺有危險,但是我真的沒有覺得有危險。也沒有覺得自己做英雄的舉動,也沒有覺得自己有可恥的行動。有很多人當然不只是中國人,是美國學者都覺得我做得很不對。我做科學院的代表,進入政治那麼深,危害了中、美學術交流關係,有人有那麼個看法。罵我,可是罵我的人、說我是英雄的人,我都不認同,我真的不認同。我覺得那一天做的事情非常很離奇古怪是真的。可是我做的決定,我根據什麼價值觀做了什麼決定,我沒有覺得是很特殊的。
六四是個轉折點,公共價值觀缺失
主持人:所以六四,您以前也說過對您個人也是個轉折點。那是個什麼樣的轉折點呢?
林培瑞:我剛才說八九年的二月底跟《瞭望雜誌》那個大概是我自己的轉折點。說六四是轉折點,從宏觀來說,我覺得六四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個轉折點。因為八十年代畢竟學生和知識分子和社會上許多人,有一種樂觀主義,中國會改變、能改變。而有不同看法的知識分子能夠跟上面某些領導人有一種互動,有一種聯繫。什麼趙紫陽、胡耀邦、田紀雲,這種比較開放的上面的人,有互動關係。
但是六四以後沒有,徹底不在。當然趙紫陽已經被捕了,胡耀邦死了,其他的開明的人不敢開口。所以九十年代跟八十年代相當不一樣。尤其是因為九十年代對中國的權貴高層,等於是說你們可以來為所欲為,然後李鵬家裏變成李家電,電的系統都是李家去管。然後科技系統是誰?是江綿恆。
主持人:江家。
林培瑞:對,他去管了。然後分別任何有勢力的高層的家庭,能夠撈一把賺錢,包括習近平的家也包括溫家寶的家庭。後來美國的《紐約時報》、彭博社(Bloomberg)有很大的報導都揭發這些。對下面的信號是說,我們在撈一把賺錢,為所欲為,你們也可以跟着來。然後中國社會上徹底它失去了任何的公共價值的概念。
中國文化裏頭當然有公共價值是很重要的一層,從儒家以來怎麼做人,古人怎麼做父親、怎麼做丈夫、怎麼做兒子,都有道德標準在裏頭。中國這個文化還是追求這東西,但是在九十年代就徹底沒有了、徹底破產了。
還有不同的宗教的興起,什麼道家、佛教復興,你們法輪功也出來、基督教也出來,這說明什麼呢?說中國老百姓的文化裏頭,這最底層的文化裏頭還是追求價值,希望能夠有公共價值。可是公共價值跟政府毫無關係的,沒有關係。公共價值在政治看、政府看,只有兩條。一個是賺錢,跟着我們去不擇手段地賺錢。一直到現在,我覺得中國社會太看重那個價值觀,賺錢。能夠賺錢,把錢弄到手裏頭是本事。
第二個價值觀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狹隘的那種淺薄的「我們是世界第一那種信念」。一直到現在,那小粉紅在電腦上當然充滿了這一種信息。跟着老百姓也有點過分地接受了這個,覺得這個東風吹倒西風,或者我們中國如何,我們的管制這個疫情比西方國家好,而且我們自豪我們這個民族主義。我說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我覺得是一種比較脆弱的一種民族主義,跟中國的最深刻的價值已經脫離了。你看中國的文化裏頭那麼多歷史、文學、思想、藝術,一直到現在在吃飯,中國菜……
主持人:飲食文化。
林培瑞: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豐富都多,有那麼多的好東西,有那麼多我認同中國文化的根據。可是共產黨鼓勵的是民族主義,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什麼奧運會、冬奧會,我們如何如何金牌多。這種東西跟更深的價值觀關係不大,但是吸引了很多中國老百姓,向這種比較膚淺的價值觀去找尋。
中共封鎖信息及製造恐懼,鼓吹賺錢或狹隘民族主義
這是共產黨的一種策略吧,它知道它沒有一種深層的真的牢固的價值觀。它六四以後,那種價值觀就破產了,它不能把自己推到「我們是道德模範」的地位上,沒有。所以它只能抓這種賺錢主義或者狹隘的民族主義,去讓老百姓做它的中國認同的對象的目標。所以我在這個層面上,我覺得六四是個轉捩點,真的。
主持人:對,我覺得您說得特別好。因為在中國這種民族主義其實是官方在灌輸的民族主義,但是我覺得中國的老百姓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接觸到很多信息。這個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怪他們,就是他能看到的就是官方的宣傳。那我覺得您說到六四,有中國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說如果當年六四之後美國和國際社會能夠對中共進行嚴厲的制裁的話,可能中共會垮台,因為六四事件。但是為什麼當時美國和國際社會沒那麼做呢?您的看法呢?
林培瑞:你剛才在我聽來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想說一說。為什麼中國老百姓認同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我自己覺得有三個原因。一個是有假的信息、廣播在那,有假的一些很多信息他們當然信了,他沒法不信呢?除非是能夠跳牆。
主持人:翻牆。
林培瑞:他不知道別的信息。但是有兩個更深的問題,一個是任何民族包括中國民族,當然希望能夠自豪,能夠proud of我是中國人、我是美國人、我是哪個人。所以中國老百姓當然他希望能夠be proud of china,這我不怪他。所以他看到什麼冬奧或者別的原因,或者說我們管的疫情比西方國家管得好,所以我們自豪。我不怪中國老百姓,也同意這種看法。
第三層,這也是因為住久了,一種極權主義底下的壓力的一個結果。很多人怕,他希望能夠跟別人一樣,跟別人沒有衝突。所以別人都那麼說都那麼看,我就跟着潮流,因為我這樣才安全。我站出來把自己的話說出來,有不同的看法說出來,哎啊,不安全。這是極權主義日子久了,灌輸到老百姓的腦子裏頭。所以很多人就聽到那些假的消息或者這個那個看法,或者中國站起來了,或者冬奧如何如何光榮啊。別人那麼說我就得那麼說。所以我覺得有這三層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我不怪中國老百姓。
但是弄得他們最後很難獨立思考,很難覺得有安全,把自己的不同看法說出來。包括我在加州大學中國來的學生都有這個問題,他們上課他問我,老師對的答案正確的答案是什麼,我把它抄下來,我跟您再說出來。
但是你讓他有自己的看法,你看這個故事那個小說,你自己覺得主人翁、主人公做的對不對,或者哪兒對哪不對,你怎麼分析,他很難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上,很難。所以我認為洗腦的層面,你表層上是把假的一些信息告訴人家,但是洗腦的深層影響,常常是毀壞了人的能夠獨立思考能力。你第二個問題是問……
西方若對中共制裁,會起好作用
主持人:當時美國和國際社會嚴厲制裁中共,中共有可能會因為六四垮台,這是有些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但是美國政府當年為什麼沒有……
林培瑞:這個我沒有水晶球,中國知識分子朋友也沒有水晶球,我們都只能說不知道。但是說美國和其它外國施加那個制裁能不能更嚴厲,那肯定會,而且我覺得更會起好作用的。就是說老布殊在六四沒幾個星期之後,他秘密地派了兩個人,坐飛機到北京,想跟鄧小平的人敬酒,去保持友好關係,這是非常噁心的一個舉動,非常不好,他不應該這樣。
而能夠跟最近西方對普京侵略烏克蘭,那麼有制裁,有成功的制裁一樣,當時在六四之後能夠這樣制裁中國,我說不準,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兒,但是至少會起好作用,比後來沒有起到的作用會有好作用。
主持人:對,是,就是在很多中國人看來,「六四」其實是共產黨顯露它真實的面目的一個重大事件,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事件沒有能引起西方世界足夠的重視和警惕。所以「六四」發生以後呢,美國和西方的這些國家,我想不只是布殊一個人啦,應該相當一批政要和西方的這種精英的人士,他們仍然覺得可以跟中共,就是跟它合作,給它更多的空間啊,您覺得為什麼呢?
香港自由被侵蝕比烏克蘭嚴重,西方為何對中俄態度不同
林培瑞:這個故事說起來也長着呢,從歐洲十六、十七世紀以來,歐洲的文化傳統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看法。就在其它的歐洲國家都是我們鄰近的,也跟我們也是信基督教,跟我們都有同樣的文化。
但是中國呢,遙遠的、神秘的、跟我們文化、跟我們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可是有時候也很理想,中國的社會據說是有士大夫念過書的人去當官的,這比我們的歐洲更好……都有一種,有一種浪漫的、不實際的想法。中國是遙遠的、神秘的地方,這種態度一直到最近還是有的。
對遠東或者,尤其是中國這個不同文化的概念,要尊敬,我們跟他們不一樣,我們也尊敬他們走自己的路,是,我們沒有資格去過問,有那麼個態度。比如說烏克蘭這一次發生的事情,普京侵略的時候,西方世界跳起來了,你這不行,你不能這樣,有很強的一種反應。為什麼對中國沒有那種,就香港,香港被侵略,被極權主義化了的例子,比烏克蘭還要清楚,而流血沒有烏克蘭多。
但是一個極權主義侵略一個愛好自由的一個城市裏頭,把它吃掉。香港的例子比烏克蘭還要清楚。所以我一直覺得西方關注烏克蘭的代價之一,是他不注意習近平,他把重點放在普京,不看遠東的這個發展。遠東的發展我覺得習近平威脅世界的將來那比普京大多了。
中國的經濟比俄國的大九倍,對不對?他的這個軍隊的人數也是大概比俄國大十倍。而且他的野心,普京的野心好像是要恢復大俄國的規模,包括東歐、包括中亞,但是習近平的最後的這個目標,不只是習近平,這個共產黨的高層,他們是想做世界一把手,他們一直認為美國是世界一把手,我們得跟美國去競爭,中國應該是一把手。
所以它是一個全世界規模的一個競爭心理,比普京還大,而且他的資源還比普京大。但是為什麼西方世界那麼看重烏克蘭,不看重習近平的侵略?我覺得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那是十七世紀以來,在東歐的那種,和遠東是不同的神秘的、遙遠的,跟我們沒有那麼切近的利益關係,有那麼個態度。當然我先得說明,對烏克蘭我是100%支持烏克蘭、反對普京。所以我剛才的話不是說美國和西方不應該關注烏克蘭,他當然應該關注。
主持人:您剛才說的那個民族主義啊,就是說共產黨這個沒有其它的可以凝聚老百姓的了,就用民族主義。那因為去年您不是寫了一篇研究的文章嗎?說共產黨用恐懼無知和暴力統治社會,那民族主義是不是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可以造成民眾的這種無知呢?還是說是民眾的這種就是說一種恐懼呢?
林培瑞:嗯,對,你提的對,恐懼和無知跟民族主義是有關的。你恐懼的話你的安全在哪?你的安全是認同共產黨希望你認同的民族主義。你的無知跟民族主義有關也是因為,比如我剛才提到幾次這個疫情的侵襲,說西方管的沒有我們中國好,這當然不是真的,就是根據一些歪曲或者不全面的信息。所以愛國主義愛我們中國怎麼怎麼樣,常常是因為不知道真況,當然共產黨希望你把黨和國看在一起,所以愛國變成愛黨,你愛黨共產黨歡迎,而這是你的安全。所以我還是覺得恐懼和無知是最基本的兩個工具。愛國主義也是一個建立在它們上頭的一個辦法。
中國人對美國的矛盾心態,年輕人私下會講真話
主持人:而且我覺得中共用的這個民族主義也好,或者所謂的愛國主義也好,它是用一種恨來凝聚人。我不知道您怎麼看啊?比如說很多人說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它都是一種愛呀、自豪啊、正面的。但是中共這個民族主義呢,它很容易就用恨來凝聚人,恨日本、恨韓國、恨美國。
林培瑞:你說的對。這個我覺得中國不只是共產黨,整個文化有時候對美國說是恨也不對,說是愛也不對,是一種愛恨交雜的一種態度,寧願說是一種競爭主義,一種Rivalry。你美國一把手,我恨你,我要跟你競爭,你不對,我恨你,但是恨裏頭也有尊敬,你是一把手,我妒忌你這個位置,等於說是我肯定你這個位置,所以不是徹底的恨,而是一種競爭主義。
而在實際上,你看那麼多中國這個權貴階層的人,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哪兒去上學,高考考不好,進不去北大,好,去美國、去澳洲、去加拿大、去英國,有多少西方的畢業生,中學畢業生,哎呀嚮往到天津、到北京、到上海去上大學。沒有。所以有時候不管話怎麼說的呢,具體的行動也說明問題。
主持人:對,沒錯。
林培瑞:不過我在加州這些學生,他們到美國來念書,在開課的時候,在上課的時候,他們不敢說任何對共產黨的有批評的話。但是等畢業以後想回國嗎?不一定,他想進入美國的研究所,大部分也希望能夠撈到綠卡,留在美國。一方面是說美國如何如何不好,另一方面是想方設法在美國留下來。
主持人:對,您之前跟我說過一個事情,就是說您在教課的時候,談到中國發生了這個三年大饑荒,幾千萬人死亡什麼的,然後中國學生不相信,他聽到您說這個他還很不高興,是吧?
林培瑞:對,年輕人他不知道。「六四」發生了什麼他不知道,有一個很聰明的學生跟我分析魯迅的小說分析得很好。他有一次到我辦公室來問,林老師,到底在天安門是學生殺軍隊多還是軍隊殺學生多?而他不是演戲,他真的不知道。
我把這個材料給他看之後,大饑荒啊,三千萬人死亡這些事兒,根本不知道,他們年輕人不知道,跟他們說的話,嗯有的信,有的不信,半信不信。而且我發現一個現象,在上課的時候他們不表示相信,甚至於反對,但是一般沉默。有任何一個所謂的敏感問題出來,或者批評共產黨的一個題目出來,他們大陸來的學生一聲不吭、不說話。但是一對一地跟他們交往,有時候常常是在辦公室裏頭,他們到我辦公室來談話,一對一的話,他就展開來問問題,甚至於說話。
我記得那年有一個研究生,我們在研究文學作品,研究到敏感問題的時候,他不說話,不說任何話。然後過幾天到我辦公室來,別人不在呢,他說:林老師,我爸爸簽了「零八憲章」。「零八憲章」被壓製得很厲害的時候,劉曉波去坐監11年的時候,非常敏感。可是他到我辦公室來說,我爸爸簽了「零八憲章」。
另外一個學生來跟我說,他準備回國的時候跟艾曉明合作。艾曉明在廣州是個很好的、很偉大的一個做紀錄片的一個人,可是在共產黨看是個很敏感的人。這個學生上課的時候他絕對不會說這個話。他告訴我,他不但是知道和佩服艾曉明,他準備到艾曉明那裏去工作一個夏天。所以那也是兩個層面,有的時候是一種精神分裂,真的,你剛才說的對。但是有的比較聰明的孩子,他能夠掌握兩個層面,他也知道他這是有計劃的處理,我什麼場合上說這個話,什麼場合說那個話。
中國老百姓的價值觀,正義感還在,就是希望
主持人:是,我覺得很多時候,很多事情其實都歸到您剛才說的這個恐懼和無知,就中共它用這些東西來統治民眾。但是我覺得在今天的中國,應該還是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而且中共這兩年很多的事情做的包括這個清零政策,可能也會讓很多人覺醒。您的看法呢?
林培瑞:清零政策起的反感到現在為止是大的城市上海有幾十個例子發生的,而這些人比一般的中國老百姓是更有知識、更sophisticated的人。他們起的反感,我覺得跟美國人會起的反感差不多的,你這樣不像話,不讓我出門等等等等。至於是一般的廣闊的老百姓的話,不一定那麼sophisticated。
但是與其說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我覺得不如說他是一種保持傳統的日常的價值觀的人。你說哪怕中國共產黨摧殘了中國文化那麼多年,有一種基本的價值觀還是生存的,尤其是比如正義。
前幾年我研究過中國的順口溜,然後網絡上那種調侃的話,他最恨的是腐敗。官方的不規矩的任何腐敗或者別的,他都很反感。這是根據什麼?是根據一種正義感。我覺得中國老百姓的正義感沒死。所以說是空白,我覺得也不是,它是一種普通的價值觀還在那生存。正義也隱含着一種平等主義,因為正義是什麼東西?你跟我或者甲跟乙、跟丙跟丁有不公正的意思是說應該平等,而不公正的含義就是說違反了它的自然的平等。所以在最根本的一個層面上,我覺得中國的老百姓的價值觀還在呢,沒死。
最近在冬奧發生的事,官方灌輸了那麼多「共產黨偉大偉大、怎麼光榮的意識」,我不是說沒有效應,是有的。但是同時也是今年的二月,在網上傳播了鐵鏈女那個故事,那麼多人馬上同情鐵鏈女的命運。是為什麼呢?這跟共產黨的官方的灌輸的價值觀沒有關係的,因為這是中國在社會上丟臉的事情,共產黨丟臉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人馬上就同情呢?是因為他們都認識鐵鏈女嗎?不會,只有非常少數的人認識她。是不是因為在江蘇那一帶有親戚朋友怕他們受影響啊?也不是,因為是全國的現象。那點擊率比在冬奧的點擊率還要高,這是一種從下往上的沒被打死的價值觀還在那。
所以我剛才說,與其說是沉默的大多數,我覺得是一種也有說話而且還有正義感的老百姓在底層有。所以我對於中國的將來不是那麼十分的悲觀,因為不管共產黨的上面的假新聞,灌輸假的概念等等多麼厲害,它還得對付老百姓的自然從下面生根的正義感的這種價值觀。
中共絕不認錯,計劃一切但計劃不了自己
主持人:是,而且我覺得從網上流傳的很多,可以看出他很有智慧。你比如像中共習近平現在這個清零政策啊,網上民眾就調侃說他跟這個古代的什麼精衛填海啊、夸父追日是一個意思。就是意思明知不可能做到,卻一定要做的事情。那您怎麼看為什麼習近平一定要堅持這個清零政策呢?您對這一點有什麼觀察。
林培瑞:共產主義自從蘇聯到中國來的時候,不允許共產黨有任何錯,要百分之百對,by definition。甚至毛澤東你可以,鄧小平說他是七分對三分不對,個別人能夠犯錯誤,但是黨不能犯錯誤。那習近平做黨魁他不能承認有任何錯誤,他有任何錯誤的話,他就不但是丟臉,他丟他的政治資本的一部分。所以清零政策從武漢以來,在武漢清零政策起了作用,然後它用這個事實去跟西方的西班牙、英國、印度、美國的處理方法做對比說,我們更明智。
好,當上海流行疫情的時候,它能夠放棄它那一種原則嗎?它能夠承認它以前的原則是有錯誤的或者是要改的嗎?不會,也不是因為任何健康有關的問題,是因為政治問題。「我承認我錯了」有很大的政治代價。所以我覺得我當然我這個人很難同情習近平,但是這一點上我可以理解他的困擾。
他一方面也許知道我這樣對待上海是起反作用、是很危險的,不要這樣堅持清零政策。但是同時我在這一邊要是承認清零政策是不對的,那就甚至更麻煩。所以他壓在這裏兩個勢力當中,到現在只能堅持他的清零,這是我的分析。
主持人:那您怎麼看最近就是圍繞習近平是否失去權力有很多傳聞,有說政變啦,有說什麼習下李上啦,有說什麼軟政變啦什麼什麼。您怎麼看呢?
林培瑞:我再說我沒有水晶球,而且共產黨高層裏頭的那些,對我來說是黑匣子裏頭的東西。我研究中國半天,我很難看清黑匣子。最近大概一年前到美國來了蔡霞女士,她以前是黨校中國共產黨史的一個教授,最內部的一個人。最近她說,因為有人問她你剛才問我的問題,習近平到底危險不危險?會不會有政變或者什麼?她說只有一句話能夠百分之百肯定,就是說「不知道」,你不能推測。
方勵之本來在他的回憶錄裏頭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話,他說:「共產黨對什麼都有計劃,有五年計劃、有經濟計劃、有政治計劃、這個計劃那個計劃。唯獨不能計劃的東西是什麼呢?它自己。」它自己怎麼計劃,沒辦法,因為不能控制。什麼林彪事件一來,那個事件一來,沒有人計劃,不能計劃。我覺得現在習近平的將來,也是那種情況。我同意蔡霞和方勵之的看法,不知道。可是我們不知道這個事實也是個挺有意思的事實。為什麼不知道?
主持人:對,我插一句,因為我也問過蔡霞教授這個問題。她跟我說的是:「凡事皆有可能。」所以我在想說您說的這個「不知道」,其實它代表說大家知道中共的是不可預測的,對吧。
林培瑞:對、對。我說她「不知道」跟你說她說「不能預測、不能有任何把握」是同樣的話、同樣的意思。
美中文化和老百姓有親近感,對美中關係走向樂觀
主持人:好,那最後想請林教授再說一下,您怎麼看美中關係的走向呢?
林培瑞:中美關係的將來,我這個問題我總喜歡把政治層面的關係跟老百姓之間的關係做區別。你說這個外交上的關係,我大概會同意布林肯今天的話,我沒有聽到。可是我覺得自從川普(特朗普)以來,川普的中國顧問,什麼余茂春或者白宮裏的人,我覺得很對,而且民主黨接他的班子的時候,沒有改變川普的國務院的方針。我覺得是對的,所以我比較樂觀在這個問題上。
樂觀是說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的樂觀,但是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老百姓之間長遠地來看,我還是樂觀主義。我覺得中國文化跟美國文化有些相同的地方,其它的文化不一定有,比如這個幽默感。美國和中國的幽默感,相關講這個話當然話題很大,很難一句話把它說清楚。我就把這問題說到我自己的頭上去好吧。我上大學的時候學中文念了一年級、三年級,到後來能夠說基本的日常話,到中國去、到香港去、到台灣去說話。
我的感覺是我越說中國話,越能夠在文化層面上接受中國的文化,中國人越歡迎我。你也是個人,我們跟你溝通沒有問題。但是比如說我很喜歡日本,也很喜歡日本文化,所以你不要誤解我這個話。
可是我到日本去雖然是學了點日本話,我覺得日本人聽到我的日本話,他總是要保持一種距離、一種障礙。非常客氣是非常客氣,對我非常好,客氣得不得了。所以我沒有任何抱怨,但是那個層面上,哎,你也是個人我能夠接受你,我們放下架子去說話。這種感覺沒有,或者輕薄一些。所以長遠地來說,中國的老百姓跟美國的老百姓能不能有結合有彼此喜愛、認同的可能性,我還是樂觀的,我覺得有。
主持人:那我可不可以這麼理解,就您的意思就是說,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這個人性,就是老百姓的這種人性,它最終能夠戰勝中共的這種黨文化也好,還是這種統治也好。
林培瑞:我覺得會。因為回顧中國歷史,哪個朝代是最嚴厲的、暴政的?秦代、晚隋,隋代,隋煬帝和秦始皇,蓋了長城、殺了很多人。可是畢竟是在中國歷史的長流裏頭不是主流,他們比較短暫。共產黨已經七十年已經不那麼短暫了,可以也不是長流的中國文化。
我覺得長期的中國文明,最後會超過共產黨的生命。因為共產黨這種統治,連那些我們剛才說的那種有分裂、心裏分裂的那種人裏頭,他畢竟他的理解就是不正常的。這不是一個人能夠長期生活的一個正常的這個狀況。所以早晚會超過了它,我覺得會。
主持人:是,我想沒有共產黨的話,中美關係會很好的,會很融洽地發展。希望是這樣。
林培瑞:會比現在好,好許多。是不是馬上一切問題消失呢?我們也不能太理想。
主持人:好的,那非常感謝林教授。我們今天也聊了挺長時間的了,我想這個再聊下去還是能聊很多,但是我想今天就先到這裏。非常感謝您今天來跟我們分享,您當年中國的這些經歷。
林培瑞:對,很高興。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那也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