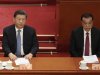去年底至今,簡中輿論場大概只有三個主題,豐縣小花梅事件是列第一位的,冬奧像是插播的臨時活動,等到烏克蘭戰爭爆發,冬奧會及其明星運動員的光環快速熄滅。即使遠程圍觀戰火時,小花梅事件仍能沖將進來,在戰爭悲劇上嫁接鐵索寒。
這是一個耐人琢磨的問題,小花梅事件為什麼能對泛知識階層造成如此大的衝擊,如此普遍地表現出PTSD的共有症狀?一個悲慘女性,蘇北村落的荒蠻,罪與罰的狡猾與公憤,官家面貌與官僚主義等,在別的事件中也有,可為什麼豐縣事件別具一格?
同時,這是一個轉回頭來需要討論、值得重視的問題。當民間敘事獨立成文,各種通報、發佈再也無力干涉民間文本的形成,泛知識階層闡釋並「擁有」小花梅的故事後,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這一切?以致於,過去那套有效的主流敘事機制在這件事上完全失效。
這套主流敘事機制由近年來體制內外的變動塑造而成,因應信息環境的新格局,服務於輿情應對的政務目標。在影響大眾認知上,它實際上表現為一個配套的矩陣:機關報(媒體)打頭定下基調,在社媒形成輿論氛圍,地面政務跟進穩定事件,打消影響。
從輿論的角度看,豐縣事件是一次沒有新聞機構參與的、完全由社交媒體推動的信息運動。在此一事件上,「輿論」以純粹的方式實現了對新聞的超越。這期間,也出現了陽謀與爭鋒,但最終都在近乎聖潔的公義之下,以歸於緘默的形式讓位於這股輿論的「主流」。
豐縣事件無可否認的意義,也許是挑明了這麼個事實,像是對現有的媒體建制說:在座的都是垃圾。打破或無視媒體的存在,反而獲得了視野,得到了解放。這對研究新聞與媒體的,或許是一個值得繼續掘進的課題,亦即:失去的是新聞,得到的都是解脫。
也可以說,豐縣事件在某種「無意識」中,不再糾纏於新聞到底有多少宣傳的成分(或相反),或者說,這種業界的心結對社會輿論再無絲毫價值,畢竟愧疚不等於新聞,抱愧無濟於事。如果新聞可以對受眾不忠,受眾當然有權在輿論中拋棄媒體。
在報紙的黃金年代,媒體具有體制內和體制外雙重屬性,當它監督權力時會被認為有社會力加持,當傳遞民間意見時它又被認為可通公權。這種「首鼠兩端」,一度是媒體的優勢所在。但在今天,這種腳踩兩隻船的好日子結束了,這就是媒體的重新體制化。
重新體制化後,過去那種以新聞屬性自外於宣傳功能的「標榜」,或者將宣傳意圖藏匿於新聞包裝的「機巧」,都沒有意義了。因為,無論媒體如何狗苟蠅營,人們的希望不變,就是想看到事情的「解決」——既然新聞或宣傳都無意於此,也就莫怪它們皆受冷眼。
在豐縣事件之前的劉學州事件上,因不忿於新京報的表現,輿論中很有一些為機構媒體辯護的聲音(包括舊聞評論)。但在豐縣事件上,任誰也無法再為機構媒體辯解(它們也不需要)。當然,義正嚴詞地抨擊「媒體缺席」,也包含着顯而易見的虛偽。
作為後果之一,媒體教育對大眾再無實際意義。媒介素養,如何識別宣傳,怎樣體諒新聞人苦衷,都沒有一點意思。人們不再「通過」媒體看世界,人們意識到「自己」就是那殘缺世界;既然媒介不忠用,人們沒有耐心再與之周旋。新聞人的內心戲,對人們來說屁也不是。
自從新聞自我放逐,與新聞學、新聞教育脫鈎,新聞(實際上是媒體)再一次與受眾失去了情感聯繫。這不是「霧都孤兒」的悽美故事,而是「西部世界」的機械人起義,在被媒體遮蔽了多少回後,人們從最原始的感情邊緣甦醒,掙脫媒體那百無一用的存在。
新聞或宣傳,民意或輿論,都返璞歸真,回到「信息」這一原始的起點上,重新建立/斷絕相互關係。這種關係不接受舊情愫、舊關係的調停,信息可以被壟斷一部分,但很難被以媒體/新聞的名義安穩地統治,也很難被治理的強權按照需求來鍛造。
當然,自此之後,所有以媒體名義展開的信息傳達、認知影響,要怪罪還是讚美,都與「媒體」無關,恩威雨露都是行政結出的斑駁果實。如此,討論豐縣事件在議題榜「安家落戶」,就從「新聞無為」「媒體何為」過渡到「政務若何」,不滅的議題成為衡量政務與人民關係的新指標。
政務系統曾經有過理想,比如說打造「黨政分離」「法治政府」來展示它與民眾的關係,這種嘗試也推行過,但在這種不穩定的關係中持續地釋放出麻煩來。改弦更張,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建造新模式,就成為延續至今,在方方面面都展示給人們看的龐大工程。
簡單來說,新的政民關係中,民在關係之中,但政既在關係之中,又在關係之外,還在關係之上,總體上是一個無所拘束的存在,靈活且無止境地從關係中汲取力量。這種新的政民關係,自然帶來政務官員對民眾地位及角色的新見解,以及新的安排。
對豐縣事件的處理,包括地方通報型應對方式,以及省里派出臨時行動組的方式,都是對新的政民關係的遵循。在關係之中,所以才有縣市省逐級增加的權威背書;在關係之外,才有調查過程的不公開;在關係之上,才有給出一個結論即希望平息事態的打算。
實際上,民眾早就不再以想像或虛假希望看待政民關係,而同樣是在實用主義層面論斷政務新關係。所以,就能看到兩下對話泯滅、交流困頓的現實,因為「在關係之中」不只是在等待某個答案就完事,但「之外」「之上」卻以為答案才是唯一,且相信那是唯一答案。
豐縣事件在政民新關係幾乎無障礙的運行中,稍稍政務官主導的關係模式,不僅無法隨意地取信,還會因單方面自上而下的「誤解」,將自身捲入麻煩當中——儘管這「麻煩」很輕,且以不打碎鐵飯碗為底線,但足以蠶食對新模式的自信,逐漸地積累沮喪。
在豐縣事件上,隨着議題輕鬆地突破其他議題的競爭,毫無衰減之色,也無滅失跡象,它幾乎是倔強地支持一個至今徘徊不去的問題:在這件事上,政務官們與大眾民意是不是沒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立場可言?既然沒有辯解,沉默也許就是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