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傳統媒體,這次都保持了「得體的沉默」。
我記得若干年前,曾經看過一本小說,名字和故事今天都已經忘卻了,只記得文末有這樣一段描寫:當主人公終於在社會的重壓和自身不幸的際遇的夾擊下死去後,作者寫到:他死了,而世界對這場死亡,保持着得體的沉默。
「得體的沉默」,這個形容,我當時讀出來的時候,感到一股寒氣從腳底襲來,直衝頭頂——真的恐懼莫名。
我覺得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對一場悲劇最大的不尊重,而是悲劇發生後,人們對它毫無感觸,甚至連追問一下真相的興趣和努力都沒有。這種「得體的沉默」是一個社會的恥辱、也是終將讓它喪失性命的癌症。
昨天,莆田兇案的嫌犯歐金中死了,警方公佈的說法是「畏罪自殺」。而大多數主流媒體,都只是原文轉發了這個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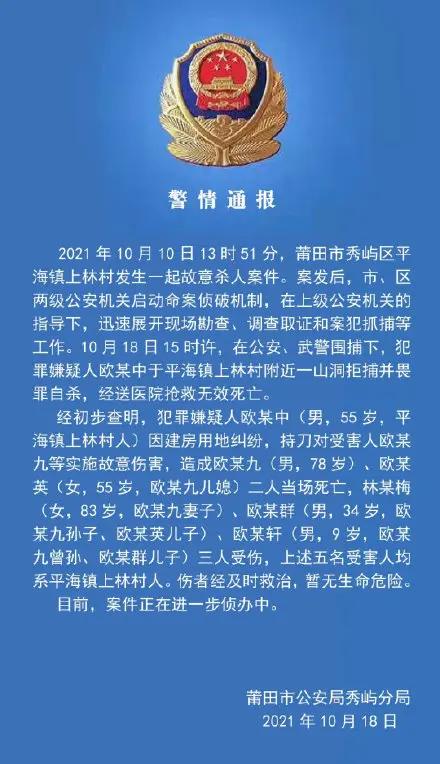
看到這種普遍的報道方式之後,我在想,歐金中這人,不管他生前遭遇了什麼、又做了什麼,他都死的很潦草——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對這場悲劇的反思,就是很潦草的。
你看,那麼多媒體,都千篇一律的成了這份簡稿的轉發機器。
眼下的我坐在寫字枱前,想對這場被公眾輿論關注了一個多星期的事件寫幾個字,卻發現自己其實什麼都寫不出來。因為對於這場案件,很多基本而關鍵信息都是模糊、眾說紛紜的:
歐金中這人,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為什麼他在已經辦好蓋房手續之後,卻又住了五年的鐵皮房?他稱自己的遭遇了村霸的阻撓,到底是不是真的?這上訴的五年中,又是什麼擋住了他的維權之路?案發前他與鄰居的糾紛又是如何激化的?
所有這些疑問,現在都沒有一個權威的解答。所以每一條關於該事件的報道下面,你都會看到對真相的不同解讀者在捉對廝殺。可以說在這起案件中,公眾陷入的是一個「無真相迷宮」當中,因為討論的基準坐標是缺失的,所以不得不進行一場蒙眼的戰爭。
而隨着歐的死亡和大眾興趣點的轉移,估計這些疑問,也不會再有得到解答之日了。
其實不僅歐金中案,遍觀這兩年的很多社會事件,你會發現有一種東西正在離這類事件遠去——這種東西叫做正規媒體的權威、深度報道。
曾幾何時,這種報道在中國還是蠻多的,孫志剛案、楊永信案、溫州動車事件,曾幾何時,每一個公眾事件之後,都會有幾篇甚至十幾篇來自主流媒體的高質量追問,這些報道促進着社會的改革,讓悲劇沒有白白髮生。

但是,我昨天晚上翻了一晚的互聯網,想找到一篇有關歐金中案的深度報道,發現一個都沒有,居然!
甚至連肯到現場採訪一下的媒體也不多。我所看到的當中,似乎只有新京報和中國新聞周刊,前者拍了一個很短的短視頻,後者寫了一個不長的稿件,且都是在兇案發生之初的,後面就都沒聲了。
直到歐金中「畏罪自殺」為止,大多數主流媒體都保持着「得體的沉默」。
當然,網上對此事的評論很多。有人說歐金中案至少給自媒體創造了幾億的點擊量。
可是再有深度的評論,也是不能彌補新聞事實的欠缺的,前兩天我曾經寫過一篇《「老實人」歐金中的生存困局,是怎樣煉成的》的文字。我看到有讀者留言批評我寫的過於「理論化」,建議我到當地實際調查之後再發言,因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我當時感覺真是哭笑不得——作為一個曾在媒體供職的前新聞人,我當然知道新聞事實的重要性,也承認「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可是,一個關鍵問題是,我有這個調查權嗎?
按照目前國家的相關規定,非公有制實體是無法採編、播發新聞的。其實連點評嚴格說來也算違規。
所以這種事情我就是去查了也沒用,作為普通受眾,只能等待正規的傳統媒體去幫我們調查真相。
但現在的傳統媒體,除了發通稿,幾乎都不理這茬事兒了。我曾工作的一家媒體早幾年就取消了深度報道部了。寫稿子之前,我還特意問了一下前同事們,得到的答案是現在那裏已經沒有能寫這種報道的記者了,想派也派不出。問大家在忙啥,答曰都忙着去拍能出「爆款」的搞笑、暖心、小知識或正能量短視頻去了。而那種東西,現在是大部分傳統媒體都在着力「轉型重點」。
我有個可能得罪人的觀感,時下中國大多數傳統媒體記者們的工作,跟散戶自媒體人們是一樣的,只不過前者有個編制而已。
傳統媒體們也許還沒有死,但已經無所謂了。
專業的媒體深度報道為什麼會消失?
一談這個問題,很多人本能的會往監管日嚴上想。可是我回憶了一下我曾經的從業經歷,得到的結論並非完全如此。
殺死深度報道的真正兇手,是來自全社會的苛責與不寬容。
從某種意義上說,深度報道絕對是媒體行當中的奢侈品。媒體需要高投入,調撥精兵強將長期追蹤一個案件,才能夠寫出一篇新聞事實和見解俱佳的文稿。
但矛盾的是,這類報道從來也是最惹麻煩的存在。因為一篇報道寫出來不可能是毫無傾向的,記者再費心調查,也只能報道事件的部分真相,不可能面面俱到。
可是當你把文字寫出來,登上報紙,產生了社會影響力,就要承受來自全社會的挑剔。會有很多人質問你「為什麼只報道一方面事實?」「你是不是立場有問題。」嚴重的時候還會給涉事記者、媒體,惹上沒完沒了的官司和麻煩。
我在傳統媒體的時候主要是寫專欄、做評論員,可是耳聞目睹,見識過不少深度報道記者因為一篇文章被人找上門來謾罵、甚至遭遇人身威脅。有個深度記者對我說的話,我印象極深:「我們這個行當都不敢做的太長,能幹三五年就是極限了,因為再幹下去,走到哪兒都會有你的仇人。」
跟我說這話的前輩,在總在他的包里常備一把便攜式防暴棍,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他不干深度記者、辭職下海很多年以後。
不僅當事方會給深度報道記者施壓,公眾對為他們呈現深度報道的媒體也不怎麼寬容。
比如國內將深度報道堅持到最後的幾個報紙包括《南方周末》《新京報》等,可是你到各個網站上去搜一下,會發現這些媒體的「黑粉」是極多的,網上總有一堆的人在咒罵這些媒體「居心叵測」、罵他們「歪屁股」、甚至是「編內公知」。而這些人找的證據,往往都是這些媒體的深度報道如何「不全面」,並最終上升到道德批判高度。
雖然付出了極大的辛苦、承受了莫大的風險,深度報道在中國卻始終是一種沒有榮譽感和安全感的工作。過去這個行業能維繫的主要原因,只是大家都讀報紙、看電視,傳統媒體當年還有比較好的收益,可以為相關記者發放對得起他們辛苦的酬勞。
可是這兩年隨着傳統媒體越來越走下坡路,「地主家也沒有餘糧」,長工們當然要餓死。於是深度報道就成了一種費力、招罵還不掙錢的行當,媒體紛紛裁撤深度報道部、相關專業記者都轉了行,深度報道的消亡成了一種必然。
我想起了一個詞:「扒糞者」。
它來源於老羅斯福總統上世紀初對深入報道社會負面新聞的記者們的嘲笑。
1906年,老羅斯福在一次演講上如此形容這些記者:「這些人拿着糞耙,目無旁視,只知道向下看;他被請求用天國王冠來與他的糞耙做交換,但他既不抬頭,也不看王冠,仍繼續清理地上的髒東西。」

老羅斯福說這話是含有對「扒糞者」記者們的道德批判的:我們的社會欣欣向榮(當時的美國確實高速發展)。你們這些記者怎麼就不能報道點光明的東西呢?
但正因為社會是在前進道路上高速奔馳的,所以需要有人來給這台機器檢修。扒糞者就是這種檢修工,他們自身也許穢物滿身,卻幫助社會維護了它的乾淨和體面。
所以記者們自豪地將這個名字據為己用。
從此,「扒糞者」就成了形容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媒體人的尊稱。在美國社會發展史上,為維護社會的正義、促進制度的完善,寫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筆。
其實在「扒糞者」出現之前,美國19世紀的著名新聞人普利策就曾說過:專業記者不必也不能保證自己寫下的內容能完全還原真相——那是上帝才能做的工作,而他們只要能保證自己寫下的信息能為讀者提供善意的幫助即可。

這段話的深意,我看很多人至今也未必明白。因為時至今日,我們的社會當中仍有大量的受眾在以「不全面」苛責新聞人,甚至把他們的個人道德品質與他們報道的新聞進行關聯——你這個記者(或你這家媒體),為什麼總盯着社會的陰暗面看?你是不是歪屁股?你是不是居心叵測?你這個xxx!
這樣無理的問責,問到最後,並不能消滅悲劇和社會的陰暗面。只能消滅那些敢於把它報道給你的「扒糞者」們。搞到最後,大家都不再做費力不討好的深度調查了,社會在一片「短視頻」「爆款文」的狂歡當中,對那些值得追問的事件,保持了麻木的無視和得體的沉默。
而今,我們正在陷入到這種麻木與沉默當中,我不知現如今再回過頭來呼籲社會善待那些「只看陰暗面」的「扒糞者」是否還來得及。我只知道,如果這種來自社會的苛責與不寬容沒有改變,當下一個歐金中死去的時候,迎接他的將仍是一片「得體的沉默」。
請善待扒糞者們,讓他們為社會去污——如果這種人還有的話。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