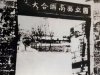南開從廢墟中站起
在中國八年抗戰史上,教育曾經寫下了被世界譽為「奇蹟」的輝煌篇章。其中大學教育最有代表性的學校是西南聯合大學,中學最有代表性的學校是重慶南開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初名為「南渝中學」),初設於1936年,為天津南開的掌門人張伯苓所建。張伯苓之所以在重慶設校,是緣於當時的華北局勢。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華北業已處於險境。張伯苓意識到局勢嚴峻,為退路計,決定於大後方的重慶設校。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了。天津南開各校遭到了日軍的瘋狂轟炸,建築幾乎全部被毀,校園成為一片焦土。為存續南開之生命,南開大學撤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中學部分師生員工撤往重慶,與「南渝中學」合併後改名為「南開中學」。
在國難當頭的艱困歲月,重慶南開中學不僅延續了南開之生命,而且發揚光大了南開之精神,也因此成為舉世公認的中華民族不屈於外侮,不甘於落後的生動例證。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特使威爾基到中國的戰時陪都重慶後,曾專程訪問南開中學並發表演說,回國後,寫了一本名為《四海一家》(One World)的書,介紹了這所中學。威爾基在演說中說:「像南開這麼好的學校,你們中國固然很少,我們美國也不多。」
於今,80年過去,威爾基當年對戰時重慶南開的評價應當說依然沒有過時。
一、清晨,升旗儀式之後,已是古稀老人的張伯苓校長嚴正表態:「咱們南開已從天津退到重慶,現在不能再退。敵人當真來,南開只有同大重慶同存同亡。」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張學良曾於是年8月在台北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廣播協會記者的專訪。採訪中,日本記者突然向張提問:「先生在年輕時受誰的影響最大?」張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張伯苓先生!」接着張回憶了早在1916年他還是一位年僅16歲的少年時,在瀋陽聆聽了張伯苓先生的一次講演所受到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應瀋陽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來到瀋陽講學。在瀋陽青年會對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講演,講題是「中國之希望」。這時張伯苓年屆40,正當壯年,他創辦的天津南開中學已譽滿全國。張伯苓的演講引發了一陣陣熱烈的掌聲,當講到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時,有一句話更是驚四座:「中國不亡有我在!」張伯苓講道:「每個人都要自強,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國就亡不了。我們必須有這麼想的氣概,不管人家怎麼說,自己要有這種信念!」這些話在東北各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就連張學良聽了後,也深深折服,從此拜張伯苓為師。
教育家張伯苓先生一生的事業是從創辦天津南開中學開始的,而創辦南開是為了實現其教育救國的夢想。
教育是國家的希望。1807年,普魯士王國慘敗於拿破崙,威廉三世國王挽救普魯士的重大舉措是設立一所新的大學。1810年,柏林大學開學,在德國最偉大的教育家洪堡兄弟領導下,很快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並由此奠定了普魯士再度復興的學術與知識的基礎。張伯苓等一批了不起的中國教育家在民族存亡危機之秋也心繫於此,並以此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追求。
張伯苓多次說起他辦教育的緣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日本人所奪走。當我到劉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迴蕩。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他多次對人們說:「悲楚和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種堅強的信念:中國想在現代世界生存,唯有賴一種能夠製造一代新國民的新教育,我決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國的事業上。」
所以,在張伯苓的詞典里,教育——南開——愛國是同義語,張伯苓其人其名本身就是一面愛國的大旗。正因為如此,日本人在發動侵華戰爭之初,就視張伯苓為抗日派,必欲除之而後快。九一八東北淪陷後,日本軍部加強了在天津的動作,試圖採用暗殺的形式除掉張伯苓。他們收買了一批漢奸到南開大學來搗亂,妄圖趁亂殺死張伯苓,都被聞訊而來的東北軍趕跑了。
1937年7月底,日軍攻佔天津,隨即下令轟炸南開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女中,三校頃刻化為一片廢墟。眼見30餘年的心血頓時化為烏有,悲憤之中,張伯苓發表了義薄雲天的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作為戰時中國一個慘痛的象徵,南開的被毀也引發了全國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同情。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約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及平津教育學術界人士蔣夢麟、胡適、梅貽琦、陶希聖等。會談中,蔣當面向張伯苓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並贈一面彩旗,其上繡有6字:「中國在,南開在。」
南開這種與生俱來的愛國情懷在西遷戰時陪都重慶後,也深深地植根到了重慶南開中學的校園之中,並且在八年抗戰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奏出了教育救國的最強音。
作為中華民族在外侮面前永不屈服精神的象徵,重慶南開也像天津南開一樣,成了日軍必欲摧毀的目標。從1938年7月開始,重慶南開中學先後多次遭到日機的轟炸,午晴堂、芝琴館、范孫樓都被震裂,損失巨大。面對敵人的大轟炸,重慶南開人處之泰然,毫不退縮。他們採取延緩開學、調整上課時間等措施,以保證教學秩序。在敵人的「疲勞轟炸」中,張伯苓校長總是立即讓人修復受損設施。有人問修復之後日機再來炸怎麼辦,張校長的回答擲地有聲:「再炸再修!」
抗戰八年中,重慶南開就是這樣在敵人的炸彈下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才。
除了堅持學習,重慶南開中學還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戰。重慶大轟炸開始後,南開師生發起了抗日救亡、募捐賑災活動。在校門外搭起帳篷,準備食品及藥品,救護受難同胞;在校內禮堂前設捐獻點,開展集體、個人兩項募捐比賽。有學生拿來抗日宣傳影片《東亞之光》在南開放映,門票收入悉數捐出。期間,學生組成了抗日下鄉宣傳隊,步行40多公里,到江北縣沙坪場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演出活動。1943—1944年,重慶南開中學學生和廣大熱血青年一樣,在民族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紛紛投筆從戎,到血與火的戰場上詮釋熾熱的愛國之心。據統計,重慶南開中學參加印緬遠征軍的學生有50多人,他們有的在軍中從事文化工作,有的隨部隊搞後勤保障,有的直接上了戰場殺敵,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做出了貢獻。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1941年12月初,湘桂戰場潰退,日軍深入貴州,重慶風聲鶴唳,謠傳又要遷都。這是抗戰以來重慶最為寒冷的一個冬天。就在驚聞獨山失守的時刻,一些身為軍政要員的學生家長準備舉家避居西昌,並為其子女向學校請假。面對此事,張伯苓極為憤慨。清晨,升旗儀式之後,已是古稀老人的張伯苓校長嚴正表態:「退學可以,請假不准!」略做停頓之後,又說:「咱們南開已從天津退到重慶,現在不能再退。敵人當真來,南開只有同大重慶同存同亡。」此時的南開,初中、高中、女生部的全體學生,齊集大操場,鴉雀無聲,強忍熱淚,在寒風中肅立。是夜,熄燈號聲之後很久,宿舍里的學生還難以入睡,他們三五成群,相互傾訴愛國憂國之心。也就在此時此刻,馬原、袁澄等幾個年僅十四五歲的初中生萌發出了編輯出版壁報《健報》的想法。他們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為名,呼喚「一切為了反攻」,「一切為了勝利」。第一期「代發刊詞」開宗明義:「過去的一年已成流水可是誰能忘記,在這一年裏中國又失去了多少錦繡江山?河南43天,失去44個城市。湖南52天,半省淪亡。廣西不滿百天,全省變為戰場。日寇甚至深入貴州腹地。因此誰能不說,一切都是次要,只有反攻才是刻不容緩!」其副刊名為《寒流》,刊載了一篇取材於史可法抗清殉國史實的「故事新編」——《梅花嶺》。就這樣,在抗戰以來重慶最寒冷的這個冬天,這些還是「不識愁滋味」的初中少年,超前滿懷「憂患意識」,超前成了憂國憂民的國家公民!
二、一位高一學生突然想到南開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學」,「日新月異」就是破舊立新。
作為教育家,張伯苓關注的始終是如何通過教育,達到「改造國民」,從而實現「教育救國」的目的這一核心問題,也就是培養什麼人的問題。這既是他興辦教育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是他的教育理想之所在。而這一點,則集中體現在他為南開所確立的校訓上。
1934年,在南開創辦三十周年校慶紀念會上,張伯苓先生正式宣佈「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為南開校訓。關於「允公允能」,他解釋說,「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己,算不得什麼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集體主義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設現代化國家,要有現代化的科學才能。而南開學校的教育目的,就在於培養具有現代化才能的學生,不僅要求具備現代化的理論才能,並且要具有實際工作的能力。」
「公」「能」教育可以說是熔社會公德教育與個人能力教育於一體的現代公民教育。前者是一種公民品格的培養,而後者則是一種個人能力的鍛煉。其根本宗旨是:不僅要求受教育者能充實個體,同時還進一步要求個體的充實不單為己用,更應該為公為國,為人群服務。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是天津南開的校訓,也是重慶南開的校訓。重慶南開的校歌,也沿用了天津南開的校歌: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
汲汲駸駸,月異日新,發煌我前途無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純,以鑄以陶,文質彬彬
大江之濱,嘉陵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
校歌僅僅在後面一段詠唱時,宣示了其新生命的地點在長江與嘉陵江的邊上。這一集中體現了南開精神的校訓、校歌同樣也在重慶南開中學落地生根。
1945年抗戰勝利的那個秋天,重慶南開舉行了一次作文比賽,題目為「論述南開精神」。一位高一學生突然想到南開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學」,「日新月異」就是破舊立新,他「越想越激動,字跡潦草,墨跡斑斑,卷面骯髒」,結果竟獲得了第二名。一絲不苟的喻傳鑒主任親自找他談話:「你知道你寫得這樣亂為什麼還得第二名嗎?就因為你論述南開精神有獨到之處……現在的中國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學啊!」
學生對體現了南開精神的校訓能夠有這樣深刻的理解,本身就是對學校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且卓有成效的公民教育的一個最生動的證明。
抗戰時期的重慶南開中學,是真正以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識的國民為目的。公民教育作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民主、開放、多元、自由。所以,重慶南開首先是自由的,這種自由,不僅表現為南開的學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更表現為外界也將這裏視為一片自由的沃土。學校在學生心中播下的絕非只是知識的種子,更重要的是植入了最樸素的科學民主精神。抗戰時期的重慶南開中學是私立學校,為了學校的發展,張伯苓向許多持不同政見的士紳名流募捐,他們多為張校長辦教育的情懷所折服,紛紛解囊相助。蔣介石也對南開青睞有加,特批了5萬大洋撥款建校。但學校從未因此而出賣自己的辦學品格。作為抗戰時的最高領袖蔣介石曾多次到學校看望師生,學校也從未組織過師生員工搞什麼列隊歡迎、山呼萬歲等;而後來重慶南開中學的許多學生都成了共產黨員,南開人也並未就此感到不安。因為只要學生愛國,選擇怎樣的黨派完全是他們的自由。學生中也有不少國民黨政要的子弟,但他們在校內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們同平民家庭出身的學生一樣地穿校服,一樣地吃食堂,也沒有人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學面前逞威耍橫,不同背景的學生在南開中學仍然可以自由交往。經濟學家茅于軾曾在南開就讀,他回憶說:「一些大官的子女當時我們也並不知道,到了畢業以後才慢慢聽別人說起。學校從不趨炎附勢,校園裏絕對沒有任何特權的氣氛。」學校自編的國文教材,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東西以及蔣介石喜歡的王陽明的文章,也一篇也未能入選。在學校看來,學府的尊嚴和學術的自由決不能為權勢所左右。
在這裏,時事辯論賽也是家常便飯,而且視野宏大和高遠。「戰爭促進抑或毀滅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實現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誰勝?」等等辯論題讓人難忘。一次,全校男女生兩部舉辦辯論賽,題目本來是一件生活瑣事,張伯苓校長散步時偶然看見海報,說沒出息,什麼時候了,還淨辯論這些小事。當夜,學生們就把題目改成了「美國是否應該參戰?」其時,珍珠港事件尚未爆發、美國並未參戰。
結社、演出、辦壁報,也如火如荼,而且都是自發的,是他們興趣、才華、理想的萌動。這使他們在實踐中學會了獨立思考,學會了表達,提升了他們青春的生命質量。校園廣場上到處張貼着他們自辦的壁報,內容五花八門,既有探討人生的,也有關心國事的,《健報》《公能報》《曦報》《晨鐘報》《野猿報》以及以「民間報紙」(區別於班報、校報)自許的《翔翎報》等競相爭妍。他們甚至通過各種渠道,親自登門採訪邵力子等政要。茅于軾在這裏讀高三時,也曾和幾個同學一起辦過一個名為「旁觀者」的英文牆報。這其中,以精彩紛呈的手抄壁報,最能凸現南開學子「允公允能」的公民意識和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校園中,校方為各社團設置的璧報欄,遙對校門,成一字形排列,佇立在一株株梧桐下,俯視運動場,背倚歌樂山,連接了忠恕圖書館與午晴堂。因為本身確有亮點,並且『天時地利人和』兼具,所以影響越出南開校園之外,甚至戰時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些主要代表,每次出入南開,只要時間允許,往往會在璧報欄前停步。比如,在1946年4月8日重慶版《世界日報》的『教育界』專欄,就留存了「3月31日午後,周恩來夫婦悄然來校,在梧桐樹下觀閱各種璧報,見夫人指某報載延安跳舞盛會消息一則,二人相盼」的歷史鏡頭。
前面提到的以評說國事為主的《健報》,就發表過許多專業水準的「本報專訊」。譬如抨擊孔祥熙家族的《三億美金究竟誰人所有?》,報道巨奸周佛海由滬飛渝的《大漢奸!殺嘸?赦!》。當年《健報》的主創者馬平在《前塵似夢話〈健報〉》中,還專門提到學校的璧報審查制度:「當時負有審查璧報之責的訓育主任——綽號『官腔』、南開大學政治系畢業、頗有口才的關性天先生,懷疑《健報》是否幕後有人『捉刀』,在找我『個別談話』之中,幾次要我『謹防交友不慎』了。」「雖然當時《健報》夥伴,除了對中共黨報《新華日報》並無偏見、甚至還是長期訂戶之外,對於南開是否已有中共組織,也和教師之中誰是國民黨員一樣,同樣都還沒有興趣;對國共雙方都是力求保持一定距離。關某於1945年秋在一次『時事報告』里,以《健報》某期所載邵力子氏關於國共談話為例,斷言:『只有小孩子才會相信,邵力子對他們說心裏話。』我們在題為《敬質關XX先生》的『社評』里,就在關XX姓氏之前,加上一個既不必要、且當時缺乏憑據的定語:『國特分子』,而且未經訓育處蓋章就發了出去。對此,這位訓育主任大人自然很難平靜。只是因為南開素有民主傳統,同時關某其人也還需要表現一些『民主』風度,所以表示只要『下不為例』,可以免予『警告』處分」。
一位女校友回憶說:「對南開,我是從比較中來認識的。在此之前,我上過兩個中學,其中在江津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附中讀過四年。但一進南開,就感到正規、朝氣蓬勃和清新。本來國立學校是靠政府撥款,公費吃飯,伙食標準就很低,再經管理人員甚至工友貪污就更糟糕了。可在南開一年沒有傳聞過貪污的事,而是在一種清正廉潔的風氣中培養學生的公能精神。」「我因為窮,即使保送我也很難上大學,同學們知道了就主動陪同我到訓導主任關性天家反映困難,關答應在保送書上註明『該生家境清寒,建議給予貸金。』有了這個前提我才上了大學。」
連南開的「國特分子」關性天都有如此雅量和樂於助人,真是令今人不勝唏噓。
三、南開教育之所謂的『高貴』,指的並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無人和頤指氣使,而是對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高素質要求。
重慶南開中學自開辦之日起,就憑藉校長張伯苓的巨大聲望和其出色的教育質量,贏得了社會各階層的垂青,「得入南開,便可放心」成為當時家長們的共同心聲。1936年,初建的南渝中學所招學生不過200餘人,到1937年更名為「南開中學」後,在校學生就迅速增加至1500餘人,之後歷年均有所增長。報考重慶南開的人數則更為巨大,高峰時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之比竟達到了10:1,最高甚至高達幾十分之一,可見影響之大。當時國際友人有來渝參觀戰時教育者,南開也是必到之處。
重慶南開中學現在科學館中的牆上掛有三十多位曾經就讀於該校的院士的照片,其中陪都時期的學生就有25位,如:馬杏垣、錢寧、朱光亞、郭可信、樓南泉、鄒承魯、何曼德、周光召、楊士莪等;除了理工科外,文科的學子著名的有吳敬璉、茅于軾、湯一介、張豈之、鄭必堅等;政界則有鄒家華、閻明復,等等。一所新學校,也就十幾年的時間,竟培養出了這麼多的人才,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奇蹟的產生緣於當年南開的教育精神。
南開的教育精神與工具主義截然對立,培養人始終是其堅定不移的目標。如前文所言,南開所要培育的人才,要既有公心,又有能力,即校訓指出的「允公允能」的現代國家公民,說得更具體一些,這種全力服務於社會的現代國家公民,要有完善的人格,科學的思想,健全的體魄,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法治的素養。而這一目標並非空洞的口號和說教,而是體現在重慶南開的各科教學、校園生活、學校管理等各個方面,特別是集中體現在那些冰清玉潔才華卓著的教師身上。在這方面,南開國文教師孟志蓀最具代表性。據當年學子回憶,孟先生的授課特點,一是不偏重於課文詮釋和講解,而是以淵博的知識旁徵博引。講文學可以從曹雪芹講到莎士比亞、狄更斯、莫泊桑;講先秦諸子孟荀墨莊四家,其精神品格、哲學思想無所不涉,引證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學生體會這樣上課可以觸類旁通。二是課文講授基於自己的研究而不迷信權威,不循常規,不囿定見。如講「詩言志」時拎出劉邦《大風歌》。在他看來,潑皮起家的皇帝「短短三句話,就把市井無賴心靈暴露無遺。」那「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是流氓闖江湖發了橫財回老家炫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象發了不義之財的小癟三日夜坐臥不安,渴望尋得高明打手看家護院。講解屈原、司馬遷、杜甫時,則道出文學史上通常發生但也通常迴避的現象:「後世欣賞的作家,也許今天正挨窮受困,默默無聞」。這種授課,學生印象深刻、終身難忘,從中獲得多少知識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在學生心田播下了獨立思考的種子。但這並不意味着忽視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相反,以孟志蓀為代表的南開國文教師對此是極為重視的。從字詞讀寫到分析解讀能力,訓練十分嚴格。由於反覆糾正容易錯寫錯讀的字詞,諸如「土蕃」、「滑稽列傳」的「滑稽」的讀法,上過他課的學生是不會錯的。而理解能力訓練也是別有洞天。例如,指導學生自選題目,對杜詩進行小型研究,審閱後再作專門講評。通過這種過程,學生不僅增強了對作品的理解,而且獲得進行學術研究的訓練和指導。
南開的教育精神也體現在一個「嚴」字上。南開的「嚴」是有名的。從招生來看,考入南開就不容易。按說,這樣嚴格錄取的學生,順利升級直至畢業,應該不是問題。但與此相反,南開面對這樣的學生,也有嚴格的淘汰制度。據說考進來的學生要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要在三年中被淘汰。每次考試下來,都有許多人不及格,全及格的學科根本沒有。若是那門學科及格以上的人數多了,據說任課教師還要受到教導處的批評。南開還實行累計留級制。以英語為例,若一生一年級時不及格,二年級時又不及格,就新老賬一起算作兩科不及格,那就有留級的資格了;如果以後二、三年級都及格了,一年級的不及格稱作「舊欠」,便不再追究,可算做「過關」。
但在南開,嚴格的考試又不是衡量一個學生的絕對標準,教學能力也不是衡量一個老師的絕對標準,人本身始終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從屬的、次要的。在這方面,發生在物理老師魏榮爵身上的畢業考物理白卷「給分六十」的故事,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經典案例。1941年畢業的謝邦敏富有文學才華,但數、理、化成績不佳。他在畢業考時物理交了白卷,即興在卷上填了一首詞。魏榮爵評卷時也在卷上賦詩一首:「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這位學子因此得以順利畢業,並考入西南聯大法律專業,後來登上了北大講壇。這樣判卷,居然也得到了學校的認可,其中所蘊含的教育真諦發人深省。
據說,重慶南開校友中有近40%的人從事與化學有關的事業,都是由於化學老師鄭新亭的影響。鄭老師常對學生說:「科學領域內,現在不為人知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任何一個問題都夠你研究一輩子的!」幾句話便激發了學生對化學的興趣。他的課更是深入淺出,生動活潑,而且還能與日常生活緊緊聯繫在一起。校友們永遠忘不了他講醋酸鉛具有甜味的性質時所舉的例子:「在家鄉,小孩摘吃沒有熟而酸澀的梅、杏時,往往偷來母親、姐姐的鉛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變甜了。」
南開的三點半清教室制度也堪為教育經典。學校規定,每天下午三點半,所有學生都要走出課堂,參加課外活動,如果學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課被發現的話,要立刻記大過一次。課外活動主要是各種體育活動。當然,也可以利用這時間,進行其他課外活動,如歌詠活動,排戲,辦壁報,等等。這使他們養成了經常運動的習慣,增進了身體健康。南開的各種運動隊都是業餘的,隊員都不是什麼「特長生」,他們沒有任何特殊待遇。對隊員功課的要求,也和其他同學一樣,不及格的要補考,三門不及格的要留級,絕無例外,以此防止因提倡體育運動而培養出一批「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扭曲了的所謂「體育明星」。
南開對美育和鍛煉動手能力的技藝活動也一樣重視。音樂教室里,音樂教師阮北英幾乎是不分晝夜地教每個班、每個組,從中國民歌、抗戰歌曲直到西洋古典樂。20世紀80年代,當幾個60多歲的學生在80多歲的阮老師面前,流着熱淚唱起他從前教的歌時,已經幾十年沒有聽過這些歌的阮老師激動得哭了。美育也滲透到了學生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此養成學生愛美的習慣。學校要求教室和宿舍都要整潔,學生宿舍都要定期進行「考美」。美育還和許多課外活動緊密結合起來。如,組織歌詠隊,排練大合唱,演話劇,唱京戲,組織欣賞古典西洋音樂會,等等。這都是在實踐中體現美育。
對於南開的教育精神,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的體會最為深刻:「我雖然只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是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練方面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除語文、數學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公民』課上關於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決的訓練……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總之,就我的親身感受而言,南開教育之所謂的『高貴』,指的並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無人和頤指氣使,而是對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高素質要求。」
讓我們尤為感佩的是,這樣「高貴」的教育,都是在日寇飛機經常性的狂轟濫炸的艱險條件下實現的。抗戰期間,重慶南開中學有好幾次成為敵機的特定轟炸目標。尤其是在日機頻繁轟炸重慶的1939-1941年三年間,跑警報、躲避敵機轟炸幾乎成了這所民辦中學所有師生員工日常經歷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在這樣嚴酷的環境下,張伯苓硬是把這所戰時中學辦成了讓國內外都為之矚目的中學歷史名校,而且至今難以超越。
1938年12月南渝中學更名為重慶南開中學後,為了紀念在天津本部的津南,張伯苓特在重慶南開校園內仿北方四合院修建了小型的建築群,命名為津南村,為教職員工的宿舍。抗戰時期張伯苓(時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馬寅初、柳亞子等名流要人皆寓居於此,津南村也因此成為當時文化教育界的社交活動中心。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也常到津南村看望張伯苓等人。
1946年3月,張伯苓離開重慶南開中學裏的津南村去美國訪問。1948年11月,他請辭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一職,又回到了津南村,住了一年半。其間,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過津南村,請他去台灣,而他卻放不下南開,終於留了下來。1950年5月,張伯苓離開重慶南開的津南村,回到了天津。但新政權和已經被新政權接管了的南開卻沒有了他的容身之地;而離開了張伯苓的南開,當然也就不再是南開。
1951年2月,張伯苓在天津抑鬱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