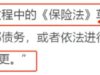中國經濟成長率造假一直都沸沸揚揚,由「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順口溜或可見一斑。
六、黨國資本主義下的中國經濟成長
大體而言,自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實施「放權讓利」政策,與蘇聯、東歐諸國由共產倒向私產,迄一九八八年成效卓著,而實際主導者是趙紫陽。由中國一九八○年代初期流傳甚廣的「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順口溜,已鮮活反應出趙紫陽在經濟事務上的能耐。
(一)趙紫陽擔綱中國經改
一九七五年趙紫陽出任中央四川省委書記,中國農村由於文革而民生凋敝,趙紫陽乃「放鬆」政策,允許農民自行種植經濟作物,恢復家庭副業和自留地,推動「包產到戶」等改革,農民種糧誘因大增,蜀糧年年豐收。趙紫陽推動農村經改獲得中共元老鄧小平等人賞識,在一九八○年代出任國務院總理,與同樣開明著稱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形成在鄧小平主導下的「胡趙體制」,大力推動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大致上,經改由趙紫陽擔綱,他將在四川實施成功的改革開放用於整體經濟。
簡言之,趙紫陽的改革就是走向「私產體制」,但由公產到私產並非一蹴可及,不論是理論、觀念的建立和傳布,或是實際上眾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攔,都是重大課題,而趙紫陽又只有中學教育程度,且活在共產體制里,更讓人懷疑其是否真有能力擔任改革的重責大任。不過,如上文所言,由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教授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在全球著名華裔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陪同下和趙紫陽對談兩小時之後的評述,可知趙紫陽的確明白中國經濟的情況及如何改進,但在共產黨最高權力的掌控下卻碰到困難,而經濟自由化有成效之後,引發對政治自由的需求,終於爆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坦克輾壓學生,血流成河,趙紫陽被削權、軟禁,中國的民主化功虧一簣,經濟改革也受阻,更慘的是,六四鎮壓引發全球公憤,各國紛紛祭出經濟制裁,使原本遭遇改革困頓的中國經濟更雪上加霜。不過,當時台灣經濟過熱,金融資產泡沫,勞力全面短缺,勞工、環保運動蓬勃發展,產業轉型急迫,中國提供充沛勞力、土地加上其他政策誘因,於是台商如潮水般流向中國。我在一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發表的〈為一絲希望而寫〉這篇文章,這樣寫着:
「這幾年,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我們的前途有着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麼都沒有;我們步向天堂,我們走向地獄。』時常被朋友們朗誦著。兩年前,強人時代結束時,一般人是滿懷希望期待最好時代的來臨,然而,一晃眼,兩年消逝了,我們的社會卻變化着令人痛心疾首,投機、貪婪無所不在,治安敗壞,暴力事件無日無之。於是,原本意氣風發者沉寂了,滿懷希望者失望了,自我放逐者增加了,整裝出走者也絡繹於途了。
記得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香港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張五常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就叫做『為一絲希望而寫』,他是中國實施經改五年之後,當一些實地考察過中國的人士都對其前景極度灰心失意時所寫的,他說:『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看。……我沒理由懷疑中國大陸的主要執政者需要大事改革的誠意,……。但我認為這些執政者過於着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見,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缺乏認識。我也認為幹部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既得權力;在半開放、半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就變成官商。……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刻,要寫一些建設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對開放拍手,見到走向歪路,就站起來大聲疾呼。『不樂觀,從何建議?』他又說:『當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議的會被接受,也絕不相信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可以改進社會。……二百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中國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張教授寫的是中國,但拿之來看今天的台灣,也同樣適用,雖然我不具有張教授那般深厚的經濟學理功力,也沒有他的遠見,但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關切之情應該遠甚於張教授之於中國的,何況台灣的條件又遠優於中國,我當然更加急切的對台灣有所盼望,而『不樂觀,從何建議?』……。
……不可否認的,台灣人民的福祉還是寄託於經濟進步,而台灣之能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靠的也是經濟發展;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未來還更應是如此。那麼,經濟發展靠的是什麼?是產業的發展和其結構的不斷演變,經由生產力的持續提升,人民的就業和所得也都增加了。產業演進雖由農業到工業及服務業,而在比例上服務業終會佔上風,但基本的生產事業仍然是靈魂,雖然其產值和就業之比重會隨經濟的演進而下降,但絕對值還是會持續上升,而且生產方式也由勞動密集趨向資本和技術密集。這樣子的演進既不會有產業空洞化,也不會有失業的出現。當然,不求上進業者是會被淘汰出局,或是向外移動的。
考諸台灣的發展過程,的確符合此種情況,而迄一九八七年明顯出現的『勞工短缺』及『外籍勞工』現象,更印證了這種演進結果。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年來,『表面上』勞工、環保運動蓬勃發展,自力救濟層出不窮,導致社會脫序,加上眾多民眾追求金錢遊戲,人心受到腐蝕,社會風氣敗壞。此外,更因為海防疏漏導致黑槍泛濫,以及警力素質低落和力量的誤用,於是治安快速惡化了。
在人人自危,連一般人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嚴重的威脅時,你想,必須投下巨資的業者豈不更為憂心?何況已到必須從事投資回收期較長、風險性較高事業之際,怎能不會躊躇不前呢?這個時候,如果別的地區也開始發展經濟,又提供更優惠的條件時,原先在台灣必須轉型的業者哪裏不會趨之若鶩呢?事也真巧,這幾年世界各地掀起一片開放熱潮,所以,在台灣內部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配合下,台灣的業者就大批的外流了。」
(二)台商西進填補中國的投資
雖然到中國投資的風險大,但生產成本極低和人力、土地資源的致命吸引力,讓台商蜂擁西進,而台灣內部的「產業空洞化」憂慮普遍瀰漫。就在外力(特別是台商)挹注下,中國並且拷貝台灣經濟奇蹟的發展方式,以加工出口特區的方式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快速成長起來。
除了台商大舉西進的幫忙外,值得再強調的是,一九九二年「法輪大法」開始在中國洪傳,中國人民爭先恐後地學練,數年間人數竟上億,修煉者凡事向內找並將所從事的工作努力做到最好,實現「真善忍」,化戾氣為祥和,也將下崗者所可能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化解。
中國經濟成長率造假一直都沸沸揚揚,由「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順口溜或可見一斑,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全球經濟一片淒涼,唯獨中國一枝獨秀地平均每年維持百分之七的成長率,但Thomas Rawski教授在二○○一年為文質疑。中共官方公佈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的累積實質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五,Rawski認為有高估之嫌,他比較了這段期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就業,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的趨勢,並參考日本、台灣、韓國,以及中國本身過去發展的模式,認為中國這段期間的實質經濟成長率,應該是介於百分之零點四到百分之十一點四之間。其實,中共總理李克強自己就有所謂的「李克強指數」(先是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新增銀行貸款;二○一五年又改為社會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三項),看來他也並不相信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呢!
關於GDP及經濟成長率的造假,並非中共獨有,英國經濟學家黛安‧柯爾(Diane Coyle)在二○一四年出版的《GDP的多情簡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一書中,一開頭〈引言〉就說了個真實故事:二○一○年下半年,安德烈亞斯‧耶奧爾耶歐(Andreas Georgiou)從國際貨幣基金(IMF)和歐盟空降,出任新成立的希臘官方統計局(Elstat)局長,幾星期後,他的電子郵件遭到駭客攻擊,幾個月後,新近遭到裁員的舊統計局理事指控他違反希臘國家利益。檢方後來在造成希臘人意見嚴重分歧的一個案子裏,指控他玩忽職守,偽造官方資料等重罪。耶奧爾耶歐的罪名是:試圖提出與希臘經濟有關的精確統計。特別是在統計官員承政客之命,粉飾統計數字幾十年後,他的做法真是可能替自己招來牢獄之災。這個案子關係重大,因為歐盟是否撥付紓困資金,救援希臘政府,防止希臘經濟崩潰,取決於希臘是否達成刪減政府支出與借貸的目標。該目標是以預算赤字GDP的比率表示。
耶奧爾耶歐獲得任命前不久,歐盟執行委員會公佈的調查報告指出,希臘已經篡改數字多年。這一年稍早,希臘國家統計服務局(新統計局的前身)局長在多少有點絕望之餘,跟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員聯絡,「宣稱官方干預數字的提供」。這份報告斷定,希臘多次誤報統計數字。就是懷疑希臘提供的數字造假,IMF和歐盟執委會要借給希臘紓困基金時,才派任耶奧爾耶歐創建新的統計機構,作為條件之一。耶奧爾耶歐遭到背叛國家利益的指控後說:「我因為不做假賬,而遭到起訴。」
連希臘這種自由民主先進國都會假造GDP數字,中共這個統計技術落後和後進發展的國家的統計數字之可信度就不用多說了。不過,雖然數字造假嚴重,但中國經改開小門讓經濟自由,其經濟會快速成長卻是毋庸置疑的。
(三)中國經濟成長速度
在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共根據「鐵飯碗」的原則運作,領導階層不承諾高成長,就業或機會,而是承諾足夠的糧食和生活基本需求。集體農場奴工和中央計劃便足以履行這些承諾,但也只能如此。穩定是目標,成長只是難以企及的理想。
自一九七八年底開始,鄧小平打破「鐵飯碗」,以追求成長的經濟取代。承諾人民自求多福的機會,不再保證糧食和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當時的經濟完全稱不上自由市場而且共產黨也沒放鬆管制。不過,國內企業和外國買家總算可以利用廉價勞工和進口技術,在種類繁多的可貿易製造業產品上創造比較利益或比較優勢。
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就這樣創造出來,中國的GDP從一九七九年的二、六三○億美元,到一九九○年增為四、○四○億美元,迄二○○○年再提高為一點二兆美元,到二○一一年更攀升至七點二兆美元,在三十年間增加了二十七倍,以此數字來看,成績着實十分驚人。依此趨勢,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GDP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強權,也將恢復久遠之前的明朝時代之地位。
不過,推論很少能正確指引未來,這樣的預測看看聽聽就好。就各地區的發展經驗,從未發展開始,就像從無到有,亦即基期很低,由這種成長過程可以得知,中國的高經濟成長完全稱不上奇蹟。如果以像新加坡、台灣和日本採取的合理政策取代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國的高經濟成長可能提前幾十年發生。但由一些分析和檢驗,已讓許多人質疑,中國是否能繼續以飛快的速度成長。
GDP可以化約成平均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力的乘積,其成長(即經濟成長)動態過程,很容易隨着生產因素的使用和耗竭而改變,不論是變好或變壞。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敎授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九九四年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亞洲經濟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中,就明白指出,共產國家成長快速系奠基於生產要素投入的擴增,而非生產力的提升或技術進步。該文因預測中國經濟成長將趨緩而備受批評,但後來證明是先見之明。
克魯曼就是以「勞動力和生產力的增加來促進經濟成長」這個根本原則來推論:如果勞動力增加停滯、生產力也維持不變,GDP也將不變,經濟也就沒有成長。勞動力的增加系由人口結構和教育來驅動,而生產力則由資本和技術來驅動。
一九八○年,中國經濟擁有充沛的勞動力和外國資金的流入,其結果不難預測。勞動力有賴從提高識字率出發的教育,以及更高階的科技和職業技術的發展來提升素質。中國在一九八○年的農民超過五億,農民不可能在一夕之間轉為工廠工人,需要住宅和運輸基礎設施之配合,這需要時間,而這種過程在一九八○年已經啟動。
勞工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湧入城市,資本也動員起來,因而勞動生產力提升。資金來自外國私人投資(台商扮要角)、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以及中國的國內儲蓄,資金很快被轉成機器設備、廠房和基礎設施。
克魯曼指出,勞動和資本這兩種生產因素的投入模式是兩面刃。當這些因素很充沛時,成長可能很快,但不足時會發生什麼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就是當勞動和資本投入減緩時,成長也同步減緩。克魯曼的分析對學界和政策制訂者來說是常識,但美國華爾街的啦啦隊和媒體所知不多。那些認定久遠的未來仍會快速成長的推測,忽略了生產因素終究會耗費、減緩。
舉例來說,五個工人以手工組裝產品,可以製造一個特定的產量。如果有五個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農民,加入該工廠工作,並用同樣的手工組裝技術,那麼產量將加倍。若廠商買進機器,以自動組裝取代手工組裝,而後訓練工人操作機器,如果每部機器的產量是手工組裝的兩倍,而每個工人都有一部機器,產量將再增加一倍。在此例中,工廠的產品量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先是勞動力倍增,而後是自動化生產再增一倍。這不是奇蹟,而是簡單明了的勞動力和生產力擴增的過程。
不過,此過程有其極限,到最後,由農村來的新工人將不再有,即使有新工人,利用資本的能力將受到實體或財務上的限制。如果每個工人都有一部機器,而同一時間只能操作一部機器,此時再增加機器也無法增加生產。經濟發展比這個例子複雜多多,有許多因素會影響成長的過程,但減少投入會導致成長減緩的基本原因,卻是無法規避的。
投資銀行家瑞卡茲(James Rickards)在二○一四年出版的《下一波全球貨幣大崩潰》(The Death of Money: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書中,就用這個理論以專章來剖析中國的經濟成長。他認為到二○一四年中國經濟已到停滯階段,雖不表示成長會停止,但會減速到一個可以持久穩定的水準。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實施一胎化政策,直到不久前還鼓勵墮胎和殺女嬰,以致陷入人口陷阱。中國的人口成長從三十五年前開始減緩,影響了現今的成年勞動力比率,如IMF的報告所言:「中國正面臨人口結構的大轉變,將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前景造成深遠影響。在幾年內,工作年齡人口將達歷史高峰,然後急劇下滑。年齡介於二十至三十九歲的工作年齡人口核心,已開始萎縮。在此情況下,龐大低成本勞工的供應,也就是中國成長模式的主要引擎,將不復見,並可能對中國內外造成極深遠的影響。」
當勞動力趨於停滯後,技術將成為推動成長的唯一驅力。美國也面對人口結構的不利情勢,主因是出生率下降,但美國勞動力仍以每年百分之一點五的速度增加,部分歸功於移民,而且美國有科技優勢作為加速成長的潛力。中共雖然模仿既有科技上很成功,但尚未證明有能力發明新技術。勞動力和科技是促進成長的雙引擎,在中國都早已開始減速,而且報酬遞減也早就出現。
不過,中共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每年中國經濟仍以超過百分之七的速度成長(二0一六年第二季己降至6.7%),應如何解釋?除了懷疑數字造假外,瑞卡茲由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面剖析。根據凱因斯所得恆等式,GDP=C+I+G+X-M,C為消費,I為投資,G為政府支出,X為出口,M為進口,(X-M)即為淨出口。一般都由這些因素的變動來看GDP的增長。當中國的投入因素報酬遞減時,這些因素如何增加?瑞卡茲認為得靠槓桿債務和一點欺騙。
由中國的GDP組成因素和美國GDP組成因素比較可看出端倪。美國的消費(C)通常占GDP高達百分之七十一,而中國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不及美國的一半;投資(I)通常佔美國GDP約百分之十三,而中國則高達百分之四十八;在淨出口(X-M)方面,其為中國的GDP增加約四個百分點,美國恰恰相反,淨出口為負值,不但對GDP沒貢獻,反將GDP拉低四個百分點。簡言之,美國的經濟是消費驅動(或者應該說,經濟成長大部分作為消費,提升生活福祉),中國則是投資驅動,且是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
原本投資是促進經濟成長的好方法,具有雙重效果,一是投資本身就是GDP的組成因素,其增加GDP也增加,二是投資可提升未來的生產力,當然可促進GDP成長。可是,此種投資驅動得看是自動或是強制性的,也就是得看投資是否真的能提高生產力,或者徒然浪費的不良投資。遺憾的是,中國往往是政府驅動的公共建設或基礎建設,或者是盲目的房地產炒作投資,都是耗用或浪費資源。更糟的是,這些投資是靠無法償付的舉債來支應。浪費的資本加上倒債潮,讓中國經濟成為一個即將破滅的大泡沫。
(四)中國的投資陷阱(本段引用瑞卡茲的分析)
瑞卡茲指出,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中國不良投資,已在中國文明興衰史上寫下新篇章,新的主題是中國世襲財閥體制的崛起。新財閥不同於舊時代的軍閥,但同樣都是一心追求私利而無視國家利益。新財閥以賄賂、貪腐和威嚇橫行無阻,他們是中國成長模式和所謂中國經濟奇蹟的毒瘤。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接掌政權後,中國所有企業都歸國營,直到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底推行放權讓利經改。接下來的十年,中國的國營企業有三種走向,一是被關閉或併入更大的國企以提高效率,二是被私有化,變成上市公司,三是仍然保持國有且愈來愈強大,成為特定部門的國家代表企業。
這些超級國有企業中最知名的有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石油化工,以及中國電信集團。共有超過一百家這種巨大的政府企業,由中共的政府管理,二○一○年,十家最賺錢的國營企業總淨利超過五百億美元,這些超級企業被組成十六個超大計劃,以便提升中國的科技和創新,計劃範圍涵蓋寬頻無線、石油和天然氣探勘,以及大型飛機製造。
不論走向哪條路的國企,貪腐和裙帶資本主義存在各個環節。被私有化的國企,其經理人都獲得許多好處,包括股票上市前的配股、私有化後擔任公司的主管。對仍保持國企的來說,貪腐的機會更直接,董事會成品與服務訂單。結果是:一個緊密交織的政府官員、太子黨和私有化企業經理人構成的網絡,坐享中國經濟成長帶來的財富。這些菁英變成寄生蟲階級,從原本能健康、正常成長的體制吸取養分以自肥。
寄生蟲菁英的興起和不良投資的盛行息息相關。IMF和其他國際機構都呼籲中國經濟必須從投資轉向消費,但這與菁英的私利衝突,這些菁英偏愛基礎建設,改革將阻礙利益流向他們的鋼鐵、鋁和其他重工業。
一些基礎建設計劃的例子可以證明「浪費」是司空見慣的。南京是中國的大都市,人口近七百萬,它是歷史上最重要都市之一,是數個朝代和太平天國的首都。孫中山和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年間也定都於此。南京和其他中國城市一樣,都有污染和成長失控帶來的問題,但它的環境相對宜人,有許多公園、博物館和十九世紀末帝制時代留下來的廣闊林蔭大道。南京位於北京—上海高速鐵路幹線上,交通便捷,它是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政經和教育中心之一。
緊鄰南京南方的江寧區,興建七個新城市,以高速公路和地下捷運系統連結。每個城市都各有摩天高樓群、豪華購物中心、五星級飯店、人造湖、高爾夫球場、休閒中心,以及住宅和科學措施。整個都會群的北邊是高鐵南京南站,南邊有一座新蓋機場。訪客對計劃的規模、已完工階段的品質,以及計劃進行的速度,都讚嘆有加,但參訪者都感到納悶,所有壯觀的設施里都渺無人跡。省級官員和計劃經理人都很樂於陪伴有興趣的團體參觀新城市、解說發展的潛力。一座實驗室說是將來中國無線寬頻科技未來的希望,另一座摩天大樓被生動地描述為明日中國另類資產管理業的孕育場,另一棟未完成的飯店將可接受世界級會議的訂位,全球各地重量級人物將在此發表演說。
不過,參訪者一眼望去是綿延數里的泥淖地,處處可見鋼筋水泥基座,準備興建數十座商場、摩天大樓和旅館。七座新城市的景象已夠嚇人了,但參訪者這才想起,南京只是中國各地興建這類超大規模城市群的地區之一。中共已在全球博得比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營建專家美譽。
中共高鐵南京南站並不空蕩,但它同樣顯示了中共舉債發展基礎建設的做法。二○○九年,面對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蕭條,中共推動四兆人民幣(相當於六千億美元)刺激方案,主要用於基礎建設的投資。推行四年後,成果是處處可見像北京—上海高鐵和南京南站這樣的計劃。中共官員反駁產能過剩的批評,他們辯說是為長期發展興建高品質的基礎設施,即使要花五到十年才能充分利用產能,這種投資也值回票價。這是推托之詞。這些建設或建築就是所謂的「蚊子館」,絕大多數都荒廢掉或利用度極低。
鬼城處處的中國-產能過剩
中國內蒙耗資人民幣五十多億打造的鄂爾多斯,是最知名的鬼城,鄂爾多斯的意思是「眾多的宮殿」,它的面積三十二平方公里,花了五年建成,原本要成為鄂爾多斯對外炫耀的中心,奈何卻成為中國房地產泡沫的見證。宮殿內外只有偶爾出現的孤獨行人和掃街的人,看起來就像幻覺之中、恐怖襲擊之後的倖存者。沒有人住,有的只是沙子,這個鬼城連同中心的成吉思汗廣場南端的景觀湖,最後恐怕只有被黃沙吞噬的命運。中國特色的高價建築往往很短命,平均壽命只有三十年,不用沙漠吞噬,它自己都會很快消失。
鄂爾多斯在城市競爭力排名中,是全中國第一:每人平均GDP曾達一萬美元,富裕超過北京和上海。鄂爾多斯老區擠著三十萬人,政府手中有了些錢,便開始建新城。為何建造的新城沒有人氣、沒有人住呢?主因是高房價和租金太高的商鋪。即便沒人,政府仍認為新城康巴甚的未來是不可限量的,十倍於當今規模的新區二期建設早已開始。其實,同樣的供給過剩,中國到處都是,北京、上海、沿海、大陸,一幢幢商業大樓都空着,全國商品房面積二億平方公尺,空置率據說高達百分之六十。
鄂爾多斯等的房子沒人住,但還繼續建,在正常社會是絕對不可能的,那中國社會是不正常的囉?到底如何不正常呢?房價漲到三、四萬人民幣/平方公尺,已使房子和普通人民完全無關,連年收入十萬人民幣水準的家庭都買不起。買得起、願意買的,多是囤積居奇者,試圖以更高價格賣出的人,而買得起的完全是中央權貴階層的最新特權。
房子賣不掉又不降價,而開發商也不破產,玄機何在呢?不需降價、不需撤資,用的一定是別人的錢,並且是不需特別擔心還債的別人的錢。究竟是什麼人不怕賠錢,不急着還錢,還拚命加碼繼續建造呢?一定是把持社會公器,可以從中漁利、任意揮霍的那一幫人。
中共的政治領導人了解中國經濟充斥着浪費的基礎建設支出,但他們的政策受到許多因素掣肘。這些計劃確實能創造短期性就業,沒有政治人物願意採用流失就業的政策,即使它們能帶來有利的長期效果,畢竟政治的考量是短期的,因而長期的利益經常被忽略。
另一方面,政府投資驅動政策替掌管國有企業的太子黨、親信和黨幹部帶來暴利。建設需要的鋼鐵、水泥、重機設備、玻璃和銅等。大肆營建對這類材料與設備的生產商有利,他們的利益向來是支持不計成本或需求而進行更多的營建。中共沒有節制這類利益或導引投資到更有利方向的市場機制,有的是一個菁英寡頭階級堅持其利益凌駕國家之上。政治菁英挺身對抗經濟菁英的能力有限,兩類菁英其實交錯複雜,他們透過交叉所有權、家庭關係、門面公司和名義股東的方式,形成錯綜複雜的利益網絡。
影子金融
中共基礎建設的背後,是一個更危險的銀行業結構,為過度建設提供融資。中國的銀行業只是全局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包括一個影子銀行體系,背負龐大的不良資產和隱藏債務,大到足以危及中國銀行業的穩定,導致能震撼全球的金融恐慌。這個體系的透明度低到連中國銀行監管當局也不知道風險有多大和多集中,這可能使恐慌一旦發生更難阻止。
中共的影子銀行有三個構成要素:一是地方政府債券,二是信託產品,三是財富管理產品。中共的市級和省級政府不能發行債券,但地方政府利用保證、合約和應付賬款戶等方式來運用財務槓桿,中共的信託產品和財富管理產品是西方結構式金融的變形。中國人的儲蓄很高,這是基於理性的考量,因為缺少社會安全網、健保醫療、失能保險和退休收入。過去中國人依賴大家庭和養兒防老,但一胎化政策已侵蝕該社會支柱,現在年老的中國夫妻發現必須自求多福多儲蓄。
西方的儲蓄者一樣,中國人也求高報酬。中共的銀行提供極低的利率,這種金融壓迫和美國及其他各國的做法很像,使中國的儲蓄者很容易被高收益報酬吸引。金融管制讓中國人無法購買外國金融商品,而國內股市波動激烈,中共的債券市場又尚未成熟,於是中國儲蓄者就受到房地產和結構式金融商品的吸引。
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特別是公寓住宅,但並非每個儲蓄者都有條件參與這個市場。銀行業者為儲蓄者設計信託商品和理財產品,理財產品是共同集資或基金,讓眾多投資人可以買小單位、集資者再以累積的資金投資在高收益資產。可以想見的是,這些資產包括抵押貸款產品、房地產和公司債。中國的理財產品不受法律規範,因而這些產品就像西方最糟的金融產品。理財產品由銀行發售,但相關的資產和債務並不列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因而銀行業得以宣稱財務健全,但實際上它們的財務是建立在倒金字塔式的高風險債務上。投資人受到理財商品高收益率的吸引,他們認為有銀行支持,理財商品就像有存款保險一樣安全,其實高收益率和本金的保護都是虛幻的。
投資在理財商品的錢被用來融資基礎建設和房地產泡沫,這和信用緊縮措施之前銀行業利用資金的方法相同。這些計劃創造出的現金流不夠用來支付給理財商品投資人的收益。理財商品的到期日往往是短期的,而它們投資的計劃卻是長期的。結果是資產和負債的不匹配,可能導致投資人在恐慌時拒絕展延到期的理財商品。這就是二○○八年造成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倒閉的原因。
出售理財商品的銀行業,因應資產違約和到期日不匹配問題的方法是,發售新理財商品。而後新理財商品被用來以高估的價格收購舊理財的壞資產,以便舊理財商品到期時可被贖回。這是一個巨大規模的龐氏騙局。據估計,二○一三年存在的理財商品有兩萬種,遠多於二○○七年的七百種,二O一二年上半年的理財商品銷售估計募了近二兆美元。
龐氏騙局的崩潰是遲早的事,而影子銀行支撐的中國房地產和基礎建設泡沫也一樣。崩潰將從特定的計劃展延失敗開始,或與特定計劃有關的貪瀆被揭露。崩潰的具體觸發時機不重要,因為必然會發生,而一旦出現,不靠政府控制或紓困將一發不可收拾。只要一出現崩盤跡象,投資人將大排長龍贖回權證,銀行將支付排在最前頭的投資人,隨着人龍愈來愈長,銀行將宣佈停止贖回,絕大多數人將空留一文不值的證券,投資人會說銀行曾擔保可拿回本金,銀行則矢口否認。然後銀行開始出現擠兌,主管當局宣佈關閉部分銀行。社會動亂將發生,共產黨的夢魘—太平天國或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歷史重演,將為時不遠矣!
雖然中共龐大的外匯存底和IMF金援有可能清理金融爛攤,也可能有足夠資源鎮壓不滿,但信心遭受打擊將大到無以名狀。而且弔詭的是,一旦金融崩潰,儲蓄會增加而非減少,因為個人需存更多錢來補損失;股市將重挫,因投資人得變賣流動資產以補現在不流動的理財商品造成的影響。對信心和成長的傷害將不限於中國,還將擴及全球。(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