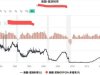《永不消逝的電波》柳尼娜(陸麗珠飾)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紅色電影」中,以「反特」為題材的電影佔有相當地位,同時也是那時代最受觀眾歡迎的電影種類。而這類電影之所以受歡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其中往往有那種以女特務身份出現的人物形象。這種女特務,雖然是「反面人物」,雖然導演和演員極力要表現出她們心靈的兇殘和骯髒,但廣大觀眾仍然深深被她們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話:女特務是「紅色電影」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由東北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鋼鐵戰士》於1950年上映,賀高英扮演了其中的國民黨女特務,這個女特務一心想以色相引誘被俘的「我軍」張排長,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應該是49年後出現在銀幕上的第一個女特務形象。
此後,這類女特務在電影中頻繁出現。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英雄虎膽》中的阿蘭和李月桂(分別由王曉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柳尼娜(陸麗珠扮演),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別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曲曼麗(姜曼璞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寂靜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玫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虎穴追蹤》中的資麗萍(葉琳琅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鐵道衛士》中的王曼麗(葉琳琅扮演),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冰山上的來客》中的假古蘭丹姆(谷毓英扮演),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跟蹤追擊》中的徐英(紅冰扮演),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秘密圖紙》中的方麗(師偉扮演)……
這一系列女特務形象,構成了「紅色電影」中一種十分獨特的人物畫廊。當年的觀眾中,至今還有一些人對這類女特務一往情深、懷戀不已,提起來便兩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戀的情人。
在五六十年代的「紅色電影」中,有「敵方」的特務形象,也有「我方」的偵察員形象。「敵方」的特務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務能組成一種人物畫廊。而「我方」的偵察員,則往往是男性。說得更直白些,在這些電影中,「敵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潛入「我方」執行特務任務,而「我方」潛入「敵方」執行特務任務者,則總是青年男性。其實,不單是電影,在那時期的小說中,情形也是如此。與其說這有現實生活做依據,毋寧說是某種微妙的心理意識使然。不僅五六十年代公開發表出版的作品中,有這種「敵女我男」的模式,「文革」期間屬於非法的手抄本小說,也總是嚴守這一不成文的規範。
有人曾指出過這一現象:「從革命者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來講,無論是革命年代的地下黨,還是和平時期的公安偵察員(正方的符號代表),為完成艱巨任務,均可憑藉談戀愛的手段打入敵人心臟(反方的符號代表),但主人翁必須是男的且不能與反方的女特務或罪犯發生實質性的性關係,而反方則往往是用放蕩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員,且被誘惑一方都會巧妙躲避或嚴詞拒絕而過美色關,否則,一旦沾染女色,不是變節投敵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偵察員絕不能施用美人計這一手段,此癥結直到現在所能見到的文字或文學作品中概莫能外。」(周京力:《長在瘡疤上的樹》,見《暗流》,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4頁。)
「紅色文藝」表現的當然是「紅色道德」。在這種「紅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現這種情況:「敵方」可對「我方」大施其美女計,但決不可對「我方」施以美男計;「我方」可對「敵方」施以美男計,但決不可對「敵方」施行美女計。這種「紅色道德」顯然並不令人陌生。「敵方」對「我方」施行美女計,其結果當然是徒勞,從「敵方」的立場來說,是偷雞不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從「我方」的立場來說,則是不但挫敗了「敵方」的陰謀詭計,還多少佔了些便宜。「我方」對「敵方」施行美男計,其結果當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勝告終的,從「敵方」的立場來說,仍然是雙倍的損失,而從「我方」立場來說,則是雙倍的收穫。
退一步說,即使「我方」對「敵方」施行美男計而未能達到最終的政治或軍事目的,也並不是純粹的失敗,至少「我方」美男在與「敵方」美女的周旋中不無收穫。這種「紅色道德」顯然認為,女性的姿色和身體,是她所從屬的陣營的利益之一部分,或者說,是她所從屬的陣營的一種特殊利益,這種利益或許比陣地、領土、金錢等更為重要。
既如此,在「敵方」女性的姿色和身體上占些便宜,也算是繳獲了一種特殊的戰利品。既然「我方」女性的姿色和身體,也是「我方」的一種特殊利益,那就決不能拿這種利益去冒險。「我方」對「敵方」施行美女計,即便最終達到了政治和軍事上的目的,也不是一種純粹的勝利,也付出了特殊的代價。當然這裏說的是電影等文藝作品中的情形,真實的情況如何,另當別論。
電影等文藝作品中反映的這種「紅色道德」,實際上不過是某種陳腐的意識、觀念披上了紅色的外衣而已。
「紅色電影」不僅僅寫「敵方」女特務以色相引誘「我方」人員,還往往讓女特務對「我方」人員「動真情」,這也是很耐人尋味的。《英雄虎膽》中的阿蘭,風情萬種、艷壓群芳,但卻對打入「敵方」內部的「我方」偵察科長曾泰一往情深。《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儀態萬方、妖冶嫵媚,但卻對打入「敵方」的「我方」偵察員王煉情深意濃。
「紅色電影」不僅讓「敵方」女特務愛上「我方」偵察員,而且往往還要強調她們是在有眾多追求者的情況下對「我方」偵察員情有獨鍾。讓女特務對「我方」偵察員「動真情」,當然意在表現「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過女特務的眼光來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價值。然而,深究起來,「紅色電影」中的這種「匠心」,這種用意,卻是與「紅色價值觀念」相衝突、相背離的。依據「紅色價值觀念」,敵人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都是毫無價值的。只有敵人的恨,能證明「革命者」的價值;「革命者」被敵人恨得越深,便越有價值。
女特務是特別危險特別可惡的敵人,那就更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無絲毫價值可言。然而,當電影以女特務的「真情」來證明「革命者」的價值時,卻又分明認可了女特務「真情」本身的價值的,因為如果女特務的「真情」本身是毫無價值的,那就非但無法證明「革命者」的價值,相反,對「革命者」只能是一種貶低、一種侮辱、一種否定,只能證明「革命者」的無價值。
人們當然可以說,女特務也是「人」,她的「真情」只是一個女性對男性的自然情感,本身是超階級、非政治的,是與她的階級屬性和政治身份無關的。然而,我們分明記得,「紅色價值觀念」根本不承認有「抽象的人」、有超階級非政治的「普遍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藉助女特務的「真情」來表現「革命者」的價值,仍然與「紅色價值觀念」相齟齬。
在「紅色電影」中,女特務可以對「我方」人員使出種種引誘手段,甚至大動真情,但「我方」人員在與女特務周旋時,卻必須嚴守分寸。那是一個禁慾的時代,那是一個女性全面男性化的時代。「我方」人員與女特務周旋雖是出於「革命需要」,但也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這危險並不在於「我方」人員是深入虎穴,而在於女特務的美麗迷人,在於女特務作為女性對於男性的性魅力。在禁慾的時代,在禁慾的道德氛圍中,女性的美麗嬌媚,某種意義上是對「革命者」最大的威脅,是瓦解「革命鬥志」、破壞「革命友誼」的最可怕力量。
「紅色電影」中,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方」偵察員,可對「敵方」女特務虛與委蛇、虛情假意,但卻絲毫不能弄假成真,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是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在身體上,「我方」偵察員可與女特務做有限的社交性的肢體接觸,如握手、跳舞等,但「佔便宜」僅限於此,並不能與女特務有任何真正私密性和性意味明顯的身體接觸。「紅色電影」往往不厭其煩地渲染女特務怎樣用身體引誘「我方」偵察員,怎樣百般忸怩、千般作態,但「我方」偵察員總是能巧妙地擺脫與拒絕,始終嚴守界線。在表現「我方」偵察員對女特務的引誘與拒絕時,還不能讓觀眾覺得他是在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覺悟」強壓欲望,而要讓觀眾覺得他對如此的美貌、如此的柔情、如此具有誘惑力的身體,壓根兒就不動心,壓根兒就沒有生理上的欲望。
相反,「我方」偵察員,對女特務的搔首弄姿、投懷送抱,只有生理上的厭惡,他需要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覺悟」所強行壓制的,是這種對女特務的厭惡。要問「我方」偵察員對女特務是否也有欲望,也可以說有,那就是立即消滅她的欲望,他同樣必須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覺悟」強行壓制着這種欲望。
在「紅色電影」中,如果「我方」偵察員在肉體和情感上失了分寸,面對女特務時動欲、動情甚至付諸行動,那就意味着變節、墮落,就是萬劫不復的醜類,就是「革命」永遠的敵人。在與女特務的周旋中,在面對女特務的百媚千嬌時,「革命者」應該時刻保持厭惡和仇恨,即便為了工作需要而對女特務甜言蜜語時,內心也應有着鋒利的殺機,他應該能夠隨時對她手起刀落。
在「紅色電影」中,與女特務形成對照的,還有那類「正面」的女性形象。這類電影所精心塑造的那種女性「英雄」,所極力歌頌的那種女性「革命者」,在性格、言行上總是非常男性化的,用通俗的話說,總是沒有丁點「女人味」的。這是「紅色價值體系」對女性的要求在文藝中的反映。
「紅色文藝」大行其道的時代,也正是「紅色價值」主宰整個社會生活的時代。在現實生活中,女性普遍男性化,在髮型、服飾上,將「女性味」減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舉止上也最大限度地與男性認同。女性身上的任何一點「女性味」,都被視作是「小資產階級情調」,都被看成是「思想意識」有問題的表現;都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可靠、不過硬;都會招致領導的批評、群眾的非議;一旦來了政治運動,還會成為批鬥的對象。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失去了「女性味」;在文藝作品裏,「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沒有絲毫「女性味」。
在那個「紅色時代」,電影中以直觀的形象出現的女特務,就成了「女性味」最合法的載體。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負面的價值,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腐朽、墮落甚至邪惡,那當然就要在女特務身上充分體現。同時,女特務要以色相引誘「我方」人員,也非有濃郁的「女性味」不可。這樣一來,仿佛人世間所有的「女性味」都集中到女特務身上。
這樣一來,女特務就成了關於女性知識的啟蒙老師。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從女特務的頭上,懂得了什麼叫「燙髮」;從女特務的唇上,懂得了什麼叫「口紅」;從女特務的眉上,懂得了什麼叫「畫眉」;從女特務的臉上,懂得了什麼叫「塗脂抹粉」;從女特務的衣着上,懂得什麼叫「旗袍」、什麼叫「胸針」、什麼叫「高跟鞋」……這樣一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從女特務的一起一坐、一顧一盼、一顰一笑、一嗔一喜中,懂得了什麼叫「儀態萬方」、「閉月羞花」、「傾城傾國」、「國色天香」……這樣一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是從電影中的女特務身上,體會到女性的魅力,並體驗到什麼叫「神魂顛倒」、什麼叫「如痴如醉」、什麼叫「心旌搖盪」……這樣一來,那個時代的小伙子,竟然是對着銀幕上的女特務情竇初開。
在那個「紅色時代」,現實生活中沒有愛情的位置,文藝作品裏更是不能從正面充分表現愛情。正面人物要麼根本沒有兩性關係,要麼這種兩性關係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藝作品裏,男女間純粹的兩性私情,都是負面的東西,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情感的表現,都意味着精神上的「不健康」。在文藝作品裏,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相互吸引的理由必須首先是政治性的,諸如思想覺悟高、生產勞動強、「毛主席著作」學得好之類。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談戀愛」時,談的也是國際風雲、國內大事和單位里的「階級鬥爭」。既然純粹的私情是與「革命者」無緣的,那就必然與「反革命者」大有緣了。
「紅色電影」中有女特務出現時,往往要讓女特務以色相引誘「我方」人員,甚而至於在不知不覺間對「我方」人員動起真情,落入自織的情網而難以自拔。無論是假戲真做,還是真情流露,女特務在與「我方」人員的交往中,都會把兩性之間純粹私情的一面充分表現。這樣一來,那個時代的青年人,是從電影上的女特務那裏,懂得了「兒女情長」的意義、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義、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義、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義、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義……這樣一來,那個時代電影中的女特務,竟鬼使神差地成了愛情和人性的啟蒙者。
今天我們看那個時代的電影,對那些女特務或許根本沒有什麼興趣。但那個時代的人們,尤其是青年人,卻被這些女特務深深吸引,這還可以從別的方面來解釋。茨威格在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中,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維也納禁欲主義的道德風尚有深刻的剖析。茨威格說,那是一個用盡種種手段「掩蓋和隱藏性愛」的時代,以致一個女子根本不可能把「褲子」這個詞說出口。然而,「凡是受到壓抑的東西,總要到處為自己尋找迂迴曲折的出路。
所以,說到底,迂腐地不給予任何關於性的啟蒙和不准許與異性無拘無束相處的那一代人,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享有高度戀愛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為只有不給予的東西才會使人產生強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東西才會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聞目睹得愈是少,在夢幻中想得愈是多;一個人的肉體接觸空氣、光線、太陽愈是少,性慾積鬱得愈是多。」茨威格的剖析,也適用於「紅色電影」在中國盛行的時代。由於「性愛」在現實生活和文藝作品中都被千方百計地隱藏,那個時代的青年人,內心深處,其實遠比今天的青年人更為色情。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的青年人對電影上的女特務有異常興趣的原因。可憐的他們,只有讓電影中的女特務陪伴着自己性愛方面的幻想與衝動。
在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扮演女特務柳尼娜的演員陸麗珠,「文革」中慘遭批鬥,原因就在於她把女特務這一角色演得太好。
一個演員,因為戲演得太好而受迫害,當然是奇聞。然而,卻又並非不可理喻。「紅色電影」中之所以需要女特務出現,本意只是為宣傳和強化「紅色價值」服務,然而,女特務們卻在客觀上構成了對「紅色價值」的挑戰,鼓勵、導引和啟發了「紅色價值」所極力要壓制、掩蓋和隱藏的東西。
當「紅色價值」的捍衛者意識到這一點時,當然要惱羞成怒,而把怨恨發泄到扮演女特務的演員身上,也在情理之中。「紅色電影」的編導們,本意是要讓女特務的各種表現引起觀眾的厭惡、仇恨,沒想到卻事與願違,女特務成了觀眾最喜愛的人物,至今還有些人像懷念初戀情人般地懷念她們。不得不說,這是「紅色價值」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