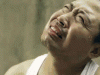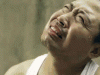幽默生物學:關於笑的學問
就在此類悲劇的基礎上,誕生了一門關於笑的科學。多少個世紀以來,從亞里斯多德到達爾文,不知有多少大思想家都希望搞清楚幽默的本質及其起源,可都僅僅停留在對各種想法的驗證水平上,最終都沒能留下任何精妙的結論。但是,對類似衛理·安德森(真名不明,醫學文獻都只提到這個假名)這樣的腦損傷病人的研究,卻因先進而複雜的活人腦組織掃描技術的應用而得到有力的支持和發展。幽默研究人員經過數十年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在他們的同事看來還覺得有點荒唐),最後把研究重點鎖定在人腦的所謂「笑迴路」上。
人類可能是唯一能笑出聲音來的動物,可實際上,喜歡笑(但笑不出聲來)的動物並不少。查爾斯·達爾文在他1872年完成的研究專著《人類與動物的情緒表達》中指出,很多種猴子在高興的時候都能發出一種重複而短促的叫聲,和人類的笑聲具有明顯的可比性。此後,更有研究發現,很多動物,甚至連沒有多少事情可以「一笑」的實驗用老鼠都有幽默感。兩年前,《腦行為研究雜誌》上刊登的一篇研究報告稱,心理學家痒痒老鼠的肋骨和肚皮時,老鼠竟出現玩耍性的咬齧反應,並發出超聲波級的吱吱聲,而且,聲波最強勁的老鼠也最渴望痒痒。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喜歡痒痒的老鼠,經過4代之後,發出吱吱聲的比率竟可達到它們的曾祖父母的2倍。
不管笑或痒痒感有沒有相應的基因,但真正的幽默感確實不是有幾根敏感的肋骨就能夠說明問題的(其背後有非常複雜的神經生理機制)。倫敦神經科學研究所神經心理學家文諾德·高爾給笑話下的定義是:可令人發笑的笑話首先是一種屬於認知水平上的一連串心理機制,然後才是基於這一串心理機制基礎上逗樂感。這個定義本身就顯得十分滑稽,但不管怎麼說,我們也該謝天謝地了,因為我們畢竟有了一個定義。按照這個定義,可把笑話分成三個熟悉的子類別:第一類是語音層次上的笑話,或叫俏皮話(類似「腦筋急轉彎」一類的笑話),如:「高爾夫球手為什麼穿兩條褲子?——因為有一條褲子破了。」第二類是超越了詞彙遊戲水平的語義層次上的笑話,如:「工程師會用什麼手段控制生育?——用他的人格。」第三類是無言笑話,如漫畫或滑稽動作。每一類笑話(從內因上看)都依賴一系列心理機制,他們在大腦中都有其相應的區域,具有多米諾骨牌效應(直至從外觀上表現出笑的行為)。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期間,科學家對這類心理機制的作用地點已經越來越清楚。神經科學家早就懷疑右腦半球是情緒、人格和非字面語言的所在地。語言機能障礙是否由於大腦右半球受傷引起的?在研究這個問題的過程中,科學家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有語言障礙的病人往往也沒有多少幽默感。雖然病人有可能因滑稽動作發笑,可要讓他們理解書面笑話,困難就大了;如果讓他們來選擇漫畫的對應文字介紹,就會「牛頭不對馬嘴」。
心理學家普拉席巴·謝米和多納爾多·斯特斯為進一步統一以前各有關研究文獻的觀點,在多倫多大學開展了一項後續性實驗。他們先用一系列語言性的及非語言性的幽默去測試對照組的反應情況,然後讓用他們認為「絕對好笑」的笑話來測試病人。病人總共21人,他們都是在成年後腦前葉才受傷的病人。研究結果(發表在 1999年的一期腦科學雜誌上)和那些笑話一樣清楚明白:大腦右前葉受傷的病人幽默感最差。這兩位心理學家在論文中寫道:「病人對簡單一點的邏輯知識並不存在什麼問題。如果讓病人為某個不是幽默一類的故事選擇一個合乎邏輯的結尾,他們的選擇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要求他們來完成某個幽默故事的結局,則病人往往喜歡沿着滑稽動作的思路來選擇一些具有出乎意料之外特點的答案,可是那些幽默故事之所以讓(正常)人發笑的結局(和他們的選擇)卻完全不同。在這些病人看來,似乎幽默的全部要素只是「出乎意料之外」。
有一個讓病人選擇具有幽默效果的答案的幽默是:鄰居來到史密斯先生家門口,問:「史密斯,你下午要用割草機嗎?」史密斯知道他的來意,於是用一種戒備式的口氣說道:「當然要用了」。研究人員給病人提供4個選擇項:
(a)鄰居一不小心,一腳踩在草耙上,耙柄差點兒打在自己臉上。
(b)鄰居說:「啊,那太好了,你既然要除草,那你家的高爾夫球棒就用不着了吧?我正好想借來用用。」
(c)鄰居說:「啊,那你用完之後能借給我嗎?」
(d)鄰居說:「鳥老是喜歡飛來吃花園裏的草籽。」
正確答案應該是(b),對照組都對了,那些受傷部位在左前葉或後腦部的病人也選對了,可右腦前葉受損的病人則往往選擇(a)。此外,後者雖然能理解某個笑話,可往往卻連微笑一下都沒有,更不用說大笑不已了。
斯特斯和謝米在總結他們的實驗結果時指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大腦右前葉是人腦最沉默的區域。可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這個區域反而可能是大腦的「票據交易所」,一切和人的自我意識有關的能力,如記憶力、邏輯推理能力、語言能力、感知能力和情緒,全都匯聚在這裏。斯特斯指出:「對幽默的理解其實是很嚴肅的問題,因為你首先需要具備理解暗示內容的能力,同時還需具有形成自我概念的能力,然後還需要把各種情緒反應正確地聯結在一起。由於大腦右前葉連接着大腦的各個區域,因此右腦前葉應具有把這些能力結合在一起的能力。」
斯特斯和謝米所研究的那些最沒有幽默感的病人,其腦前葉的受傷位置就在一個叫做「腦前葉下腹中軸皮層」的地方。最近,文諾德·高爾和雷蒙·多蘭在其發表在《自然》雜誌「神經科學版」上的相關論文中,更進一步突出了這個區域的功能。研究人員邀請14名沒有腦損傷的試驗者來聽一系列語義笑話和語音笑話(即前文提到的前兩類笑話——譯者注)。試驗者一邊聽着笑話,實驗人員則在一邊用腦功能核磁共振成像儀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以追蹤和記錄他們的大腦活動情況。結果都在意料之中:語義類幽默激發的大腦區域正是語義理解功能所在地——後顳葉;而語音類幽默激活的正是右顳葉,它是大腦處理多義詞的地方;但無論哪一類型的幽默,那個叫做腦前葉下腹中軸皮層的區域都始終處於激活狀態。高爾說:「如果你覺得那個幽默特別好笑,腦前葉下腹中軸皮層就被激活;如果你不覺得好笑,那麼這個區域就不會被激活。」而且,一個幽默越好笑,這個區域的活動強度就越大。
至此,似乎可以認為研究可以到此為止了,因為所有幽默機制在人腦中的位置都已經弄清楚了。但有時候某個很好的笑話可能會不經意地接近大腦的某個角落,然後在某個意料不到的時刻冒出來讓你發笑。洛杉磯加州大學神經外科醫生伊查克·弗萊德在其發表在《自然》雜誌的論文中,就介紹過這麼一個例子:弗萊德當時正在研究一名16歲癲癇少女的大腦,以尋找刺激其癲癇發作的發作根源,結果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只要他給病人的左前葉(說到底就是一個不足1平方英寸的區域)施加電流,那個女孩就會笑出聲來。弗萊德問女孩什麼東西那麼好笑,她竟說她眼前的一切都很好笑,不管是一張畫着馬的圖畫,還是眼前的這些醫生自己,都統統讓她感到好笑。女孩會說「你們這些人到處站着,真是笑死我了」。如果弗萊德加大電流強度,病人的笑聲就會從一般的咯咯聲發展成一陣陣的大笑和甚至狂笑。
弗萊德的結論是:笑本身就象任何好笑的幽默一樣,會在大腦中形成一個迴路。幽默成分既有身體方面的,也有情緒方面的,還有認知水平上的,這三者的任何一方面都可能把另外兩方面都激發成歇斯底里狀態。弗萊德說:「若從神經元的終極功能——運動——去深入考察整個神經系統,那麼具有複雜的喜劇功能的腦前葉下腹中軸皮層,除了能讓人產生大笑不已的行為之外,就別無選擇了。」
責任編輯: 陳柏聖 來源:譯言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09/0201/118918.html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