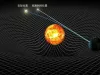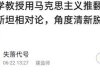撰文 喬治·默爾(Jorge Moll)
里卡多·德奧利韋拉-蘇扎(Ricardo de Oliveira-Souza)
翻譯 馮志華

1939 年8 月2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緊張氣氛令人窒息。就在這一天,愛因斯坦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了一封可能左右戰爭走向,甚至影響人類未來的信。在信中,愛因斯坦含蓄地建議羅斯福下令研製核武器,他這樣寫道:「從現在的局勢來看,我們需要提高警覺性,如有必要,政府部門應採取緊急行動。因此,我認為我有責任提醒您注意以下一些事實和建議……」
愛因斯坦的這封信涵蓋了道德決策(moral judgement)的幾個關鍵方面:道德感(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果的憂慮)、對道德困境的分析(是否向羅斯福透露一些科學證據,說明這可能導致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誕生)以及利弊權衡(如果是美國而非德國研製出了這種武器,是否會有更多的人倖免於難)。可以想像,在下筆寫信之前,愛因斯坦經歷了一個極其艱難的抉擇過程。
半個世紀後,隨着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我們已經知道,在道德判斷與倫理思考背後潛藏着怎樣的神經機理。很多研究都曾探討過這樣一些問題:在兒童尚未發育完全的大腦中,道德感是如何產生的?不同的大腦損傷如何影響道德判斷?當我們在道德層面產生憎惡感時,大腦的哪個區域在發揮作用?面對令人困惑的道德上的兩難局面,我們又如何抉擇?如果在搜尋引擎上輸入「大腦 道德」進行搜索,你將得到200 多萬條搜索結果。從這些數不勝數的文獻當中,我們對這一內涵豐富又不斷發展的領域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然而在道德判斷中,理智和情感存在怎樣的關係這一關鍵問題,我們仍知之甚少。情感如何影響我們判斷某件事情是否符合道德規範? 2007 年4 月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為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而新穎的見解。米高·柯尼希斯(Michael Koenigs)[目前在美國國立神經紊亂及卒中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der and Stroke)進行博士後階段的研究]、利亞納·楊(Liane Young,哈佛大學認知心理學專業的研究生)及其同事發現,一些大腦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區域(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縮寫為VMPFC,位於眼眶上方的前額葉皮質區域)受損的患者在面臨集體利益和少數個人利益的道德兩難選擇時,傾向於使總利益達到最大的「實用主義」選擇。該研究為這一熱議的辯題——在道德決策過程中,我們如何搖擺於事實與情感之間,又增添了幾分熱度。
理性道德
在有關道德決策的測試中,VMPFC 受損患者更傾向於犧牲局部利益以保障集體利益。
柯尼希斯、楊及其合作者一起進行了一項有關道德決策的測試。有三個組別的人群參與測試,包括由6 位患者組成的雙側VMPFC 受損組、大腦其他部位受損組以及神經系統正常的對照組。所有參與測試的受試者都將面臨四種決策情境。第一類包含一些「高衝突性」(這裏的衝突性是指道德選擇困境)和充滿個人情感的道德決策情境,比如一輛火車正沿軌道飛馳而來,這時將一個陌生的胖子推倒在鐵軌上(這麼做將導致這位陌生人死於非命)可以挽救後面軌道上5名工人的性命;第二類包含一些「低衝突性(沒有道德選擇困境)」、但高度個人化的情境,比如一對處於冷戰中的夫婦,丈夫是否應該僱人強姦自己妻子,隨後自己出面扮演好人安慰妻子,從而實現破鏡重圓的目的?第三類情境仍存在道德選擇困境,但決策情境是相對非個人化的,比如對一名安保人員撒謊,「借」得一艘快艇,以便向旅遊者預警一場即將來襲的猛烈風暴;第四類是一種與道德無關的選擇決策情境,比如為了如期達到某地,是否應乘火車而非巴士。
在清晰明確、低衝突性的個人化情境中,VMPFC 受損患者的反應與對照組類似,對上文中提及的例子,眾口一詞的回答是「不」。當考慮一些帶有強烈情感色彩且兩難程度較高的情境時,相對於其他組的受試者,VMPFC 受損患者更有可能贊同實用主義的決策,這會使集體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例如為了拯救軌道下游的工人們,他們將那位陌生的胖子推倒在車輪下的意願更加強烈。
理智VS 情感
在最後通牒博弈中,VMPFC 受損的玩家拒絕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幾率更高。因此有科學家假設,理智與情感共同導致了道德的產生。
為何VMPFC 受損的患者更加偏愛實用主義的選擇呢?讓人感興趣的是,這一特點可能是由於通常所說的情感鈍化(emotional blunting),這種特質常見於前額葉受損的病人當中。鈍化的情感可能會使這些病人更加傾向於理智的實用主義。但是早先由柯尼希斯和丹尼爾·特拉內爾(Daniel Tranel,美國艾奧瓦大學醫學院神經學教授)開展的、有VMPFC 受損患者參與的一項研究卻另有見解。在這項研究中,患者參與的測試項目是「最後通牒博弈」。
在這個遊戲中,兩個玩家會得到一筆錢。玩家A 向玩家B 提出分配這筆錢的方案,如果玩家B 拒絕了分配方案,那麼兩人都得不到錢。對於玩家B 而言,嚴格意義上的實用主義決策就是接受任何來自玩家A 的方案,即使他或她只能得到其中的百分之一,因為拒絕即意味着一無所獲。但大多數人都會拒絕過於不公平的方案,因為這樣的方案違反了自己內心的公平感。在這項研究中,相對於對照組,VMPFC 受損的玩家在遊戲中拒絕不公平方案的幾率更高。顯而易見,由於這一不公平、但卻有利可圖的方案對他們產生的侮辱感壓過了選擇實用主義的原則,因此他們摒棄了那些不公平的方案。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完全的情感鈍化及理性的實用主義似乎無法解釋VMPFC 受損患者的所作所為。
一篇發表在《自然-神經科學進展》的論文提出了一個更為謹慎的假設,認為理智與情感共同導致了道德感的產生。對於親社會(忠實於既定社會道德準則)的情感而言,VMPFC 區域尤為重要。這類情感包括內疚、憐憫及移情等。悲傷或親和等狀態[源自邊緣系統(limbic areas,位於大腦半球腹內側的一些皮質區以及在功能和結構上與這些皮質區關係密切的皮質下結構的總稱)]與其他一些機制(例如重大後果的前瞻性評估,這類機制由VMPFC 前端區域負責調節)相整合,可以促使這類情感的產生。功能性影像學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設想。我們在2007 年《社會神經學》(Social Neuroscience) 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及此前的研究,都曾提及,VMPFC 不僅在人們進行直接的道德判斷時發揮作用,當人們被動地接受親社會道德感的刺激因素(比如一名飢腸轆轆的兒童)時,VMPFC 也會發揮作用。我們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當自願者作出向慈善事業捐款的選擇(這是一個既有實用主義因素也有情感因素的決定)時,VMPFC 前部區域會牽涉其中,這一發現發表在2006 年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
雖然腹內側或下側前額葉皮質受損會導致親社會情感缺失,但仍保留了體驗某些與憤怒、沮喪相關的負面情緒的能力[這些情緒反應更多地依賴於前額葉皮質(PFC)的邊緣區域及皮質下連接(subcortical connection)],這些或許可以解釋柯尼希斯所進行的兩項結論彼此矛盾的研究。例如,參與最後通牒博弈的VMPFC 受損玩家被憤怒或輕蔑等情緒操控,作出了非實用主義的決策,拒絕了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然而,當面臨相當困難的道德兩難情境時,VMPFC 患者更容易作出實用主義的選擇,原因是這些患者前額葉皮質的腹內側部分受損,導致他們的親社會情感衰減缺失,因此在決策過程中,冰冷的理智相對於非實用主義便具有了優勢。
這一解釋讓我們的思緒回到愛因斯坦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總統的信促使美國研製出了第一顆原子彈。這些威力驚人的炸彈葬送了數十萬人的性命,但拜這些炸彈所賜,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愛因斯坦的理性認知壓倒了情感因素,作出了實用主義的選擇,這是一種冷血行為嗎?我們並不這麼認為。愛因斯坦的理智與情感似乎完美地共同發揮作用,充分反映了思維、情感、移情、遠見、苦悶及矛盾彼此互相交織在一起,同時這些因素也是複雜的道德決策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