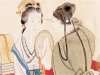序
<<山楂樹之戀>>是以靜秋77年寫的一個類似回憶錄的東西為基礎寫成的,敘事是艾米的,對話大多是靜秋原文中的。
77年是中國在文革後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一年,靜秋那時已經頂職參加了工作,在L省K市八中附小教書,她也報了名,準備參加高考。
她那時的生活已經比挑沙歲月不知好了多少倍了,這次又有幸報名參加高考,使她想起老三曾經用來安慰她的那些話,說她會從農村招回來的,說「天生我才必有用」。
可惜的是,當老三的預言一個接一個開始成為現實的時候, 卻。。。。 靜秋開始寫那個回憶錄,以紀念她跟老三一起度過的那段時光。
後來她把老三的故事寫成一個3萬字左右的小說,寄給「L省文藝」。她那時甚至不知道投稿應該寫在格子紙上,她就用一般的橫條信紙寫了,寄了出去。
那篇小說被退了回來,編輯評價說:「文筆細膩,風格清新...但人物缺乏鬥爭性...」,叫她按如下意見改寫後再寄回「L省文藝」。
靜秋沒有改寫,一是因為忙於應考,二來她寫那篇小說是為了紀念,如果按編輯要求改動,即便發表了,也沒有意義了。
後來,盧新華的<<傷痕>>發表,中國文壇進入「傷痕文學」時期...
艾米的父親開玩笑說可惜「L省文藝」的編輯膽子太小,不然可以代替<<傷痕>>的編輯,被寫進中國文學史了。
十年後,靜秋離開K市到L省的省會去讀書,再後來她妹妹出國,媽媽和哥哥相繼移民,家裏的東西都扔掉了。那篇退稿,早已不知扔到哪裏去了,但這篇寫在一個日記本里的回憶錄被她媽媽保存下來,帶到了加拿大。
艾米在參與寫完<<致命的溫柔>>後,就經常收到網友的悄悄話或跟貼,建議寫寫靜秋的故事。那時艾米還不知道靜秋的這段故事,只知道另外幾段,於是經常「威脅」靜秋,說要把她的故事寫出來,但她都沒有同意。
今年春節時,靜秋帶她的女兒SARA到艾米家來玩,帶來了那個日記本,讓艾米挑一些寫出來,紀念三十年前的那段故事。
於是就有了<<山楂樹之戀>>。
靜秋還經歷過其他很多苦難,令人敬佩的是,她沒有活在抱怨和傷痛里,而是成為一個能開解他人的知心姐姐.
七四年的初春,還在上高中的靜秋被學校選中,參加編輯新教材,要到一個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貧下中農家裏,採訪當地村民,然後將西村坪的村史寫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學生使用。
學校領導的野心當然還不止這些,如果教材編得好,說不定整個K市教育系統都會使用,又說不定一炮打響,整個L省,甚至全中國的初高中都會使用。到那時,K市八中的這一偉大創舉就會因為具有歷史意義而 被寫進中國教育史了。
這個在今日看來匪夷所思的舉動,在當時就只算「創新」了,因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資、修的一套,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樣:「長期以來,被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們統治着」。
文化革命開始後,雖然教材一再改寫,但也是趕不上形式的飛速變化。你今天才寫了「林彪大戰平型關」,歌頌林副主席英勇善戰,過幾天就傳來林彪叛逃,座機墜毀溫都爾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變了。
至於讓學生去編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標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總而言之,就是貴在創新哪。
跟靜秋一起被選中的,還有另外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都是平時作文成績比較好的學生。這行人被稱為「K市八中教改小組」,帶隊的是工宣隊的鄧師傅,三十多歲,人比較活躍,會唱點歌,拉點二胡,據說是因為身體不大好,在工廠也幹不了什麼活,就被派到學校來當工宣隊員了。
學校的陳副校長算是隊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語文的董老師,這一行七人,就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發了。
從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長途汽車到K縣縣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車往往要開個把小時,繞來繞去接人。K縣縣城離西村坪還有八、九里地,這段路就靠腳走了。
靜秋他們一行人到了K縣,就遇到了在那裏迎接他們的西村坪趙村長,說來也是個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縣K市都頗有名氣,因為村子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村,又有輝煌的抗日歷史,所以趙村長的名字也比較響亮。
不過在靜秋看來,趙村長也就是個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頭髮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點弓了,臉像也很一般,不符合當時對英雄人物的臉譜化描寫:身材魁梧,臉龐黑紅,濃眉大眼。靜秋馬上開始擔心,這樣一個人物,怎樣才能寫成一個「高、大、全」的英雄形像呢?看來這教材真的靠「編」了。
話說這一行七人,個個把自己的行李打成個軍人背包一樣的東西,背包繩的捆法是標準的「三橫壓兩豎」,每人手裏還提着臉盆牙刷之類的小件日用品。
趙村長說:「我們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從河溝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們幾個----,身體也不咋地,還有幾個女的,恐怕----」
這七位好漢異口同聲地說:「不怕,不怕,就是下來鍛煉的,怎麼樣艱苦就怎麼樣走。」
趙村長說:「翻山路也是鍛煉哪,走河溝還得趟幾道水,我怕你們這幾個女的---」
幾個「女的」一聽到別人叫她們「女的」,就渾身不自在,因為「女的」在當地話里,就是結了婚的女人。不過貧下中農這樣稱呼,幾個「女的」也不好發作,反而在心裏檢討自己對貧下中農純樸的語言沒有深刻認識,說明自己跟貧下中農在感情上還有一定距離,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跟貧下中農打成一片。
趙村長要幫幾個「女的」背東西,幾個「女的」一概拒絕,誰那麼嬌貴?不都是來鍛煉的嗎?怎麼能一開始就要人照顧?趙村長也不勉強,只說:「待會背不動了,就吭一聲。」
走出縣城,就開始翻山了。應該說山也不算高,但因為背着背包,提着網兜,幾個人也走得汗流浹背,趙村長手裏的東西越來越多,最後背上也不空了。三個「女的」有兩個的背包都不見了,光提着個臉盆等小件,還走得氣喘吁吁的。
靜秋是個好強的人,雖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還是堅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勞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標準,因為靜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來批鬥了,爸爸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媽媽是「歷史反革命的子女」。靜秋能被當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的待遇,完全是因為她平時表現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時時處處不落人後。
趙村長見大家有點苟延殘喘的樣子,就一直許諾:「不遠了,不遠了,等走到山楂樹那裏,我們就歇一會。」
這個「山楂樹」,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裏的那個「梅」,激勵着大家堅持走下去。
靜秋聽到這個山楂樹,腦子裏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顆樹,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樹>>,是首蘇聯歌曲。她最早聽到這首歌,是從一個L師大俄語繫到K市八中來實習的老師那裏聽到的。
分在靜秋那個班實習的是個二十六、七歲的女生,叫柳盈,人長得高大結實,皮膚很白,五官端正,鼻樑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點的話,簡直就象個外國人了。不過柳盈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雙層,而是三、四層,這讓班上的單眼皮女生羨慕得要死。
據說柳盈的父親是炮二司的什麼頭頭,因為林彪的事情,被整下去了,所以柳盈的日子曾經過得很慘。後來鄧小平上台,她父親又走運了,於是就把她從農村招回來,塞進了L師大。至於她為什麼進了俄語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為那時俄語早已不吃香了。
聽說解放初期,曾經有過一個學俄語的高潮,很多英語老師都改教俄語去了。後來中蘇交惡,蘇聯被中國稱為「修正主義」,因為他們居然想「修正」一下馬列主義。先前教俄語的那些老師,又有不少改教英語了。
靜秋就讀的K市八中,跟整個市區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麼想的,就把碩果僅存的幾個俄語老師全調到K市八中來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開俄語的中學,幾乎年年都有L師大俄語系的學生來實習,因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幾個縣裏有開俄語的中學了。
柳盈因為老頭子有點硬,所以沒分到下面縣裏的中學去。柳盈挺喜歡靜秋,沒事的時候,總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語歌曲,<<山楂樹>>就是其中一首。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是只能偷偷乾的,因為蘇聯的東西在中國早就成了禁忌,更何況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點「愛情」的東西都當作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東西給禁了。
按當時的觀點,<<山楂樹>>不僅是「黃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沒落」「作風不正」,因為歌詞大意是說兩個青年同時愛上了一個姑娘,這個姑娘也覺得他們倆都很好,不知道該選擇誰,於是去問山楂樹。歌曲最後唱到:
「可愛的山楂樹啊,白花開滿枝頭,
親愛的山楂樹啊,你為何發愁?
。。。
最勇敢最可愛的,到底是哪一個,
親愛的山楂樹啊,請你告訴我。」
柳盈嗓子很好,是所謂「洋嗓子」,自稱「意大利美聲唱法」,比較適合唱這類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時候,柳盈就跑到靜秋家,讓靜秋用手風琴為她伴奏,盡情高歌一陣。柳盈最喜歡的歌,就是<<山楂樹>>,她到底是因為覺得這歌好聽,還是因為也同時愛着兩個人,不知如何取捨,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靜秋聽趙村長提到「山楂樹」,還真吃了一驚,以為他也知道這首歌。不過她很快就明白過來,是真有這麼一棵樹,而且現在已經成了他們幾個人的奮鬥目標了。
背包壓在背上,又重又熱,靜秋覺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濕透了,手裏提的那個裝滿了小東西的網兜,那些細細的繩子也似乎早就勒進手心裏去了,只好不停地從左手換到右手,又從右手換到左手。
正在她覺得快要堅持不下去了的時候,忽聽趙村長說:「到了山楂樹了,我們歇一腳吧。」
幾個人一聽,如同死囚們聽到了大赦令一樣,出一口長氣,連背包也來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陣,幾個人才緩過氣來。鄧師傅問:「山楂樹在哪裏?」
趙村長指指不遠處的一棵大樹:「那就是。」
靜秋順着趙村長的手望過去,看見一顆六、七米高的樹,沒覺得有什麼特殊之處,可能因為天還挺冷的,不光沒有滿樹白花,連樹葉也還沒泛青。靜秋有點失望,因為她從<<山楂樹>>歌曲里提煉出來的山楂樹形像比這詩情畫意多了。
她每次聽到<<山楂樹>>這首歌,眼前就浮現出一個畫面:兩個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樹下,等待他們心愛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則穿着蘇聯姑娘們愛穿的連衣裙,姍姍地從暮色中走來。不過當她走到一定距離的時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個小伙子們看不見的地方,憂傷地詢問山楂樹,到底她應該愛哪一個。
靜秋好奇地問趙村長:「這樹是開白花嗎?」
這個問題仿佛觸動了趙村長,他滔滔不絕地講起來:「這棵樹呀,本來是開白花的,但在抗日戰爭期間,有無數的抗日誌士被日本鬼子槍殺在這棵樹下,他們的鮮血灌溉了樹下的土地。從第一個抗日英雄被殺害這裏開始,這棵樹的花色就慢慢變了,越變越紅,到最後,這棵樹就開紅花了。」
幾個人聽得目瞪口呆,鄧師傅提醒幾個學生:「還不快記下?」
幾個人恍然大悟,看來這次的採訪現在就開始了,於是紛紛找出筆記本,刷刷地記了起來。
看來趙村長是見過了大世面的,對這四、五杆筆刷刷地記錄他說的話好像司空見慣一樣,繼續着他的演說。等他講完這棵見證了西村坪人民抗日歷史的英雄樹的故事,半個小時已經過去了,一行人又啟程了。
走出老遠了,靜秋還回過頭看了看那棵山楂樹,隱隱約約的,她覺得她看見那棵樹下站着個人,但不是趙村長描繪過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綁的抗日誌士,而是一個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決心要好好向貧下中農學習,把教材編好。
這棵樹的故事,是肯定要寫進教材的了,用個什麼題目呢?也許就叫<<血染的山楂樹>>?好像太血腥了一點,改成<<開紅花的山楂樹>>?或者<<紅色山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