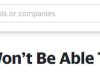中國通貨膨脹究竟因何而起?
岳健勇/陳漫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00期)]
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通貨膨脹的勢頭逐漸顯現,2007年通脹發展驟然加速,國內物價出現全面較大幅度上漲。中國國家統計局宣佈,2007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 )上升了4.8%.官方公佈的物價指數如此之低,與公眾對現實生活的感受相距甚遠。2008年春節前夕發生在中南和西南地區的雪災,造成當地基礎設施嚴重受損以及農業大面積歉收,致使物價漲勢更加兇猛。2008年2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PPI )同比上漲了6.6%,其中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9.7%;與此同時,食品價格上漲了11.0%.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已經發生嚴重通脹,「反通脹」現已成為中國政府經濟工作的首要目標。
嚴重通脹是否必然?
目前的通貨膨脹是如何產生的?不少海內外研究者認為,通脹是經濟過熱的表現,是中國外向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必然產物;而經濟過熱是由流動性過剩引起的,所謂「流動性過剩」是指國內外遊資以及銀行信貸大量增加而導致的貨幣流通量過多。有經濟學家不贊同這種一概而論的分析,認為中國經濟並沒有全面過熱,而是存在長期結構性失衡,即上游國有壟斷部門的長期「過熱」與下游競爭性部門的長期「過冷」同時並存[1].這一看法有相當的事實依據。產業發展過熱必然刺激通脹的發生,但過冷產業因上下游價格傳導關係則未必能避免通脹的波及。統計數據清晰顯示,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價格出現連續上漲,全面通脹已是不爭的事實。
問題在於,局部的產業過熱何以最終引發全局性通脹?局部產業過熱最初又是如何形成的?推動全面通脹的內外因素究竟為何?
毫無疑問,國有壟斷部門的「過熱」來自下游產業部門持久旺盛的需求。然而下游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競爭性產業的「過冷」或「偏冷」並非始於今日,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大部分時期,因通貨緊縮以及不利的制度環境,相當一批私營企業缺乏投資意願。於是,經濟分析人士傾向於將上游壟斷部門的「過熱」歸結為房地產業的過度投資。房地產業的畸形膨脹源於中國土地資源日益嚴重的短缺、以及1994年分稅制改革給地方政府造成的負面激勵。但是,1993年中央政府實施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後,金融地產泡沫破滅,商品房以及商用樓宇即出現大量空置;1998年住房改革的推行令房地產市場陷入低迷。從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上半年,房地產業發展勢頭趨於緩慢,儘管以國有商業銀行大量資金沉澱甚至壞賬為代價拉動了上游產業的發展,並推動了生產者價格指數的上升,卻並沒有造成上游部門的過熱,更沒有傳導到下游產業部門,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此外,從貨幣投放方面看,從1992年至世紀之交,中國對外貿易幾乎年年順差,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可是中國既沒有出現人民幣升值的明顯壓力,也沒有出現流動性過剩。相反,由於持續通貨緊縮以及美國經濟出現衰退跡象等原因,人民幣甚至一度(2001年下半年)出現貶值壓力。通貨緊縮意味着國內需求相對於供給的不足,對此,中國政府一方面記取1980年代末的政策教訓,決意杜絕通貨膨脹,在不斷降息的同時,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貨幣流通總量;另一方面,又通過發行國債、投資公共工程等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增加總需求。這種近似於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取得的即時成效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得以實現,但通縮依舊,中國經濟墮入了「流動性」陷阱。
中國政府試圖通過赤字財政和大規模國債投資來刺激內需。然而,由於國內普遍缺乏投資意願,且公共工程腐敗低效、並對社會投資發生「擠出效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造成極高的經濟社會成本,使中國經濟難以維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對於這一時期所謂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可以得出三點結論:其一、實際經濟增長率存在高估的可能[2];其二、外向型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引發通貨膨脹;其三、中國經濟在通貨緊縮狀態下取得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
轉折的出現:入世與「戰略機遇期」
出口和外資對中國經濟越來越顯著的刺激作用,鼓勵並誘導着更大程度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而經濟增長的高度政治化隨着中國經濟對外資和海外市場依賴的加深,必然導致經濟政策的極端自由化。不惜代價加入世貿組織(WTO )以維持經濟增長,反映了中國在改革和經濟增長日益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自由主義取向經濟發展方針的激進化[3].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WTO 是個標誌性的重大事件,表明中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進程從此不可逆轉,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入世後,外資將其製造業的低端大舉轉移到中國,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遂告形成。伴隨這一重大變動的是,中國政府於2002年開始了以放鬆銀根、擴大投資和出口為標誌的宏觀政策的重大轉變。
促進這一轉變的不僅有經濟全球化因素,國際政治方面的變化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2001年9.11事件使美國轉向單邊主義,並將全球反恐戰爭作為軍事安全戰略的核心,令1990年代後半期以來一度緊張的中美關係得到根本改善。經濟全球化及安全環境的改善使中國政府做了如下戰略判斷:中國正處在一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乃至「和平崛起」的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政府「戰略機遇期」的提出,加強了海內外投資者關於中國經濟在加入全球化後將持續高速增長的預期。作為跨國公司價值鏈中最理想的低端生產環節,中國成了跨國公司向其全球營銷網絡提供最有價格競爭力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在中國入世後的幾年間,外資對中國產業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不但佔有相當可觀的國內市場份額,而且控制了中國一半以上的進出口貿易和近90%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海外市場的擴大則對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專事低技術產品生產的中國產業提供了強烈誘導。因此,中國入世導致國際貿易、特別是出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急劇擴大,外匯儲備迅猛增長,由此造成了海內外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國外遊資大量進入中國。而銀根的進一步鬆動(2003年)導致銀行信貸量大增,貨幣流通量迅速增加,流動性過剩問題開始浮現。
走向通貨膨脹
中國經濟再度強勁增長的預期使房地產業迅速回溫。2003年下半年,SARS疫情一結束,全國各地房地產業便陸續走出低迷,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過熱苗頭。從2004年下半年起,許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出現較大漲幅,並加速上升。
表面上看,房地產迅速升溫是由國內遊資炒作而起,其實是房地產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利用「戰略機遇期」所塑造的市場預期聯手共謀的結果。這一局面有其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不能簡單將責任單方面歸咎於謀求自利的地方政府[4].共謀若僅僅立足於政策想像空間則難以成功並持久,只有發掘和引導出足夠多的市場需求,方能使房地產的行情不斷膨脹。這取決於市場供求態勢、尤其是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和購買意願。在供給方面,國內可供開發的土地數量持續下降使房地產增值成為必然,中國土地資源的日漸稀缺則使房地產投資成為可居之奇貨[5].因此,房地產價格已然蓄勢待發,只待宏觀政策的改變。一旦貨幣政策環境寬鬆,房地產價格便可能大幅上升。在需求方面,房地產較大的漲勢以及房價將持續攀升的前景促使許多購買者將未來消費轉化為當期消費,因而出現了旺盛的市場需求[6].與此同時,銀根鬆動後,商業銀行為實現業務品種和利潤來源的多樣化,爭相發放個人按揭貸款和消費貸款;而銀行間的惡性競爭又導致了貸款條件的不斷放寬,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購買需求。需求的大量增加推動了房價持續上升,價差的擴大同時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造成供給緊張甚至短缺,吸引了開發資金不斷流入。
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自然希望房地產維持較高的市場價格,以便儘可能長久地支撐土地一級市場的出讓價格,以確保地方政府投資各項工程、特別是形象工程的預算外資金來源。近年來,因土地和居民住房被強行徵用拆遷所引發的城鄉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其背後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以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名,通過商業運作方式追求土地收益的強烈衝動[7].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共謀的結果是造成了房地產業驚人的暴利,吸引了大量海內外遊資和銀行信貸資金進入房地產業。2003年下半年以來,投機嚴重的房地產價格連續大幅度上升,早已超出了絕大多數普通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和正常的市場需求,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
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意志不堅決,是房地產業發生惡性膨脹的重要外部原因,但這只是問題的表象。調控不力從根本上暴露出中央對地方控制能力下降。與1980、90年代相比,地方當局通過壟斷當地資源和操縱本地市場,已積聚起相當可觀的經濟實力和輿論影響力,其力量之強大,捍衛自身利益態度之堅決,已遠非昔日可比。在缺乏制度創新的情況下,中央控制地方的有效辦法似乎只有加強中央集權一途,但這不可避免地使中央和地方的權力之爭或政策之爭最終表現為雙方經濟利益上的爭奪。房地產市場的快速泡沫化,實際上反映了地方對中央宏觀政策在初期的成功利用和其後的有效抵制。
現代工業經濟的複雜性表現為產業部門之間的密切關聯和相互依存,中央和地方在宏觀調控上發生的利益衝突並不總是零和博弈。地方政府推動形成的房地產業泡沫為上游的原材料、能源等國有壟斷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強勁需求。這些大型國有企業處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管之下,不受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近年來在產業規模迅猛擴張和利潤激增的基礎上,已發展成通過集體分肥保持內部凝聚力,敢於公開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甚至影響政策制定的能量極大的既得利益集團[8].這些處於產業上游的寡頭壟斷企業一方面採取各種手段使政府的價格管制措施變形或失效;另一方面又以資源短缺和投入品成本上升為由,要求政府提供巨額財政補貼,或接受其維持壟斷高價、甚至提價的主張。
上游壟斷部門的持續過熱,根源在於下游產業(主要是房地產業)的強勁需求。從理論上講,如果需求控制失效,就只能從增加供給入手。但弔詭的是,投資擴大帶來的供給增加未必引起價格的回落。因為上游產業必需的大宗原材料嚴重依賴進口,進口量的劇增導致國際原油和鐵礦砂等價格急劇上升。由於投入品的剛性成本壓力,加之大型央企的行業壟斷,上游產品價格非但未隨供給增加而回落,反而繼續上升。
正因為國有壟斷部門「給定」了市場價格,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些非國有企業也向上游增加投資。江蘇常州「鐵本事件」即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中處理上游產業投資泡沫的重要個案。其處理結果表明,中央政府既無意於深究私營鋼鐵企業「鐵本」背後的地方政府責任,更無意於觸動與自身財政利益密切相關的大型國企的利益。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上的躊躇不決和力不從心,使通貨膨脹向下游產業的蔓延終於無法避免。國內下游產業大多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製造,價格競爭異常激烈,很難通過提高產品的國內價格和出口價格來轉嫁上游傳導的成本壓力。發展的艱難導致相當一批低技術製造業投資意願下降,一些企業減少了投資甚至轉向房地產和股市以牟取暴利,而部分企業則通過降低產品的質量標準以求生路,質量下降等同於變相提價。
食品價格上漲對分析通貨膨脹的根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食品業自身的產業鏈成本價格變動通常是引起通貨膨脹的一個獨立變量。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對可耕地的大量佔用,中國的土地資源急劇減少,2007年已降至18億畝的警戒線,農產品供給出現較大缺口。同時,入世後農業的開放使小農經濟無法抵禦來自發達國家農產品的競爭,迅速喪失了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如大豆和小麥)[9].而分銷業的開放則令相關的下游國內食品加工業同樣受到嚴重衝擊,進而推動了產成品價格的暴漲(如植物油)[10].更為嚴峻的是,由於全球能源供給的有限性,美國等發達國家已開始從農作物中提煉能源,大大減少了農產品的出口,由此引起了全球農產品價格的暴漲。這些因素都引起國內食品價格的大幅度上升,進而推動國內的通貨膨脹。
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巨量遊資及銀行信貸資金湧入股市,推動了股價全面暴升,出現了多年罕見的牛市奇觀。但股市暴漲卻缺乏上市公司業績全面提高這一微觀基本面的支持。若剔除與股市泡沫相關的資本交易等非主營業務收入,上市公司的業績並無根本改善。這反映了中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多年沉疴,即上市不過是圈錢的手段,並未根本解決多數上市公司的產權約束機制問題。股市暴升的動力來自中國證券監管當局放寬外資進入國內資本市場的准入標準。其背景是,入世後國內產業遭遇前所未有的國際競爭壓力,當局希望通過大型國企上市以補充資本金的傳統辦法,來提高這些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國外金融資本進入中國股市進一步加強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僅帶動了國內遊資加入,還吸引了懷有種種複雜心態、渴望暴富的國人蜂擁入市。進入股市的資金量之大把市盈率很快推高到幾倍於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股市泡沫迅速積聚。國外投資者在2007年幾度在波段峰谷及時淡出,它們看中的並非中國股市的投資價值,而是人民幣匯差和股市價差的雙重財富效應。中國政府的機會主義政策指引刺激了股票市場濃厚的投機行為,造成了嚴重的股市泡沫,間接刺激了通脹的發展。
綜上分析,中國通貨膨脹的起因相當複雜,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有關經濟將加快發展的預期與政策調整是主要原因;而全球化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如糧食危機和國企的生存壓力,也從不同方面推動了通脹的發展。中央與地方行政分權的制度安排與壟斷性央企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則在相當程度上抵銷了中央政府化解通脹的宏觀調控努力,以至於局部產業發展過熱演變為全局性的通貨膨脹。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與日本1980年代末的情形表面上很相像,但重大區別在於兩國的國力不同。日本當時已經是高度工業化國家,這是日本能承受泡沫破滅後長達十餘年經濟衰退的國力基礎;而中國的企業嚴重缺乏創新能力,產業升級遇到極大困難,因而無法通過「走出去」來緩解國內通脹帶來的壓力。即便是擁有技術優勢的西方跨國公司,由於在華經營的成本優勢受到通脹的侵蝕,也有意撤資。筆者曾以「無技術工業化」這一概念闡釋中國產業發展狀況:「無技術工業化意味着作為尚未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被牢牢鎖定在國際分工的底層,它的表現形式就是中國對外資以及對海外出口市場的雙重依賴」[11].這種依賴與當前通脹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通貨膨脹將可能讓中國失去出口和外資這兩大經濟發展推動力。一旦泡沫破滅,中國經濟衰退的表現形式及其產生的社會政治後果,無疑將比當年的日本要嚴峻得多。
「注釋」
[1]郎咸平,2008年1月12日在「中國房地產20年」年會上的演講(中華金融網:www.folcn.com/news/caijingguancha/20080123)。
[2]Thomas G.Rawski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Sept.12,2001(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1/gdp912f.pdf );LesterThurow,「A Chinese Century ?Maybe It 『s the Next One」。New YorkTimes ,Aug.19,2007.http://www.nytimes.com/2007/08/19/busin ... 9view.html[3]朱鎔基2002年3月在會見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時坦承:「如果(中國)不加入世貿,改革和經濟增長都是不可能的」。StephenRoach (from Beijing),「China :Straight Talk from Zhu 」,March 27,2002(www.morganstanley.com/GEFdata/digests/20020327-wed.html )42003年。
[4]2004年6月房地產業已明顯過熱,中央銀行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121號文件),以控制投資過熱。這一措施激起了房地產商的強烈反對。7月,國內經濟學界開始爭論經濟是否過熱。溫家寶在與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商務部、發改委等部門的經濟學者座談時表態:「我有主心骨,不會動搖」,「中國經濟發展正處於重要的機遇期」。8月31日,國務院出台了「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18號文件),房地產界為之振奮,有「地產界教父」之稱的任志強表示:「可見國務院的水平大大高於央行一頭」。見報道「尋蹤第五次宏觀調控」,《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5月25日。
[5]例如,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如廣東省,可供商業開發的土地已基本批租或拍賣完畢。
[6]這裏需要提到一個特殊情況,在房地產價格出現較大升幅後,許多與權力部門有密切關聯的利益集團以各種名義和方式向其內部職工提供可觀的購房補貼,使他們實際支付的購房成本不高於這一輪房地產漲價前的市場價格。房地產市場的火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這部分特殊需求支撐的,目前尚難估計,但其提供的強大購買需求無疑助長了房地產市場的快速膨脹。
[7]有關數據顯示,地方政府每年從土地出讓中取得的收入高達9,000多億,約佔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見「地方政府『吃』地為生數十年收益一朝耗盡」,《南方都市報》2008年3月15日。
[8]一位中央政府官員曾對筆者說起,隨溫出訪的某大型央企領導人在其面前口出狂言,說:「在(中央)制定政策上,總理現在也得聽咱們的。」
[9]李昌平:「中國農民正在失去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南方周末》2008年1月16日。
[10]佔有全球90%市場份額的4大國際糧油交易商ADM 、邦吉、嘉吉、路易。達孚,現已控制了國內85%的大豆加工能力,從而形成了從大豆原料進口、加工到成品(豆油)批發的完整產業鏈。外資的壟斷競爭優勢令國內豆農和加工廠無法與之抗衡,面臨滅頂之災。見「大豆淪陷」,《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12月15日(www.21cbh.com/Content.asp ?NewsId=7432)。
[11]岳健勇,「人民幣升值背後的去工業化憂慮」,《鳳凰周刊》2007年第18期,2007年6月25日。
岳健勇/陳漫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00期)]
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通貨膨脹的勢頭逐漸顯現,2007年通脹發展驟然加速,國內物價出現全面較大幅度上漲。中國國家統計局宣佈,2007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 )上升了4.8%.官方公佈的物價指數如此之低,與公眾對現實生活的感受相距甚遠。2008年春節前夕發生在中南和西南地區的雪災,造成當地基礎設施嚴重受損以及農業大面積歉收,致使物價漲勢更加兇猛。2008年2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PPI )同比上漲了6.6%,其中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9.7%;與此同時,食品價格上漲了11.0%.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已經發生嚴重通脹,「反通脹」現已成為中國政府經濟工作的首要目標。
嚴重通脹是否必然?
目前的通貨膨脹是如何產生的?不少海內外研究者認為,通脹是經濟過熱的表現,是中國外向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必然產物;而經濟過熱是由流動性過剩引起的,所謂「流動性過剩」是指國內外遊資以及銀行信貸大量增加而導致的貨幣流通量過多。有經濟學家不贊同這種一概而論的分析,認為中國經濟並沒有全面過熱,而是存在長期結構性失衡,即上游國有壟斷部門的長期「過熱」與下游競爭性部門的長期「過冷」同時並存[1].這一看法有相當的事實依據。產業發展過熱必然刺激通脹的發生,但過冷產業因上下游價格傳導關係則未必能避免通脹的波及。統計數據清晰顯示,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價格出現連續上漲,全面通脹已是不爭的事實。
問題在於,局部的產業過熱何以最終引發全局性通脹?局部產業過熱最初又是如何形成的?推動全面通脹的內外因素究竟為何?
毫無疑問,國有壟斷部門的「過熱」來自下游產業部門持久旺盛的需求。然而下游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競爭性產業的「過冷」或「偏冷」並非始於今日,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大部分時期,因通貨緊縮以及不利的制度環境,相當一批私營企業缺乏投資意願。於是,經濟分析人士傾向於將上游壟斷部門的「過熱」歸結為房地產業的過度投資。房地產業的畸形膨脹源於中國土地資源日益嚴重的短缺、以及1994年分稅制改革給地方政府造成的負面激勵。但是,1993年中央政府實施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後,金融地產泡沫破滅,商品房以及商用樓宇即出現大量空置;1998年住房改革的推行令房地產市場陷入低迷。從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上半年,房地產業發展勢頭趨於緩慢,儘管以國有商業銀行大量資金沉澱甚至壞賬為代價拉動了上游產業的發展,並推動了生產者價格指數的上升,卻並沒有造成上游部門的過熱,更沒有傳導到下游產業部門,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此外,從貨幣投放方面看,從1992年至世紀之交,中國對外貿易幾乎年年順差,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可是中國既沒有出現人民幣升值的明顯壓力,也沒有出現流動性過剩。相反,由於持續通貨緊縮以及美國經濟出現衰退跡象等原因,人民幣甚至一度(2001年下半年)出現貶值壓力。通貨緊縮意味着國內需求相對於供給的不足,對此,中國政府一方面記取1980年代末的政策教訓,決意杜絕通貨膨脹,在不斷降息的同時,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貨幣流通總量;另一方面,又通過發行國債、投資公共工程等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增加總需求。這種近似於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取得的即時成效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得以實現,但通縮依舊,中國經濟墮入了「流動性」陷阱。
中國政府試圖通過赤字財政和大規模國債投資來刺激內需。然而,由於國內普遍缺乏投資意願,且公共工程腐敗低效、並對社會投資發生「擠出效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造成極高的經濟社會成本,使中國經濟難以維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對於這一時期所謂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可以得出三點結論:其一、實際經濟增長率存在高估的可能[2];其二、外向型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引發通貨膨脹;其三、中國經濟在通貨緊縮狀態下取得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
轉折的出現:入世與「戰略機遇期」
出口和外資對中國經濟越來越顯著的刺激作用,鼓勵並誘導着更大程度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而經濟增長的高度政治化隨着中國經濟對外資和海外市場依賴的加深,必然導致經濟政策的極端自由化。不惜代價加入世貿組織(WTO )以維持經濟增長,反映了中國在改革和經濟增長日益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自由主義取向經濟發展方針的激進化[3].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WTO 是個標誌性的重大事件,表明中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進程從此不可逆轉,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入世後,外資將其製造業的低端大舉轉移到中國,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遂告形成。伴隨這一重大變動的是,中國政府於2002年開始了以放鬆銀根、擴大投資和出口為標誌的宏觀政策的重大轉變。
促進這一轉變的不僅有經濟全球化因素,國際政治方面的變化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2001年9.11事件使美國轉向單邊主義,並將全球反恐戰爭作為軍事安全戰略的核心,令1990年代後半期以來一度緊張的中美關係得到根本改善。經濟全球化及安全環境的改善使中國政府做了如下戰略判斷:中國正處在一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乃至「和平崛起」的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政府「戰略機遇期」的提出,加強了海內外投資者關於中國經濟在加入全球化後將持續高速增長的預期。作為跨國公司價值鏈中最理想的低端生產環節,中國成了跨國公司向其全球營銷網絡提供最有價格競爭力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在中國入世後的幾年間,外資對中國產業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不但佔有相當可觀的國內市場份額,而且控制了中國一半以上的進出口貿易和近90%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海外市場的擴大則對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專事低技術產品生產的中國產業提供了強烈誘導。因此,中國入世導致國際貿易、特別是出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急劇擴大,外匯儲備迅猛增長,由此造成了海內外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國外遊資大量進入中國。而銀根的進一步鬆動(2003年)導致銀行信貸量大增,貨幣流通量迅速增加,流動性過剩問題開始浮現。
走向通貨膨脹
中國經濟再度強勁增長的預期使房地產業迅速回溫。2003年下半年,SARS疫情一結束,全國各地房地產業便陸續走出低迷,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過熱苗頭。從2004年下半年起,許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出現較大漲幅,並加速上升。
表面上看,房地產迅速升溫是由國內遊資炒作而起,其實是房地產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利用「戰略機遇期」所塑造的市場預期聯手共謀的結果。這一局面有其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不能簡單將責任單方面歸咎於謀求自利的地方政府[4].共謀若僅僅立足於政策想像空間則難以成功並持久,只有發掘和引導出足夠多的市場需求,方能使房地產的行情不斷膨脹。這取決於市場供求態勢、尤其是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和購買意願。在供給方面,國內可供開發的土地數量持續下降使房地產增值成為必然,中國土地資源的日漸稀缺則使房地產投資成為可居之奇貨[5].因此,房地產價格已然蓄勢待發,只待宏觀政策的改變。一旦貨幣政策環境寬鬆,房地產價格便可能大幅上升。在需求方面,房地產較大的漲勢以及房價將持續攀升的前景促使許多購買者將未來消費轉化為當期消費,因而出現了旺盛的市場需求[6].與此同時,銀根鬆動後,商業銀行為實現業務品種和利潤來源的多樣化,爭相發放個人按揭貸款和消費貸款;而銀行間的惡性競爭又導致了貸款條件的不斷放寬,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購買需求。需求的大量增加推動了房價持續上升,價差的擴大同時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造成供給緊張甚至短缺,吸引了開發資金不斷流入。
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自然希望房地產維持較高的市場價格,以便儘可能長久地支撐土地一級市場的出讓價格,以確保地方政府投資各項工程、特別是形象工程的預算外資金來源。近年來,因土地和居民住房被強行徵用拆遷所引發的城鄉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其背後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以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名,通過商業運作方式追求土地收益的強烈衝動[7].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共謀的結果是造成了房地產業驚人的暴利,吸引了大量海內外遊資和銀行信貸資金進入房地產業。2003年下半年以來,投機嚴重的房地產價格連續大幅度上升,早已超出了絕大多數普通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和正常的市場需求,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
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意志不堅決,是房地產業發生惡性膨脹的重要外部原因,但這只是問題的表象。調控不力從根本上暴露出中央對地方控制能力下降。與1980、90年代相比,地方當局通過壟斷當地資源和操縱本地市場,已積聚起相當可觀的經濟實力和輿論影響力,其力量之強大,捍衛自身利益態度之堅決,已遠非昔日可比。在缺乏制度創新的情況下,中央控制地方的有效辦法似乎只有加強中央集權一途,但這不可避免地使中央和地方的權力之爭或政策之爭最終表現為雙方經濟利益上的爭奪。房地產市場的快速泡沫化,實際上反映了地方對中央宏觀政策在初期的成功利用和其後的有效抵制。
現代工業經濟的複雜性表現為產業部門之間的密切關聯和相互依存,中央和地方在宏觀調控上發生的利益衝突並不總是零和博弈。地方政府推動形成的房地產業泡沫為上游的原材料、能源等國有壟斷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強勁需求。這些大型國有企業處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管之下,不受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近年來在產業規模迅猛擴張和利潤激增的基礎上,已發展成通過集體分肥保持內部凝聚力,敢於公開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甚至影響政策制定的能量極大的既得利益集團[8].這些處於產業上游的寡頭壟斷企業一方面採取各種手段使政府的價格管制措施變形或失效;另一方面又以資源短缺和投入品成本上升為由,要求政府提供巨額財政補貼,或接受其維持壟斷高價、甚至提價的主張。
上游壟斷部門的持續過熱,根源在於下游產業(主要是房地產業)的強勁需求。從理論上講,如果需求控制失效,就只能從增加供給入手。但弔詭的是,投資擴大帶來的供給增加未必引起價格的回落。因為上游產業必需的大宗原材料嚴重依賴進口,進口量的劇增導致國際原油和鐵礦砂等價格急劇上升。由於投入品的剛性成本壓力,加之大型央企的行業壟斷,上游產品價格非但未隨供給增加而回落,反而繼續上升。
正因為國有壟斷部門「給定」了市場價格,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些非國有企業也向上游增加投資。江蘇常州「鐵本事件」即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中處理上游產業投資泡沫的重要個案。其處理結果表明,中央政府既無意於深究私營鋼鐵企業「鐵本」背後的地方政府責任,更無意於觸動與自身財政利益密切相關的大型國企的利益。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上的躊躇不決和力不從心,使通貨膨脹向下游產業的蔓延終於無法避免。國內下游產業大多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製造,價格競爭異常激烈,很難通過提高產品的國內價格和出口價格來轉嫁上游傳導的成本壓力。發展的艱難導致相當一批低技術製造業投資意願下降,一些企業減少了投資甚至轉向房地產和股市以牟取暴利,而部分企業則通過降低產品的質量標準以求生路,質量下降等同於變相提價。
食品價格上漲對分析通貨膨脹的根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食品業自身的產業鏈成本價格變動通常是引起通貨膨脹的一個獨立變量。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對可耕地的大量佔用,中國的土地資源急劇減少,2007年已降至18億畝的警戒線,農產品供給出現較大缺口。同時,入世後農業的開放使小農經濟無法抵禦來自發達國家農產品的競爭,迅速喪失了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如大豆和小麥)[9].而分銷業的開放則令相關的下游國內食品加工業同樣受到嚴重衝擊,進而推動了產成品價格的暴漲(如植物油)[10].更為嚴峻的是,由於全球能源供給的有限性,美國等發達國家已開始從農作物中提煉能源,大大減少了農產品的出口,由此引起了全球農產品價格的暴漲。這些因素都引起國內食品價格的大幅度上升,進而推動國內的通貨膨脹。
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巨量遊資及銀行信貸資金湧入股市,推動了股價全面暴升,出現了多年罕見的牛市奇觀。但股市暴漲卻缺乏上市公司業績全面提高這一微觀基本面的支持。若剔除與股市泡沫相關的資本交易等非主營業務收入,上市公司的業績並無根本改善。這反映了中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多年沉疴,即上市不過是圈錢的手段,並未根本解決多數上市公司的產權約束機制問題。股市暴升的動力來自中國證券監管當局放寬外資進入國內資本市場的准入標準。其背景是,入世後國內產業遭遇前所未有的國際競爭壓力,當局希望通過大型國企上市以補充資本金的傳統辦法,來提高這些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國外金融資本進入中國股市進一步加強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僅帶動了國內遊資加入,還吸引了懷有種種複雜心態、渴望暴富的國人蜂擁入市。進入股市的資金量之大把市盈率很快推高到幾倍於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股市泡沫迅速積聚。國外投資者在2007年幾度在波段峰谷及時淡出,它們看中的並非中國股市的投資價值,而是人民幣匯差和股市價差的雙重財富效應。中國政府的機會主義政策指引刺激了股票市場濃厚的投機行為,造成了嚴重的股市泡沫,間接刺激了通脹的發展。
綜上分析,中國通貨膨脹的起因相當複雜,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有關經濟將加快發展的預期與政策調整是主要原因;而全球化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如糧食危機和國企的生存壓力,也從不同方面推動了通脹的發展。中央與地方行政分權的制度安排與壟斷性央企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則在相當程度上抵銷了中央政府化解通脹的宏觀調控努力,以至於局部產業發展過熱演變為全局性的通貨膨脹。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與日本1980年代末的情形表面上很相像,但重大區別在於兩國的國力不同。日本當時已經是高度工業化國家,這是日本能承受泡沫破滅後長達十餘年經濟衰退的國力基礎;而中國的企業嚴重缺乏創新能力,產業升級遇到極大困難,因而無法通過「走出去」來緩解國內通脹帶來的壓力。即便是擁有技術優勢的西方跨國公司,由於在華經營的成本優勢受到通脹的侵蝕,也有意撤資。筆者曾以「無技術工業化」這一概念闡釋中國產業發展狀況:「無技術工業化意味着作為尚未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被牢牢鎖定在國際分工的底層,它的表現形式就是中國對外資以及對海外出口市場的雙重依賴」[11].這種依賴與當前通脹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通貨膨脹將可能讓中國失去出口和外資這兩大經濟發展推動力。一旦泡沫破滅,中國經濟衰退的表現形式及其產生的社會政治後果,無疑將比當年的日本要嚴峻得多。
「注釋」
[1]郎咸平,2008年1月12日在「中國房地產20年」年會上的演講(中華金融網:www.folcn.com/news/caijingguancha/20080123)。
[2]Thomas G.Rawski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Sept.12,2001(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1/gdp912f.pdf );LesterThurow,「A Chinese Century ?Maybe It 『s the Next One」。New YorkTimes ,Aug.19,2007.http://www.nytimes.com/2007/08/19/busin ... 9view.html[3]朱鎔基2002年3月在會見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時坦承:「如果(中國)不加入世貿,改革和經濟增長都是不可能的」。StephenRoach (from Beijing),「China :Straight Talk from Zhu 」,March 27,2002(www.morganstanley.com/GEFdata/digests/20020327-wed.html )42003年。
[4]2004年6月房地產業已明顯過熱,中央銀行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121號文件),以控制投資過熱。這一措施激起了房地產商的強烈反對。7月,國內經濟學界開始爭論經濟是否過熱。溫家寶在與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商務部、發改委等部門的經濟學者座談時表態:「我有主心骨,不會動搖」,「中國經濟發展正處於重要的機遇期」。8月31日,國務院出台了「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18號文件),房地產界為之振奮,有「地產界教父」之稱的任志強表示:「可見國務院的水平大大高於央行一頭」。見報道「尋蹤第五次宏觀調控」,《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5月25日。
[5]例如,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如廣東省,可供商業開發的土地已基本批租或拍賣完畢。
[6]這裏需要提到一個特殊情況,在房地產價格出現較大升幅後,許多與權力部門有密切關聯的利益集團以各種名義和方式向其內部職工提供可觀的購房補貼,使他們實際支付的購房成本不高於這一輪房地產漲價前的市場價格。房地產市場的火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這部分特殊需求支撐的,目前尚難估計,但其提供的強大購買需求無疑助長了房地產市場的快速膨脹。
[7]有關數據顯示,地方政府每年從土地出讓中取得的收入高達9,000多億,約佔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見「地方政府『吃』地為生數十年收益一朝耗盡」,《南方都市報》2008年3月15日。
[8]一位中央政府官員曾對筆者說起,隨溫出訪的某大型央企領導人在其面前口出狂言,說:「在(中央)制定政策上,總理現在也得聽咱們的。」
[9]李昌平:「中國農民正在失去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南方周末》2008年1月16日。
[10]佔有全球90%市場份額的4大國際糧油交易商ADM 、邦吉、嘉吉、路易。達孚,現已控制了國內85%的大豆加工能力,從而形成了從大豆原料進口、加工到成品(豆油)批發的完整產業鏈。外資的壟斷競爭優勢令國內豆農和加工廠無法與之抗衡,面臨滅頂之災。見「大豆淪陷」,《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12月15日(www.21cbh.com/Content.asp ?NewsId=7432)。
[11]岳健勇,「人民幣升值背後的去工業化憂慮」,《鳳凰周刊》2007年第18期,200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