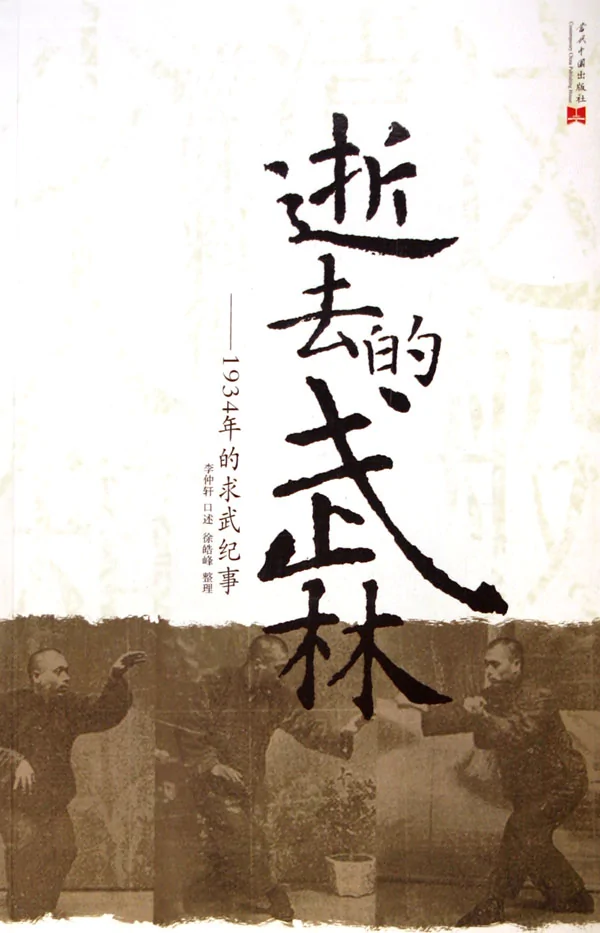|
|
|
|
李仲軒老先生確得到了唐維祿、尚雲祥、薛顛先生的真傳,並在中國武術人才斷層與技術斷層的關鍵時刻,輕描淡寫地將之披露,是在兩大技術斷層中起到了部分鋼筋支撐作用。文章面世後,得到廣泛好評,尤其在活躍的網絡上,得到不同門派的推崇,其影響還波及海外。
李仲軒老先生文章中有許多內容,再現了當時武林風俗,對習藝作人很有啟迪。例如:
一、 古人守信:
尚先生收徒時為其所立的規矩,真實地反映出前輩們凡事不僅僅考慮到自己,還要為其弟子們着想,對人負責,也對這門藝術的傳播負責。這是歷史,李老的作法也是與此一脈相承的,實現了對恩師的信用!
二、 弘揚國術精神:
誠然如李存義先生所言「形意拳叫國術,就是保家衛國」,我的恩師亦曾道: 「心意、形意的真傳正傳,乃是正、大、光、明。」這不僅僅是指技術上,更是指精氣神、膽識、氣魄與抱負!津津樂道於一拳一腳,誰勝誰負者,必與真諦相去甚遠!
三、 體現武術工藝層面:
武術的內容除去拳譜上的理論和指導時的具體要求,實際上,從深層次上分析,還有一大塊內容,那是難以表達,難以傳播的,但卻對學者的成功與否起到關鍵作用的中間內容——筆者喻之為「武術工藝層」,這些內容,處於理論與具體要求之間的夾縫中,難以尋求,不易悟到,而李老的文章中卻含有許多,實難能可貴,價值連城。
四、 提供歷史證據:
李老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技術藝術真傳等內容,而且為形意有關歷史,文化,事件現象及其人物的空白,提供了及時的證據。且提醒我們,以今日之理去判斷衡量古人,在歷史研究中是不恰當的。
以前,我們看到民國時期出版的武術書中,常有以口令形式編排的教學內容,使人看後產生懷疑:那是國術麼?是內行所為麼?
李老文中簡單的一句話,倒出了緣由:那是國難當頭時,國術界的熱血男兒為早日培養出殺敵之軍而作的努力!
歷史證據表明,中國抗日部隊確以形意門武功訓練士兵,如《最新形意刺槍術》一書,印成方便攜帶的隨軍小冊,這是歷史上形意拳大規模運用於「保家衛國」實戰中的證據,進而回證了李先生講述的那段歷史真情。
牆倒容易推,天塌最難擎。中華武學經過戰亂、抗戰戰爭、文革等,至今已經是青黃不接。技術與學術,文化與歷史均出現嚴重斷層,挖掘搶救刻不容緩,在這一時刻,出來為斷層接續的人,就是武術界的英雄。
但當李老先生開始傾吐更高層次的形意絕學,令我們了解和分享其中奇妙的時候,卻意外辭世,系列文章嘎然而止!不能不令讀者失聲、茫然……
今日,以故事等靈活多樣的形式挖掘、搶救、宣傳之文,已是武術界新穎文風。由此想到,從此開始,各武術人物都應該寫傳記,以彌補技術著作不方便寫出的內容,那將是對歷史不同側面的紀錄,將是武林的一大財富!無論對前人、對後代,功德無量!
公元二零零六年十月 胡剛
於加拿大首府渥汰華 探微齋
*****
李仲軒自傳
榮辱悲歡事勿追
我的父系在明朝遷到寧河西關,初祖叫李榮,當時寧河還沒有建縣。舊時以「堂」來稱呼人家,我家是「務本堂」,民間說寧河幾大戶的俏皮話是「酸談、臭杜、腥於、嘎子廉,外帶常不要臉和老實李」,我家就是「老實李」。
我母親的太爺是王錫鵬,官居總兵,於鴉片戰爭時期陣亡,浙江定海有紀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爺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爺」,官居三品,他後來發明了「官話合音字母」(漢語拼音的前身),據說某些地區的海外華人仍在使用。
清末時,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長)叫李作(字雲章)是我家大爺,我父親叫李遜之,考上天津法政學堂後,自己剪了辮子,被認為是革命黨,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業。他有大學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說他中了「酒劫」,他的詩文好,但沒能成就。
唐維祿是寧河的大武師,他的師傅是李存義(注1),綽號「單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鍔叫君,刀把叫親,因為刀是張揚的形狀,所以刀鞘叫師,接受老師管束之意,刀頭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義的刀法用刀尖。

李存義像
唐師是個農民,早年練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義拜師,李存義不收,唐維祿就說:「那我給您打長工吧。」留在國術館作了雜役,呆了八九年,結果李存義發現正式學員沒練出來他卻練出來了,就將唐維祿列為弟子,說:「我的東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師,就把家裏的老鼻煙壺、玉碟找出一包,給了唐維祿的大弟子袁斌,他拿着鼻煙壺喜歡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達時說:「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東西都給我了。」是袁斌將我引薦給唐師的。
唐師有個徒弟叫丁志濤,被稱為「津東大俠」。天津東邊兩個村子爭水,即將演變成武鬥,丁志濤去了。動手的人過來,他一發勁打得人直愣愣站住,幾秒鐘都抬不了腳,這是形意的劈拳勁,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釘」在地上。
他「釘」了十幾個人,就制止了這場武鬥,也因此成名。丁志濤有三個妹妹,後來我娶了他二妹丁志蘭為妻。

李仲軒與家人
寧河附近的潘莊有李存義師弟張子蘭(注2)的傳人,叫張鴻慶(注3)。唐師讓我多去拜訪這位同門師叔,並對張鴻慶說:「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勵。」張鴻慶腦子非常聰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於賭術,一次作弊時被人捉住了手,說他手裏有牌,他說:「你去拿刀,我手裏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來,他一張手,牌就沒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腦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轅(字捷軒),隨唐師習武后,寧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個人叫李允田,練單刀拐子,對我師弟周錫坤說:「二先生有什麼本事,見面我就把他敲了。」

李仲軒與母王若南、兄李捷軒
周錫坤就跟他動起手來,用橫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約了東黃莊一個姓侯的人來報復,周錫坤聽到消息就避開了。
他倆四處找周錫坤時,有人告訴我說:「周錫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們找不着周錫坤就該找你了。」我當時正和父親鬧矛盾,心情非常惡劣,從家裏搬出來,住在母親家的祠堂里,我說:「我正彆扭呢,誰找麻煩,我就揍他。」
那兩人最終也沒來找我,周錫坤回來後,也沒再找他。
寧河附近唐師有個師兄弟叫張景富,綽號「果子張」(注4),我們一班唐師的徒弟都喜歡呆在他家,他為人隨和,也願意指點我們。一天我帶了一個朋友去果子張家,正趕上午飯,就在果子張家吃了飯。
我跟這位朋友說過,按照武林規矩,只要來訪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臨走還要送路費。
沒想到這朋友後來自己跑到果子張家吃飯去了,一去多次,還帶了別人。果子張有點不高興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說:「你不是說練武術的,來人就管飯嗎?」
他是借着聽錯了去吃飯。當時寧河發大水,鬧了饑荒,紅槍會(注5)趁機招會眾,參加就管飯。唐師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飢餓參加了紅槍會,他的爺爺和我奶奶是親姐弟。
唐師、丁志濤都對紅槍會反感,說:「不能信那個,一信就倒霉。」我勸過廉若增:「義和團也說刀槍不入,結果槍也入了刀也入了,過多少年了,紅槍會還玩這套,你怎麼能信呢?」他說:「我就是去吃飯。」
紅槍會頭目楊三是治安軍督辦齊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槍,就讓我捐給紅槍會,我認為他們是騙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槍藏在神龕上面,對他說:「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楊三說:「快給我取去。」我說:「現在發大水,過不去。」他又沖我吆喝,那時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時期,我一下就發了火,說:「二先生說在四十里外,是給你面子下台,現在告訴你,就在這神龕上頭,離你五步遠,你敢拿就拿。」——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稱是二先生。
楊三沒拿,轉身走了。後來別人告訴我,有人問楊三:「楊三爺怎麼吃這癟,一個毛孩子都弄不動?」楊三說:「他六叔李牧之十九歲就當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級),現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紅槍會和日本人開了仗,幾乎全部陣亡,河裏都是死屍,寧河話叫「河漂子」。只有一個人生還,叫李銳的十四歲小孩,也是為吃飯進的紅槍會,算起來還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機關槍對着他,他嚇得直擺手,那日本兵也擺擺手,意思讓他快走,他就從死屍堆里走出來了。
可能還有一個。紅槍會的服裝是一身黑,一個生還者躲進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當時日本人開着快艇在河道轉,見到人就掃機關槍。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臨街,是躲不過。
我說:「你呆在這兒必死,翻牆吧,一直向北翻,北邊河面上沒日本人,過了河就安全了。」我教給他做水褲:將棉褲脫下來,吹足氣,紮上褲腳就成了氣囊,浮着過河。也許他活下來了。
因我與父親鬧矛盾,唐師說他有個徒弟叫郭振聲,住在海邊,讓我去散散心,並給我一塊藥做見面憑證,這塊藥就是李存義傳下的「五行丹」(注6)。我拿着藥到了渤海邊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聲不在。
他是此地的請願警,戶籍、治安都是他一個人,當時有一家大戶被匪徒綁票,索要兩千大洋,郭振聲讓朋友湊了十八塊大洋,留了九塊給母親,一個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魚籽村的旅館裏空手奪槍,捉住了兩個劫匪。其中一個竟然是大土匪頭子劉黑七(注7),不遠就是他的老巢,郭振聲知道憑自己一個人,沒法將他押走,就把槍還給了劉黑七,說:「綁票我得帶走,你要不仗義,就給我一槍。」
劉黑七連忙說:「那我成什麼了?」拉着郭振聲講:「你知道我以前什麼人嗎?」
原來這劉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飯莊——登瀛樓的少東家,因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邊作了土匪。他向郭振聲保證,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會受土匪騷擾,還要給郭振聲三十塊大洋,郭振聲為不掃他面子,拿了兩塊。郭振聲之舉,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區十餘年太平。
郭振聲帶着人票回來,全村人慶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時我已經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藥一拿出來,郭振聲就認了我這師弟,給了我五塊大洋。
從大神堂村回來後,唐師就帶我去北京找他的師兄尚雲祥(尚升,字雲翔)。

尚雲祥像
尚雲祥年輕時求李存義指點,練了趟拳,李存義就笑了:「你練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試,李存義沒用手,一個跨步就把尚雲祥跨倒了。尚雲祥要拜師,李存義說:「學,很容易,一會就學會了,能練下去就難了,你能練下去嗎?」尚雲祥說:「能。」李存義只傳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義再來北京,一試尚雲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說:「你練得純。」對別人說:「我撿了個寶。」從此正式教尚雲祥。
唐師與尚師交情深,每年到了季節,唐師都從寧河來京給尚師送螃蟹。尚師屬馬,家住觀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當時已沒尼姑了,住了幾家人,尚師家是東廂房三間,院子很小。
尚師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單廣欽的資助,單廣欽做水果、糕點生意,送錢時常說:「做我這生意的,現錢多。」單廣欽比我大三十歲。尚師開始不收我
|
|
我的姥爺叫王燮,是掌門長子,在清末任左營游擊,官居五品,先守北京東直門後守永定門,八國聯軍進北京時因抵抗被殺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聲譽。唐師把這情況也講了,尚師說:「噢,王大人的外孫子。」
尚師對我好奇,但他從來不問我家裏的事。清末民國的人,由於社會貧窮,大部分是文盲,尚師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養。
我進入尚門後,師兄們跟我說,在北京一座大廟(忘記名字)院子裏有尚師年輕時踩裂的一片磚,因為廟沒錢換磚,這麼多年還在,要帶我去看看。尚師說:「去了也就是瞅個稀罕,有什麼意思?」沒讓我去。
天津沒有尚師的徒弟。我開始住在北京學拳,後來住回天津,早晨出發,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飯後去尚師家,所以我跟尚師習武的近兩年時間裏,大部分是在中午學的。
尚師一天到晚總是那麼精神,沒有一絲疲勞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時候。對於這一點,越跟他相處越覺得神奇。
孫祿堂(注8)的《八卦拳學》上寫道:「……近於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雲祥。其庶幾乎。」(注9)說拳術可以練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的境地,當時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雲祥,找不出別人。
我們這一支的師祖是劉奇蘭,他的師弟是郭雲深。孫祿堂是郭雲深(注10)的傳人,他曾施展腿功,驚嚇了民國總理段祺瑞,被多家報紙報道,有盛名。
我想找國術館館長薛顛比武,被唐師、尚師制止了。後來唐師跟我說:「別比了,你跟他學吧。」聽了薛顛的事跡,我對這個人很佩服,覺得能跟他學東西也很好,唐師對尚師說:「我讓他去見見薛顛?」尚師也同意了。
去見薛顛前,唐師怕薛顛不教我,說:「見了薛顛,你就給他磕一個頭。」在武林規矩里磕三個頭已經是大禮了,而磕一個頭比磕三個頭還大,因為三個頭是用腦門磕的,這一個頭是用腦頂磕的,「殺人不過頭點地」的「頭點地」指的就是這個,要磕得帶響,是武林里最重的的禮節。
我見了薛顛,一個頭磕下去,薛顛就教我了。薛顛非常愛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雙龍眼盼顧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雞形(注11)。
他是結合着古傳八打歌訣教的,蛇行是肩打,雞形是頭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義傳的,是他從山西學來的。其中的蛇行歌訣是「後手只在胯下藏」,後手要兜到臀後胯下,開始時,只有這樣才能練出肩打的勁。簡略一談,希望有讀者能體會。
薛顛管龍形叫「大形」,武林里講薛顛「能把自己練沒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時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裏有他,但確定不了他的角度。這次一連教了幾天,我離去時,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名《象形術》(注12),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試手,一晃就倒。回來後,尚師問:「薛顛教了你什麼?」我都一一說了。
第二次見薛顛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裏練了一天武,他看了後沒指點,說:「走,跟我吃飯去。」吃飯時對我說:「我的東西你有了。」——這是我和薛顛的最後一面,薛顛沒有得善終,我對此十分難過。
我二十四歲時父親死了,我卻不能回家。二十五歲時,天津財政局局長李鵬圖叫我到財政局工作,也不給我安排事情做,只讓我陪他去看戲、吃飯,我一看這情況,等於做了保鏢。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實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練武。
我以前是個少爺,練武后穿着就不講究了。一天到捐物處去辦事,我戴個美國鴨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還破了個洞,漏着棉花。當時天津的捐警名聲不好,幹什麼都是白拿白占。捐物處門口是個斜坡,我蹬着自行車直接上去了,到崗亭,一個捐警一腳揣在我的自行車上,我摔倒後,他跑上來抽了我一個耳光,還罵:「打你個××,誰叫你上來的。」
我起來後,說:「你會打人,我也會打人。」拎住他抽了四個耳光,他就叫喚開了。捐
|
|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腦袋——只要他們想到這點,就會住手。」但他們想不到,掉了帽子還追我。捐警小隊長,他拎着槍下來,看那架勢要崩了我,但他認出了我,就把那幫捐警轟跑了,對我說:「您沒在我們這打人,您給面子了。」我摘了十幾頂帽子,隨抓隨掉,還剩下四個,就把這四個帽子遞給了他。
捐物處處長叫齊體元,李鵬圖給他打了電話,說:「二先生沒打壞你們一個人,這是給你齊五爺維住了體面,你也得給二先生個體面吧?」齊體元說:「行,二先生還給我們四個帽子,我們就開除四個捐警吧。」捐警外快多,被開除的四個人非常恨我。
這件事出在我身上,我覺得不自在,李鵬圖也看出我不願做保鏢。我喜歡武術,但我做不來武師,我開始絕口不提我練武了,後來到天津北站當了海運牙行稅的卡長,離開了財政局大樓,更是沒人知道我練武。
我三十出頭時,到宏順煤窯住過一段時間,礦工中有個五十多歲的通背拳(注13)武師叫趙萬祥,能把石碑打得「嗡嗡」響,不是脆響,能打出這種聲音,通背的功夫是練到了家。
他帶着徒弟在煤窯門市部後的空場裏練,礦工們吃飯也多蹲在那吃,我有時出門能碰上,我從未表露過自己的武林身份,不看他們練拳。他們都叫我李先生,非常客氣。我大半輩子都是旁觀者,這位趙拳師和我算是個擦肩而過的緣份。
只是在我大約37歲時,有一件武林糾紛找上了我。燕青拳名家張克功年老後,從東豐臺遷到了盧台,收了幾個小徒弟,他是唐師的朋友。當地的大拳師是傅昌榮(注14)的傳人王乃發,他的徒弟把張克功的匾給偷跑了。
唐師去世的時候,囑咐我照顧他的老朋友們,我就找王乃發要匾。王乃發說:「你來,我要給面子。你提唐師傅,我更得給面子。摘匾的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去,我也下不來台呀。」我說:「要不這樣——」我就給王乃發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解放前夕,我來北京找到了會計師的工作,那時尚師早已逝世,當年舊景只能令人徒生感傷,無心與同門相敘,從此徹底與武林斷了關係。
注釋:
1、李存義(1847年——1921年),字忠元,清末深州(今深州市)南小營村人。20歲時向劉奇蘭、郭雲深學形意拳,從董海川學八卦掌。
光緒十六年(1890年),李存義在軍人劉坤一帳下教士兵練武,屢建功績。後到保定開萬通鏢局。
八國聯軍侵華時,53歲的李存義參加義和團,奮勇殺敵,每戰必先。他曾率眾夜襲天津老龍頭火車站,痛殺守站俄兵。
民國元年(1912年),李存義在天津創辦北方最大的民間武術團體——中華武士會,親任會長,教授形意拳,創編十六路的《拳術教範》,編寫《刺殺拳譜》,教授門徒數百人。
民國十年(1921年),因病逝世,安葬於南小營村,終年74歲。
2、張子蘭(1865——1938),又名張占魁,字兆東,生於河北省河間縣後鴻雁村。1877年結識劉奇蘭弟子李存義,並義結金蘭。經李推薦拜師於劉奇蘭門下。
光緒七年(1881),在京結交八卦掌宗師董海川的弟子程庭華。1882年冬,董海川去世,張占魁墳前遞帖,程庭華代師傳藝。藝成後,武林名號為「閃電手」。
1900年後,在天津歷任縣衙任捉拿匪徒的營務處頭領。1911年,參與創建天津中華武士會,並執教。1918年9月,攜弟子韓慕俠進京,參加在中山公園舉行的「萬國賽武大會」,韓慕俠挫敗俄國大力士康泰爾,轟動全國。
3、張鴻慶(1875——1960年)曾用名張庚辰,天津寧河潘莊人,二十多歲到天津劉快莊劉雲濟學習洪拳,曾隨李存義學習形意拳,後被張子蘭收為正式弟子。
4、張景富以炸油條為生,是曾任清宮武術教習的申萬林弟子。一次,族人來找申萬林要錢修老屋,在申萬林不知的情況下,張景富拿出所有積蓄,為申萬林家族蓋了三間青堂瓦房。感動了申萬林,將醫藥秘本傳給張景富。
5、紅槍會是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活躍在冀南一帶的農村會道門,後發展為幾十萬人的武裝組織。
6、五行丹:形意門秘傳丹方,在內功修為上有特殊作用,但製作困難,一般煉成藥膏,用於外敷,也是形意門嫡傳弟子的身份證明。
7、劉黑七從1915年起聚眾作惡,為害29年之久。匪眾最多時逾萬人,流竄山東、河北、熱河、遼寧、安徽等十餘省,所到之處,搶劫財物,殺人如麻,官府軍閥奈何不得。山東是劉黑七為禍的重災區。
8、孫祿堂(1860—1933年)名福全,字祿堂,號函齋,武林名號「活猴」。完縣東任家疃人。
形意拳從學於李魁元,八卦掌從學於程廷華,太極拳從學於郝為真。1918年孫祿堂將形意八卦太極三家合冶一爐,創立了孫氏太極拳。同年徐世昌聘孫祿堂入總統府,任武宣官。有「虎頭少保,天下第一手」的稱譽。
孫祿堂晚年著書立說,留有《拳意述真》、《八卦拳學》等拳論,並擊敗俄國格鬥家彼得洛夫、日本天皇欽命武士板垣一雄。

孫祿堂像
9、《八卦拳學》這一章節名為「陽火陰符形式」,全文如下:
陽火陰符之理(即拳中之明勁暗勁也),始終兩段工夫。一進陽火(拳中之明勁也)一運陰符(即拳中之暗勁也),進陽火者,陰中返陽,進其剛健之德,所以復先天也;運陰符者陽中用陰,運其柔順之德,所以養先天也。
進陽火必進至於六陽純全,剛健之至,方是陽炎之功盡(拳中明勁中正之至也);運陰符,必運至於六陰純全,柔順之至,方是陰符之功畢(拳中暗和之至也)。陽火陰符,功力俱到,剛柔相當,建順兼全,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一氣,渾然天理,圓陀陀(氣無缺也),光灼灼(神氣足也),淨倮倮(無雜氣也),赤灑灑(氣無拘也),聖胎完成,一粒金丹寶珠懸於太虛空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動;常應常靜,常靜常應。
本良知良能面目復還先天,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也,再加向上工夫,煉神還虛,打破虛空脫出真身,永久不壞,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進於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矣。
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雲祥。其庶幾乎。
10、孫祿堂是郭雲深的徒孫,並得到了郭雲深的親自指導。
郭雲深(1820——1901)名峪生,河北深縣馬莊人,「神拳」李洛能弟子,
在武林有「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美譽。1877年,為六陵總管譚崇傑聘為府內武師,進而為清廷皇室載純、載廉等人的武術教師。晚年著書立說,留有《解說形意拳經》。
11、形意拳五行和十二形為基本拳法,五行對應金木水火土,為劈崩鑽跑橫五拳,十二形對應動物,為龍、虎、猴、馬、雞、鷂、燕、蛇、鼉、駘、鷹、熊。
12、正式出版書名為《象形拳法真詮》。
13、戰國時代鬼谷子於雲蒙山中觀察通臂猿動作所創,以衣服練功,講究手掌黏着衣服發勁,練時黏自己衣服發勁出響,用時黏敵人衣服發勁。在演練中啪啪見響,每一聲響,都與技擊有關。所以通背拳不許光膀子練,必須穿衣,通背拳不出響,猶如行船沒有漿。
14、傅昌榮(1885——1956年),又名傅劍秋,河北寧河人。1908年前後,投身形意拳大師李存義、八卦掌名家劉鳳春門下,藝成後出任張作霖私人護衛隊長。1927年走訪武當山,與徐本善道長互換拳術。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