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二戰時期一名普通的美國大兵,卻成為中共黨史上不能不記述的一個人物,原因有二:一、他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籍人士;二、他是在華外籍人士中境遇最不幸的一個。
他的英文名字是Sidney Rittenberg(李騰伯格),出生於美國南卡州。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被迫捲入二次大戰。
1942年,21歲的李騰伯格加入美國陸軍,被派往史丹福大學陸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
1945年9月16日,二戰結束後一個月,李騰伯格和戰友乘坐美軍運輸機,從印度阿薩姆邦飛越「駝峰航線」來到中國西南重鎮昆明。
任何人也不會料到,這次落地,竟會讓李騰伯格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待就是整整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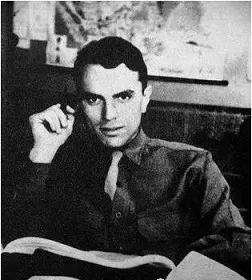
他被分配到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負責調查美軍在昆明的違法行為並向遭受損失的當地中國人進行賠償。
在這裏,一個書店老闆給他取了中文名字:李敦白。也是在這裏,他開始接觸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其中包括「傳說中」的廉潔並且充滿理想的共產黨人。
他很快就結識了幾個中共地下黨員。從小根植於心的美國的民主觀念,使他對壓制言論、抓捕異己的行為深惡痛絕,因此那些躲躲藏藏的地下黨引起他極大的同情,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給這些人送去緊俏物資,駕駛美軍吉普車把上了黑名單的地下黨員轉移到城外安全地帶。
1945底,美軍完成在昆明的歷史使命回國,而此時已經脫胎為李敦白的李騰伯格被一種激情或者說誘惑所掌控,他不願回國和家人團聚,他要親眼看看甚至親身參與中國的未來。
於是他通過昆明的地下黨和上海的地下黨取得聯繫並認識了宋慶齡,由宋慶齡給他安排在「聯合國善後經濟總署駐華辦事處」作經濟觀察員,負責將救濟糧食送往包括中共控制區在內的受災地區。
這份工作使李敦白興奮異常,因為這不僅使他脫離了美國軍隊,不用隨軍回國,而且能夠以運送救濟物資的名義進入中共控制區。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食到中共控制的湖北「中原解放區」,在那裏他結識了李先念、王震等人。他真誠地希望國共不要爆發內戰,因此將國軍的一些調動情況告知李先念,這使他取得了李先念的信任。
之後,他又前往南京拜會了周,在周的介紹下,他輾轉來到中共在華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張家口,見到了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
聶榮臻對他熱情款待,並力邀他留下來協助工作。聶榮臻說,等共產黨掌權後,首先要和美國修好,因為毛希望能得到美國貸款進行戰後重建,所以他們正在籌劃成立一個英語電台,以便向美國人民表達訴求,但是現在缺少一個精通英語的人幫助他們矯正文法文體,而李敦白正是最為合適的人選。
聶榮臻是中共的高級將領,他的話李敦白當然深信不疑。能夠在中美人民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這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啊!李敦白當即決定留下來,幫助新華晉察冀分社開通了英語廣播,並擔任翻譯、修改和播音工作。
然而,電台僅僅開通了幾個月,由於傅作義的部隊開始進攻張家口,形勢嚴峻,於是聶榮臻派人將李敦白護送至延安。
到延安後,李敦白終於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
與毛深談後,他以李先念和王震作為入黨介紹人,由毛、劉、周、朱、任這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親自批准,成為中共第一個外籍黨員。
那時的李敦白可謂是激情滿懷、熱血沸騰。
可是,時隔不久,他就遭遇了當頭一棒。
1948年底,在莫斯科為蘇聯政權搖旗吶喊近30年的美國左翼作家斯特朗發表文章,聲稱「中國革命並沒有照搬蘇聯模式」,這一言論惹惱了斯大林,於是她30年的犬馬之勞被一筆勾銷,克格勃以間諜的罪名將其逮捕,隨後將她驅逐出境。
斯特朗訪問延安時,李敦白曾經做過她的翻譯,於是蘇聯政府致電中共,將李敦白劃入「斯特朗國際間諜案」,責令抓捕李敦白。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一份「執行特殊任務」的通知,在他趕到指定地點時被以「國際間諜、美國特務」的罪名抓捕。
由於他的美國國籍,如果事情泄露出去,會招惹很大的麻煩,因此他被秘密關押在北平郊區一間窗戶都被全部封死的小屋裏,無論他如何辯白都無濟於事。
1950年,他被秘密轉移到北平第二監獄。
1953,斯大林亡故。斯大林一手炮製的很多假案開始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斯特朗國際間諜案」。
1955年4月4日,一個陌生人走進關押李敦白的牢房,向他宣佈:「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調查你的案子,發現你是一個好人,在此向你道歉。」
沒有經過任何審判,莫名其妙被關押,並且一關就是漫長的6年,而釋放他時,也是如此的輕描淡寫,如此種種,會促使這個曾經就讀於三所美國大學的年輕人「悟」到什麼嗎?——很遺憾,沒有。
早在他被釋放的前兩年,監獄長曾和他有一次談話,告訴他:「如果你撇清和中國的所有關係,你將被獲准回到美國。」而他竟然回答:「我不回美國。我要在獄中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現在即使被關在監獄裏,這也是我們自己的監獄。」
不能不承認,那時的李敦白不僅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摻雜了西方觀念的理想主義者。
出獄後,他被分配到廣播事業局工作。
也許是因為他的美國人身份,也許是為了彌補他那6年無妄之災,他受到了特別優待:獨立辦公室、專車、高薪——他的月薪高達600元,是普通工人的15倍之多。這使他過上了在當時的中國堪稱富翁的生活。
然而,這樣的生活並沒有使李敦白感覺自在,恰恰相反,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心中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中的官僚等級制度越來越頻繁地發生衝突。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這群人有特別的住房、特別的伙食,還有專車……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實也成了腦滿腸肥的一員,我感到深深的後悔和自責……難道就這樣下去嗎?我一直自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一個願為人民服務的人。難道我願意晚節不保,讓自己蛻變為特權分子?我一向鄙視偽君子和騙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他決定要有所改變。改變不了別人,就先改變自己。
他搬出了獨立辦公室,將家中的紅木古典家具全部捐給博物館,並且向上級要求取消專車、工資減半。
然而,他的要求一一遭到否決。當他自作主張,不坐專車改騎自行車上班時,立刻有安全部的人來找他談話。
以上種種,為他以後在文革中的表現埋下伏筆。
1966年,文革爆發。
李敦白有一種被解放的狂喜。他發瘋似的投入到那場運動中。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感受到了早年「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時的久違的言論自由」。
他參加了包括王光美在內的很多大人物的批斗大會,組織並擔任「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頭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一時間成為聞名全國的風雲人物。

他痛恨官僚體制,他認為只有將一切都推倒重來,才能建成他所嚮往的「自由、平等」的社會。
然而,「解放的美好感覺」沒有維持多久,他就目睹了醜惡的一面。他看到,所謂「自由」,並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僅僅是造反派的自由,甚至僅僅是各個造反派自己一派的自由,對於其他人、其他派別,不僅沒有任何自由可言,就連財產和生命都可以任意剝奪。——這完全違背了他早已根植於心的自由的理念。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文革不僅帶來了革命小將,更是放出了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蓋下,正進行着一場難以防備的醜惡暴力。」
在參加陸定一、吳冷西、周揚等人的批斗大會上,被批鬥者被打得嗷嗷尖叫,坐滿北京工人體育館看台的群眾發出痛快的笑聲。李敦白寫道:「整個批鬥的殘忍暴戾讓我生厭。我轉身問穆欣(《光明日報》總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這樣使用暴力對嗎?』穆欣狡猾地一笑說:『這不算真正的暴力。』按照穆欣的說法,敵人這樣做才算暴力,群眾這樣做就不算?我覺得這是一種自私的想法。而下次我在體育館再見穆欣時,他自己卻成了批鬥的對象,跪在那裏『坐飛機』。」
李敦白向江青抱怨:「自從接管了這裏,造反派已經染上官僚作風,居高臨下了。他們取得了批評的權利,現在卻拒絕給他人批評的權利。」江青的眉毛往上一挑,就在那一瞬間,李敦白感覺到自己觸犯了江青。
於是,李敦白遭受一生中的第二次大棒重擊已經不可避免。
1967年9月,李敦白再次被扣上「國際間諜、美國特務」的罪名。
1968年2月21日,他遭到逮捕並被投入秦城監獄。
依然是沒有審判,依然是單人監禁,連罪名都和上次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時間,這次他被關押了將近10年之久。

1976年的一個晚上,李敦白回憶:「自從我入獄後,幾乎從來沒有聽到過監獄外的田野里傳來任何聲音。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聽到鑼鼓喧天的音樂透過鄰近公社的大喇叭傳過來……又過了幾個星期,有一天我聽見有個女人在叫,這個聲音很熟悉,又高又尖。這個聲音我有9年多沒聽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萬確,是江青!」
那一刻,李敦白真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他說:「喜劇的意味已經消失,反倒荒誕悲哀。我認為我們可以在混亂中重生,創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全罩上了陰雲,我們沒有征服混亂,反而被它蠶食着。」
1977年11月,李敦白走出監獄。
十年的與世隔絕,使他連語言表達能力都出現了障礙。
他在中國生活了35年,其中竟然有16年是在單人牢房裏度過的!
那麼,經過了如此漫長而難以忍受的磨難,他總該反思和「悟」到些什麼吧?
大夢一場,他終於醒了。——1980年,李敦白復歸李騰伯格,攜妻兒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故國美利堅。
2019年8月24日,這位坎軻一生、命運多舛的老人在華盛頓州福克斯島上的家中去世,享年9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