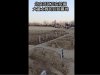鄉村的集市貿易,俗稱廟會,均有固定的時間,如逢陰曆三六九、二五八;有固定的地點,通常設在交通便利的鎮上或較大的村莊。廟會當天,從四面八方村落趕集的農民聚會在一起,出售自家的農副產品和手工藝品,購買自己需要的大大小小商品,了解各方面信息,品嘗各種美食小吃,享受文化娛樂活動以及特有的廟會氣氛。漢民族農耕文明源遠流長,集市貿易恐怕也有數千年的歷史。
小時候,筆者經常跟隨父母趕廟會。家鄉最大的廟會要算賈村鎮廟會,距離我村10里路。每逢廟會,早早的,我們就興沖衝上路了,有時父親騎自行車帶上我,有時我跟母親步行。一路上,男女老少,絡繹不絕,有肩挑背負的,有騎自行車的,有推拉小平車的,還有趕着騾馬豬羊的,人人臉上洋溢着燦爛的笑容,充滿輕鬆喜慶色彩。
廟會最圓滿的時候,大約在上午11點左右,賈村鎮的東西南北幾條街道,被擺攤設點和趕集人擁擠得滿滿當當。廟會上設有食品市,賣油糕、涼粉、醪糟、麻花、羊雜割等美食;有牲口市,從體型高大的騾馬,到吱吱亂叫的豬娃,應有盡有;有木材市,大料小料,桌椅門窗,一應俱全;有婦女市,小腳老太太和年輕姑娘擺出自己織的土布、繡件、針頭線腦……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空氣中飄散着各種美食饞人的味道,夾雜着各種響亮的叫賣聲和喧嚷聲,每一次廟會,就是當地農民生活中的嘉年華。
鄉村廟會有時還請來戲班子助熱鬧。不過,大多趕集社員沒心思看戲,頂多瞄一眼戲台上有沒有名角兒,便忙自己的事了。廟會上另有不少看似平常卻又有趣的情景。比如在牲口市,有好幾位活躍的中老年男人,在人與牲口中間穿來梭去,或摘掉頭上的草帽遮掩,或伸進衣袖間,或撩起衣襟下擺,悄無聲息地跟他人捏手指頭,「眉目傳情」,摸來捏去,一樁牛馬買賣生意便談妥了。這些人的職業叫牙客。
少年不知愁滋味。每一次隨父母趕集,他們賣什麼,買什麼,我一點也不操心。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一次父母會給我買什么小吃。或一碗醪糟,或一盤炒粉,花上幾角錢,坐在攤販的小板凳上,細細品味,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有一次,我在廟會上走丟了,釀成一起不大不小的風波。
那時我四五歲,父親一人帶我上賈村鎮廟會。中午吃過美食,我犯困了,父親就把我安置在街面一個熟人的鋪子裏睡覺。我睡着後,他自己出去辦事了。一覺醒來,我發現屋子裏沒人,便溜下炕,獨自出門,上街尋找父親。擁擠的人群裹挾着我,也不知道東西南北到了何方。等父親辦完事回到鋪子,發現我不在了,詢問房主,房主也回答不上來。
「一個四五歲男孩丟失了!」頓時成為廟會上的一大新聞。父親是當地有名的醫生,還擔任鄉衛生院院長,熟人多,一傳十,十傳百,好多熱心人分頭在廟會上幫忙尋找,還有人急急趕回村里,看我是不是被熟人領回家了。在家的母親聽說我丟失了,焦急地哭天抹淚。從我們村,到賈村鎮廟會,以及沿途,人們都在議論這檔事。
我在街上找不見父親,望着周圍黑壓壓的人群,嚇得哇哇大哭。一位擺攤賣土布的老太太瞧見了,一面哄我,一面詢問:
「這小娃,你叫啥名字?」
「我叫馮印譜。」
「你是哪個村的?」
「我家是……丁樊村。」
「你爸叫啥?」
「我不知道,我爸是醫生……」
也算湊巧,我的伯父也來趕集路過此地,聽見「丁樊村」「醫生」,扭頭一看是我。伯父立即帶我回家,並托人轉告我父親「孩子找到了」,一場風波最終化險為夷。雖說虛驚一場,但20世紀60年代初鄉村的社會風氣可見一斑。
等我上了小學,「文革」開始,父親就很少領我趕集了。他被錯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驅趕回生產隊勞動改造。到了20世紀70年代,農村的廟會已不復往日繁華熱鬧了。父親跟社員們在自留地里栽種了旱煙葉,曬乾的煙葉要拿到廟會出賣。1974年,我在離家30里的閆景村閆景中學讀高中時,家裏有一輛自行車,但我上學很少騎車,每個周末放學上學回家全要靠步行。假如我騎自行車上學的話,整整一周,自行車都在宿舍閒放着。這樣,父親就不能騎自行車趕廟會賣煙葉了。
有一天,閆景村逢廟會。中午休息時間,我上街閒逛,跟前來趕集賣煙葉的父親不期而遇。父親在街邊地麵攤開一塊包袱,上面放着兩捆煙葉,自行車倚靠在牆角,車子後座上綁着尚未擺出的煙葉。父親口乾舌燥,唾沫飛濺地向來往行人顧客兜售煙葉。我站在父親身旁,一邊詢問母親和家裏的情況,一邊感覺臉紅心跳,十分窘迫,尤其懼怕過往的老師和同學,瞅見我有這樣一位賣煙葉的父親。
父親是被打入社會最底層的黑五類分子,是階級敵人。那個年月,攤上這樣一位父親,做子女的是相當沒面子的,相當丟人的。而且,我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渴望做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多少次在入團申請書上莊嚴表態,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正在接受學校團組織對我的嚴峻考驗。
太陽當頭照,父親額頭浸出一顆顆汗珠。這時,父親說:「娃,你幫我照看一下攤位,我去上個茅房。」父親擦着汗水匆匆走了,我站在父親的位置,臨時充當賣煙小販。有的顧客過來詢問:「這煙葉多錢一斤?」我機械地回答,聲音只有對方才能勉強聽見。有的顧客過來翻看旱煙葉,我不知該說啥才好。在我身邊,兜售其他土特產的攤販扯破嗓子叫賣,竭力炫耀自己的商品如何價廉物美。我不敢抬頭,生怕看見熟悉的老師和同學。我更不會叫賣,也不好意思叫賣。我盼望父親快點回來,又希望能夠替父親賣出一點煙葉。時間一秒秒過去,父親回來了,他說:「你快回學校吧,別耽誤了上課。」我點點頭,心中不舍卻又快步跟父親告別。
坐進學校教室,我才感到非常後悔,非常內疚:大熱的天,我怎麼沒想到給父親送去一杯開水呢?初步體驗了一下父親趕集賣煙葉的滋味,我痛恨自己無能,又死愛面子,沒能幫父親賣出一兩煙葉。而父親呢,一年中要趕無數個這樣的廟會,起早貪黑,忍飢挨餓,來回奔波,賣完一包裹又一包裹旱煙葉,然後用賣煙所得供我讀高中,給家裏買糧食,買油鹽醬醋。父親跟所有的農民一樣,在參加集體勞動之餘,渴盼着廟會,依賴着廟會,同時也維護着廟會,廟會已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鄉村廟會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狀況的晴雨表。
每每想起閆景村廟會那一幕,我都為自己因政治狂熱而泯滅了人性,感到深深的愧疚,對父親有一種難以洗刷的負罪感。
可是,這樣的廟會仍然逃脫不了政治的干預。農業學大寨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報紙廣播宣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小生產每日每時都在滋生資本主義」。除了學大寨,報紙還宣傳過遼寧省河套地區取締傳統集市,創辦「趕社會主義大集」的經驗。當時,我們運城地區革委會「一把手」是從昔陽縣調來的「昔陽幹部」,此人頑固地推行極左路線,下令在運城地區13個縣全部取締鄉村集市貿易。
剛開始,社員們不理這個茬,仍然攜帶農副產品趕廟會。縣、鄉革委會執行上級命令,派出一隊隊基幹民兵,開着卡車,奔赴各個廟會,手持步槍,蠻橫肆意地攆集。致使趕集的社員如驚弓之鳥,跑得快的溜走了,跑得慢的就被凶神惡煞的民兵將農副產品沒收掉,並把他們關押在公社大院,責令各大隊幹部來公社認人、領人,領回大隊後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接受檢查批判。幾年間,往日繁榮、祥和、自由、歡樂的廟會,被折騰得雞飛狗跳,風聲鶴唳,最終一片肅殺、銷聲匿跡了。
在中華大地延續了數千年的廟會,即便在戰爭年代也沒有中斷過,在和平時期,竟然採取宣傳加暴力雙管齊下的手段,遭到無情扼殺。這難道也是「文化大革命」結出的碩果?這難道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這難道也是解放生產力的標誌?這難道也是勞動人民翻身做主、揚眉吐氣?
廟會沒了,圍繞「以糧為綱」,自留地不允許栽種旱煙葉,父親也不用起早貪黑趕廟會了。那些馬列主義喊得震天響的領導,只記住生產能夠產生財富,忘記了流通也能夠產生財富,消費同樣能夠產生財富。堵死了集市貿易這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並沒有越走越寬廣,越走越富裕,反而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1978年,我考上大學時,我們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分紅8分錢。進大學後享受國家助學金,在填寫家庭經濟狀況表格上,學校有關部門看到一個勞動日分值8分錢,大惑不解,以致懷疑我填寫的真實性,特此給我家鄉的公社發函調查,公社回函證明確實如此,我才得以享受每個月21元錢的助學金。這筆助學金不僅夠用伙食費,而且還有結餘錢可以買書和日用品。
全國鄉村集市貿易得以恢復,還應當歸功於我家鄉的幹部群眾和新聞媒體。
1978年7月21日,《光明日報》刊發一封讀者來信《農村集市貿易應該恢復》,寫信人是山西省運城地區稷山縣武勤英同志。他在信中反映,粉碎「四人幫」已經1年多了,當地的集市貿易仍未恢復,街上仍然貼着取締集市貿易的「十大好處」一類標語,群眾趕集仍然遭到工作人員的驅逐(當地群眾稱之為「攆集」),給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副業生產帶來極大困難。他呼籲:肅清「四人幫」的影響和流毒,恢復農村集市貿易。
8月4日和8月18日,《光明日報》又連續刊登了來自運城地區讀者的兩封來信:《陳壽昌的信說得好》《不能再「攆集」了》,並加了編者按。新華社對後一封來信和編者按發了通稿,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予以播出,《人民日報》也全文轉載。8月29日,《山西日報》登載了新華社轉載的《光明日報》讀者來信。山西省是「文革」中推行極左路線和學大寨運動的「重災區」,這些來信在全省基層幹部和群眾中反響強烈,迫於輿論壓力,幾個月後,運城地區最終恢復了集市貿易,傳統廟會重新煥發了勃勃生機。
同樣是制定政策,一個「封閉」,害苦了百姓;一個「開放」,富裕了農民。這期間,二元戶籍制度管轄下的鄉村農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筆者年過花甲,久居都市,常常懷念農村集貿市場那熙熙攘攘的氛圍,懷念那坐着小板凳的涼粉攤、醪糟攤,懷念那曾把我丟失了的傳統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