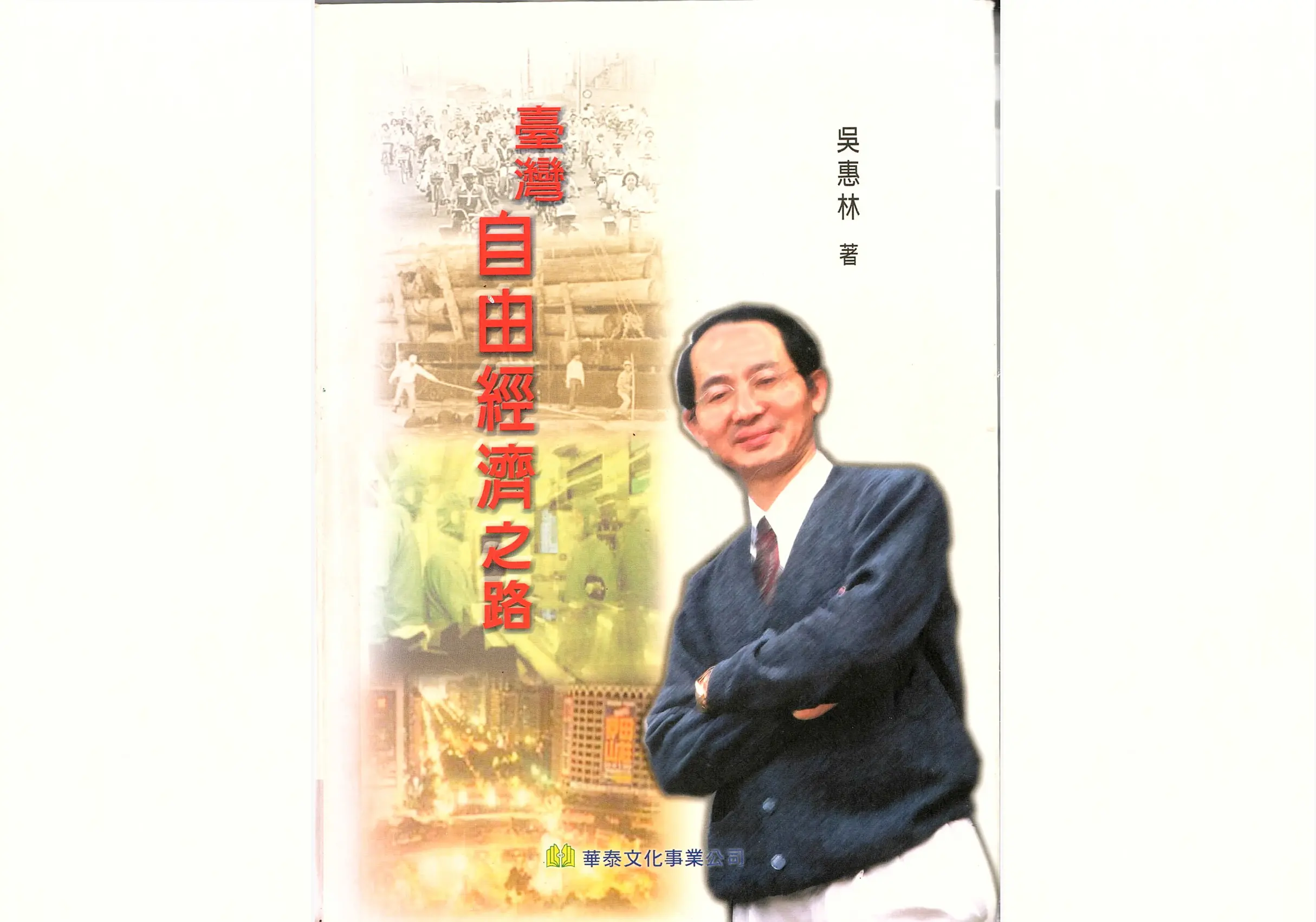
作者提供
背景說明
本文原刊於《主計月刊》549期(2001年9月號),為二十世紀末出現的失業升高現象尋找源頭,文中所用的論點可追溯自1988年明文之記載,年代雖異,然基本觀念卻相同,而當初的論點在21新世紀來看又更顯現其真。
自1996年以來,台灣的平均失業率就呈現節節升高現象,而起先引起關切的是中高齡失業,到了2001年,失業人口的年齡下降,連中壯年承擔家計者也逐漸受到波及,失業問題更成為台灣首要課題,於是失業成因的探討,如何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案等等的討論可說無日無之。
失業是勞動市場供過於求現象
其實,不管是如何歸類失業,無論由何種角度切入探討,失業現象終究是勞動市場裏「供過於求」的現象。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或者沒有任何「交易成本」存在,那麼,讓市場自由運作,均衡是時刻存在的,亦即無所謂失業問題。可是實際人生里,交易成本俯拾即是,這也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 H. Coase)呼籲經濟學家,趕緊走出交易成本為零的完全競爭象牙塔世界,擁抱滿是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以尋求解決問題良方的用意吧!
既然交易成本充斥,「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就是常態,更不能以此名詞本末倒置地指責市場機能的失靈,反而應該找出各種交易成本而去除之。准此,各種規則、制度,以及各色各樣的組織之出現,本意即在降低交易成本,可是實際人生里,往往到處見到適得其反事例。這些使成本不滅反增的制度、組織,如果是「自發性」的,很快會被淘汰,但若是「做成的」,卻存在高度僵固性,而此種做成的秩序、制度和組織,背後就是「公權力」在支撐,也就是政府這個特殊組織在操弄,骨子裏則是某些「人」或「人組成的團體」在主導,更深層的內涵就是「私利」在作祟,亦即「權力」的奪取。除非「人心淨化」、「無私無我」的倫理道德可以普及,人人自動自發「先他後我」,否則愈多的法令規章,恐怕只會淪為「爭權奪利」的鬥爭工具而已。
因此,理論上政府彌補市場失靈,讓交易成本降低很有道理,但實際上由於「人心、道德的沈淪」,非但市場失靈的程度未能減少,反因「政府失靈」的產生,讓交易成本更高,此由「尋租」(rent-seeking)或「鑽營」行為俯拾即是已可看得清楚、明白。而這些「租」或「獨佔利潤」的產生並非源於市場的自然獨佔,而是「管制權力」所營造的「人為獨佔」,勞動市場裏的勞工法令就是如此。
失業既是勞動市場內「供過於求」的現象,要讓它消失,或者勞動需求增加、或者勞動供給減少、或者兩者同時發生、或者勞動需求和供給都增加但前者的增量高於後者等等,都可將「超額供給」吸蝕掉。這樣的演變情形,利用標準經濟學或勞動經濟學中的簡單供需圖形,在黑板上繪圖就一目了然。如果供需線都不動,藉由價格的「靈活移動」就可消除,問題是:需要多長時間?這也就是標準的「交易成本」課題。其間出現了所謂「價格僵固性」現象,只是一般都不探討此現象產生的源由,更有甚者,還百般維護該僵固性的存在,或許更創造出僵固性,而「最低勞動條件,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然,如上所言,我們也可在價格僵固下,以需求線右移或供給線左移,或者兩條線都右移,但需求線移得多來消除勞動供給過剩或失業現象。可惜的是,這些做法要嘛成本相對高、要嘛時間比較長。即使如此,還是得問:這種調整到底是靠政府政策較有效,或者依恃市場較可靠?
制度、知識資產與失業
這些問題都非三言兩語、也不是能明確作數據估算來回答的。不過,我們倒可從華裔全球著名學者楊小凱的一篇《減少失業的政策》短文大致談一談。該文分析的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近二十年之後的情況,他以「廠商理論」解析,認為自由市場上僱傭關係可用來對企業家活動創造的組織經濟之無形資產間接定價。他說企業家的組織思想可以不在市場上直接買賣,而是通過僱傭人實現這些思想,其成果以有形產品的形式銷售,銷售收入減去僱傭各種要素的費用,剩下的收入就是企業家的間接價格。如果這個企業家的主意是壞的,則此剩餘收入就是負的,企業家就會破產,若是好主意,這剩餘收入就可能使企業家發大財。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家都不願當企業家去僱人,而希望等人家來雇,就會產生失業。基於這樣的體認,楊小凱認為解決失業問題,一定要從研究為什麼大家都不願當企業家創業着手。
我們可以由兩個層次來解讀楊小凱的論點,一是將企業家狹義視為生產者,如此企業家的角色就是勞動市場中的需求者。那麼,如果人人爭先恐後的想當企業家,就表示工作機會源源不斷會出現。楊小凱比較中國的失業與西方先進國家失業之間性質的差異,發現以美國、澳洲為例,要當企業家創業在這些國家是非常容易的,在這些地方,辦企業不需任何人批准,從事外貿買賣也不需要許可證,借錢創業只受本人信譽限制,基本上不愁在市場利率條件下借不到錢。這種說法即謂管制愈少的國度,創業家就愈多,而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的地方比共產統制經濟體,企業家創業當然容易許多。這在台灣也很容易了解,台灣的中小企業林立,特別是1970~90年代,它們在地下經濟里自由自在地存活、發展,而「寧為雞首,勿為牛後」就是人人爭着當企業創業家的鮮活寫照呢!
另一個看待「企業家」的方式是將「凡能創造剩餘價值者」皆包含在內,而且這種行為必須在市場公平競爭和行為人以正當方式下的作為。如此,無論是僱主、受僱者或任何身份者,只要能有「收入大於機會成本」的作為,就是具創新能力的企業家。換個角度看,只要行為人將自己的有限寶貴資源(自有或借來都涵括在內)作最有效率的發揮,創造附加價值就不成問題。一個社會中企業家愈多,附加價值就愈大,生活福祉就愈高,而失業也就愈不會是問題。
不過,不論是狹義或廣義的企業家概念,都存在「何種環境」最合宜的課題。在中國那種經濟體制里,到處存在的批准制度、許可證制度,使得人民不願或不能當企業家。就這種管制言,如台灣這類的自由經濟體,似乎也有不少,只是比起統制經濟來,程度低很多而已。不過,即使能讓市場充分自由運作,還是會因某些交易成本的存在,因而失業終究是難免的。楊小凱以勞動分工演進的一些特點來解釋,譬如:在生產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之間有很細密分工時,生產耐用品的行業會產生「周期性失業」。當分工水準低、大多數人自給自足,找不到專業化的就業機會時會有失業或隱藏性失業;而當分工水準很高時,由於大分工網路造成協調失靈的風險高,加上轉業困難也會造成失業。不過,在經濟起飛、分工演進加速的開發中國家,失業就不是個大問題,反而會有勞力短缺現象出現,台灣在1985年的時期就是如此。不過,儘管楊小凱以亞當.史密斯的分工論來解析失業,但還是將加速分工演進的關鍵條件歸給「降低交易成本」,他特別指明是政府管制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而如何創造易於創業的條件則是另一重點。
其實,不論由勞動市場的供需、抑由楊小凱的企業家和僱傭關係角度分析,本質上都是「人的行為」,關鍵則在外在環境和行為人本身之特質,特別是失業課題的當事者就是人。一個人結合各種生產資源(包括他自己)從事生產行為就是業者或勞動需求者或者是一般所稱的企業家,而只提供自己單純當生產資源者就是勞動供給者或受僱者。
我們進一步可以這樣說,在一個經濟體系里,勞動供給者扮演了兩種角色,一種是勞務生產因素的提供者,另一種是產品的需求者,也就是消費者。如果要生產不斷的提高,勞動者的數量和品質必須不斷的升高。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裏,生產者(或資本家)依勞動者的貢獻付酬,而勞動者憑其勞動生產力的表現得到報酬。生產者將其利潤再投資、購置新設備、增雇勞動者以擴充產能,使產量提升;另一方面,勞動者除將所得用於消費以增進營養、維持並增進體能之外,還用之於提升本身的生產力,亦即經由訓練、再教育、閱讀等活動來增強智能,此外,還將部分儲蓄作為培育後代的費用,使接替及補充的勞動者之素質提高,從而使生產再增加。在生產增加之後,勞動需求的強度相對的高於勞動供給,原先的勞動者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工資逐漸增加,而本來不想參與勞動市場者,由於工作機會的創造及報酬到達了自己所希望的程度,也被吸引而加入市場。這些所謂的邊際勞工加入之後,也憑其能力(生產力)獲取應得的報酬,對於所得分配趨向更為平均,也有所幫助。在自由的勞動市場下,生產力較高的工人移向報酬較高的高生產力行業,而生產力較低者則被技術需求不高的行業所吸收,於是適才適所的情況出現了,較低的失業率也於焉達到。這樣的描述,是一個自由的經濟體系下,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如何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動態交互關係簡圖,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存在着由市場價格引導的自由競爭勞動市場。
在此種自由競爭市場下,由於內外環境的隨時變化,以及每個人主客觀條件的變動,市場內的供需無法時刻充分遇合是很自然的,這也籠統的可以用「轉換成本」這種交易成本的存在來表示,因而勞動市場中有失業是很正常的,而面對短暫失業的準備也是必需的,由而「儲蓄」也應當是人生的必要行為。
華裔產權經濟學國際名家張五常教授,在1984年4月3日所寫的《重要的知識資產》這篇短文里提到,在自由市場制度里,專業人士靠知識而獲得可觀收入的例子,比比皆是。縱使被一般人認為是極平凡的專業,要有安定可靠的收入並非難事;沒有專長而有良好普通常識的人,只要肯干、有信用,何愁找不到僱主或想不出可以謀生的小生意。知識幫助生產,市場於是就獎勵知識,這是顯淺不過的道理。
他在該文中是要強調「知識資產」的重要,而吸收知識、積累知識正是「人」的特質。「知識就是力量」一語道出了知識的威力,而多了知識,就多了產品的種類,也就因而增加了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因為缺乏知識而要每星期工作60小時才足以餬口的人,若能增加知識,工作時間可以減半而生活水準仍可提高。
張五常也補充說,知識科技的增長對某些人是比較有所不利的。那些選擇了以時間勞力去爭取加薪而不將時間投資在知識增長的人,或那些向勞工收費的工會主使人,都會因社會知識的增加而受到比較上的不利,甚至可能受損。跟任何投資一樣,知識的投資是要競爭的。不參加這種競爭的人,在一個因為競爭而增加知識的社會裏,怎會不相形見絀?靠罷工或遊行示威來增加收入,在自由市場中實非善策。
張五常又說,有些人認為知識─尤其是學院裏所學的知識-不重要,因為往往學非所用。這見解也是錯了的。讀化學,卻去做生意,可算是學非所用了。但有了學識,思考比較靈活、文字比較流暢、待人接物比較得體,不是資產是什麼?十年窗下,要「一舉成名」固不容易,但「無人問」卻是不愁的。他以自己為例說,他能從事教育工作,算是學有所用;但若要轉業,又何愁沒有僱主?他說這不是誇大之辭,而是他從來不相信會做而又肯做的人,在自由市場內會找不到對所學稍有關係的工作。因薪酬不理想而不干是另一回事。
張五常下結論說,人類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人。而在人之中,除了勞力及相貌以外,其他有價值的都是知識。問題是,為什麼在自由市場下知識會增長得那麼快,而在共產政制下這增長卻乏善可陳?
在張五常的該篇文章里,兩個地方最值得再強調,一是靠罷工或遊行示威來增加收入,在自由市場中實非善策。二是「從來不相信會做而又肯做的人,在自由市場內找不到對所學稍有關係的工作。因薪酬不理想而不干是另一回事。」這幾句話。前者應該不需要多作說明就容易了解;後者則指出數項重要條件,一是自由市場,二是會做而又肯做的人,三是與所學稍有關係的工作,四是薪酬不理想不干。如果由於薪酬不理想而不干以致失業,表示失業對於當事人不會構成問題,不需太關心,這一類也就是自願性失業。會做而又肯做涉及能力和工作態度;與所學稍有關係表示知識和專業化程度。而「自由市場」這個條件恐怕是最具關鍵,這種市場應泛指任何市場,但勞動市場最為重要。自由市場存在與否當然是制度課題,而共產政制和民主私產政制則是最大的兩極分類,楊小凱的文章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體制的失業狀況,張五常更進一步剖析共產政制對知識和「人」這種人類最有價值資產的摧殘。
1984年4月6日,張五常在《知識與共產政制》這篇短文里,就勞動和知識資產的特徵致使在共產和私產制度下對該資產運用的分別,比對其他資產運用的分別大,作了詳細分析。他說每個人都有頭腦、會自做選擇、自作決定,而會作選擇決定的人跟勞力及知識資產在生理上合併在一身,由同一種神經中樞控制,不可分離。其他的資產跟作決策的人是分開的,若將這些資產做為共產,由中央作決策,因為用錯而產生的浪費之機會較大,但這些資產本身不會作決策故不會反對,也不會不聽使喚。但具主動性的勞力及知識資產之所有「人」,可以發憤圖強、自食其力、自加發展或運用,也可以不聽使喚,或反抗命令而行、甚至於會寧死不屈。
對於奴隸,若以虐待方式,「使用」的困難就會增加,主人不可能會有較多好處的。強迫使用勞力尚且如此,要強迫知識的增長及運用更將無計可施的。所以,不讓人民自由發展,不讓市場自由獎賞知識的投資及運用,要談促長科技何異緣木求魚?
張五常提出三種解釋:一是勞力和知識都是主動性資產,擁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主意,若逆其意而行就很難得到有效運用;二是每個人對自己的所長或所短,總要比別人清楚,自己的決策可能會出錯,但有誰能代作決策而有更可靠的準確性呢?三是個人的知識投資不應依個人的短長或優劣,而應依「比較利益法則」才可使投資成本較低,而市價就是比較利益生效的指標或訊息。
就中央計劃的共產和個人自由決策的私產體制比較,優劣如何不必多費筆墨解說了。不過,私產的自由經濟體制固然較佳,但在此體制下,仍然存在着類似中央計劃的機構,透過法令的訂定取得「強制人民作行為」之權力,產品市場中公營事業和特許行業及各種管制法規是常見例子,而勞動市場裏也到處可見執照、勞動條件的法規。所以,勞動需求和勞動供給,在自由民主體制下,依然籠罩着中央計劃的陰影,差別之處在於「自由度」的高低。規範權利和勞動條件的法令愈多,個人選擇行為的自由度也愈小,對於市場的競爭性也會造成妨礙。必須在此強調的是,自由市場裏並非沒有規矩,也並非沒有秩序,當然更不是無法無天,只是市場內「自發性」的規矩、組織、制度較可能讓造成市場失靈的交易成本下降,而「人造、強制性」的法規命令,往往適得其反。台灣勞動市場的演化可作例證。
台灣勞動市場所面臨的課題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顯示,至少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台灣的市場自由程度是很高的,勞動市場就是如此。我早在1988年2月在經建會《自由中國的工業》月刊中所發表的《當前台灣勞動市場所面臨的課題》那篇文章里就寫到:台灣勞動市場中勞力的買賣雙方皆無獨佔力量。就買方而言,據統計顯示,歷年來台灣中小企業數目所佔的比率都在95%以上,其僱用人數所佔的比率也都高於50%,根本無力構成獨佔力量;雖然台灣的公營事業和政府機關所僱用的人力並不少,而進入的條件也較為嚴格,但亦無壟斷力量;更何況任何人要離開原職位也都相當自由,因而實在看不出台灣勞動市場的買方具有獨買能力。再就勞動的賣方而言,雖然台灣的工會不少,而且會員人數及其佔全體勞工的比率也並不小於先進國家,但工會卻一直受到壓抑而難有作為,遑論對勞工有控制權,更別說有能力形成獨賣事實。因此,台灣勞動市場的勞力供求雙方,大都是在各自考量下,在市場上從事遇合的工作,合則留,不合則去,亦即勞工可以自由地移動、轉業。在政府的勞工法令方面,台灣很早就有勞工法令的出現,而且其規定也都兼具周全、彈性,但卻「處罰太輕或完全不具強制性,甚或不具法律效力」(張清溪,1985,頁12),而且法令的執行不嚴格(張清溪,1985,頁13—16)。再以勞工統計資料所載數據加以印證,筆者亦曾就我們的「基本工資辦法」檢討,也發現並未嚴格執法的事實(吳惠林,1984,頁28—31)。因此,政府的法令並未形成對台灣勞動市場的干預,主因在於「未嚴格執行」。這裏需要強調的是,筆者認為我們的勞工法令未能嚴格執行,並不就表示希望政府就原有的法令條文嚴加施行,相反地,筆者慶幸由於以往的此種「備而不用」的事實,才使我們的勞動市場不受扭曲,因而維持自由競爭的市場;但是,筆者也並不主張法令不應嚴格執行,而是強烈的主張:法令在訂立之前應經過審慎的研擬,求其合理可行,一旦頒佈實施,則應嚴格執行,否則寧可不制訂,以免養成人民違法習性;再者,發現法令窒礙難行,則應儘速集思廣益作檢討修改的工作。
基於此,我在該文中作了這樣的論斷:台灣的勞動市場是競爭程度很高的自由市場,在此種市場的運作下,隨着經濟的高度成長,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就增多了,工資和生產力提升了,所得分配也大致趨向均平,而且有工作能力,想要工作者也大多找到了工作。這種現象是一種總體性的概略分析,而在自由的勞動市場下,個人的行為大都是由自己來決定的,亦即決定權在於個人手中。
我們知道,一個人,一個正常的普通人。所追求的無非是「滿足」的極大。但是,每一個人的想法和感覺是不會相同的,即使每人所具備的條件,如:家庭背景、聰明才智、教育程度、性別.……等等都相同,追求滿足的手段也不一定會一樣。一個人可能認為「當老闆」能讓他得到較高的滿足,而另一個人則會認為「當夥計」較能使滿足極大。因此,在一個自由的世界裏,當勞方或當資方,完全是每個人在各自所擁有的條件下,憑着主觀的判斷去做的最適抉擇。就勞資身份而言,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裹,原本就不會有高低、懸殊的區別。有些人認為,只有工人才需面臨生存和生活問題,其實,資方也同樣的需要面對;至於他們所認為只有資本家才會面臨的發財問題,勞工也是同樣的在找尋各種發財的機會。我們不否認社會上有暴發戶、世襲地主和世襲資本家的存在,但是,只要他們不以暴力,不以非法手段經營,即使他們的獲利多,也是他們的本事,更何況他們所面對的營運風險,也相對的高得多。就我們的社會言,中小企業林立,只要有意願和能力,任何人都可以當老闆,而此種企業所獲取的利潤也相對的較低。因此。在我們的社會裏,勞資之間的強弱差別也相對的較小,而在自由競爭程度較高之下,此種差距所反映的正是生產能力的差別!
上文所言,無非強調:一個自由的社會,每個人都各憑本事,從事自已的最佳抉擇,隨着環境和具備條件的改變,也會改變選擇;如此,在無外力干擾下,正可達到所謂的「公平」境界。但是,在任何的社會裹,總是有個超級龐大的機構—政府,打着提供「具外部性」財貨、彌補市場機能不足的旗幟,然而卻往往被既得利益者利用或與他們掛勾,以致更加扭曲市場機能。無可諱言,過去台灣也確有此種情事,譬如限制進口、不准進口,以及高關稅等,培養了一些寡佔企業,並利用管制設立行業的手段造成了某些行業的特權、壟斷等等,不過,在私產擁有,有能力者得以出頭的大環境下,這些情況並不十分嚴重。
在將台灣的勞動市場運作與經濟發展間交互關係作總體觀察,並且說明個人在相對自由的大環境下之經濟行為之後,我在該文中又再次強調:自由勞動市場的維繫,實系台灣經濟高度成長、平均所得,以及低失業率之所以能夠達成的主因。當時我就曾問:情況是否改變?勞動市場方面有什麼重要的問題產生?它們對經濟發展將有何種衝擊?我們有何妥善因應之道呢?
我在該文中是這麼樣回答這些問題的:自從俞(國華)內閣(在1984年)揭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大纛以來,開放、解除管制的行動就接連而來,尤其近年來受到美國的逼迫之後,原本拖、拉、緩、遲的自由化行動也加快了速度。影響所及,國內的眾多管制也漸成眾矢之的,國營事業的長期特權、獨佔、特許行業的存在,高速公路權的管制,大宗物品的聯合採購,乃至《獎勵投資條例》等等都在主動或被動之下,一項項的陸續開放或廢止。這些訊息告訴我們,靠政府管制力量的壟斷或寡佔企業,將愈來愈難有存身之地,產業間的競爭也將愈趨激烈,如此一來,勞動市場中勞力買方的獨買行為勢必更加不可能發生。
對勞力賣方而言,在前述的流動自由勞動市場裏,勞動者的報酬大致系依勞動者的生產力支付的。不可否認的,由於資訊的不完全,市場也無法達到完全競爭的境界,因而總有人認為自已沒有獲得應得的報酬,這種現象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有的,也就是此種原因才有勞動移動的產生。每個人總是想要更多,而且希望更好的,這是人的本性,也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但由於本身的條件以及環境的限制,往往只能達到某種地步,在一個沒有扭曲的自由社會中,這就可解釋作自身生產力的反映。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裏總有某些生產力極低者,其報酬或僅能餬口,他們是應該得到幫助,不過,原則上,採取積極的「提升他們的生產力」以及「提供更多的訊息」是較妥善的做法,不要利用硬性的重分配方式——即強將高所得者的所得壓低,以之重分配給貧民。
在勞動報酬反映生產力的過程中,隨着勞動所得的提高,勞工知識水準的提升,勞動者的協商能力自亦增加,他們所提出的契約條件也會愈來愈高。亦即資方所要支付的勞動成本也從而增加。這本是一個經濟不斷成長的社會,自然會發生的現象。我們知道,為了使利益達到最大,生產者或會選擇獨資,或會結合成為廠商或公司,或者組成更為龐大的組織。同樣地,勞方也在利益與共的情況下,很自然的會結合成群體來與資方協商。以增強議價能力,並加強勞資雙方的溝通,以減低資訊成本,俾生產力提升。這個樣子的組合方式,純粹是出於個人的意願,也就是說,是每一個人依其自身的考量,所作的最適選擇行為,這應該就是工會的正確產生方式。如果個別會員一旦覺得工會無法合乎其願望,他可以自由的離開,或者選擇加入其他的團體。在這種情況下,個別勞工依其自由意識,可以結社,也當然有罷工的權利。但是,有個重要的原則需要強調:勞工個人的行為系基於自願,而非經由脅迫而來,因此,事件的後果也應由個人來承擔。
過去,台灣由於某些顧慮,根本禁止罷工,而且也限制人民結社。在一個開發程度較低的社會,由於勞工們的知識程度較低,求取溫飽尚來不及,自然也不會有此等需求。但在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之後,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知識水準普遍上升。勞工們也理所當然的會有前所未有的進一步要求。再加上社會輿論的推波助瀾,結社權和罷工權自然也在需求之列。
對於這樣的發展,政府已加緊各項勞工事務的改革措施。而民間某些個人或團體也積極的在為勞工爭取權益。這其中也有許多人暗自擔心,深恐我們的社會將重蹈歐美先進國家的覆轍,而讓工會淪為野心政客的工具。所以,這裏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認為我們的社會,勞工們一直太受壓抑,無法享有應有的人權,因而必須立法保護勞工,以維護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退休生活,提高勞工福利,並爭取工會獨立自主,要求恢復罷工權,俾促進勞資雙方平等地位,使勞資的關係和諧。第二種看法則認為,我們之能有今天的快速發展,勞動市場中沒有工會力量發生扭曲作用是一種重要因素,尤其是沒有暴力威脅的罷工更是重要關鍵,他們多半經歷過英、美等國家的罷工場面。印象深刻而惡劣,在心有餘悸之餘,深信罷工權一旦開放,一定淪為野心政客的工具,後果堪虞;他們也甚至認為,英、美經濟力量之所以逐漸衰弱,工會太強系主因之一。這兩種極端相反的看法都有其道理存在。我們當前的情況已明顯的走向開放結社權和罷工權的路,問題在幅度如何,而上述的反對人士的擔憂,也並非毫無道理。因此,工會的定位,以及罷工所應有的尺度,就是迫在眉睫的課題。尤其如何防範工會壟斷而致勞工形成獨賣,更是值得特別留意。這裏面的關鍵,在《工會法》的如何訂定。因此,徹底檢討和修改現行的《工會法》已是勢在必行了。
至於政府的一般勞工法令,雖然以往的法令都未認真執行但卻不意味將來亦會如此,就筆者來看,1984年7月所頒佈實施的《勞動基準法》,可能認真的實施。以目前發展的情況言,它將會扭曲勞動市場的競爭,至少會削弱競爭程度,怎麼說呢?由於以往發展的結果,勞工所獲的報酬,除了生活所需外,尚有餘裕充實自己及家中成員們的生產力,使工作報償又再提升。依此種良性循環,勞工的知識水準提高,協商能力也增加,他們所提出的契約條件也會愈來愈高,也就是說,資方所要支付的勞動成本也愈高,這本是一個勞動自由移動社會之常態。在沒有法令規範下,勞雇雙方會經由不斷的咨商協調,得到彼此都滿意的均衡。這個時候,如果社會上有一法規,明訂勞工們所應享有的最低條件,而該法規的條文中又有許多較某些勞工所應得到的為高的目標。由於此時的勞工們已經學會了據法力爭,加上民間某些輿論和團體的大聲疾呼,而且政府又成立位高權重的執行機構。則法令破壞勞動市場的競爭是可預期的。現今的台灣,情況正是如此。一來各界殷切盼望的勞工委員會業已成立,其急思有所作為,嚴格執法是可以想像的;二來民間對於勞工運動的熱切參與,已然形成風尚;三來《勞基法》中又確有許多嚴重扭曲及破壞競爭勞動市場的條文。
因此,如何防止《勞基法》阻礙勞動市場中價格機能的運作,甚而使其發揮正面效果以幫助價格機能運行;如何避免工會發展走向偏鋒,以及避免罷工權成為勞動獨賣所賴以形成的一大助力,實系當前朝野必須一致戮力的重點。
我在該文接着對工會的形成及其功能也作了詳盡剖析,其內容還是值得作為當前修訂《工會法》的參考。不過,在此不免要表示遺憾,因為十多年前所寫的文章,在今日看來一點都未過時,甚至顯示出極為適用呢!只是參與修《工會法》者對此文未知可曾看過否?由於《工會法》尚未對台灣的失業發揮影響,而依自由工會的精神也似乎成為主流,在此不擬再引該文,對此課題的討論有興趣者請自行參酌。對「《勞基法》的修改問題」,卻非常急迫,因而以下將該文對修改《勞基法》之分析再作引述:我們在上文一再強調,台灣的經濟不斷成長,以致勞動報酬和工作條件也逐漸提升,在無外力或較少外力干擾的自由市場下,這種良性循環仍會持續下去。在一個自由經濟體系裹,不但個人在他自己的條件限制下,有選擇當勞方或資方的自由;而且,就資方而言,生產、經營的方式也各有別;對勞方來說,也有各種不同的工作條件的選擇方式。因此,有否必要制定一致遵守的標準格式也就有商榷的餘地。理想的做法,在於提供一個環境,讓供需雙方自由表達自己的意願,而在協商過程中決定雙方都接受的條件。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提供更多的資訊,讓雙方都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我們也知道,完美的社會是不存在的,基於自利心,每一個人都想要得到更多,於是人與人互動之間也就產生了制衡力量,在無外力脅迫時,大家都可達到限制條件下最適狀況。所以,一般而言,隨着本身具備條件的高低,就有不同水準的報酬,如果憑少數人的主觀判斷,訂定了所謂最低標準,其結果,不是扭曲價格(工資)機能,就是其規定本身如同具文(過去的經驗是如此)。為什麼會這樣呢?
基於一般的社會公義,對於邊際勞工(也就是那群勞動條件低於所認定的最低標準者)應有所照顧,尤其社會愈進步,就愈應有能力做到。最根本和有效的做法,應是設法增強這些人的能力,不過,這種工作往往吃力而且費時。一般人最先想到的便捷方法,就是立法加以規範。上焉者以市場不完全為由,力主以公權力來匡正,下焉者則直覺認為,立法之後就能確保邊際勞工的權益。於是,最低工資法、同工同酬法、公平就業法等等勞工法令紛紛出籠,發展至今,不但大多數國家都有,而且還有國際組織特別在為這方面操心。甚至還訂有各國應遵守的規範。問題是,這些法條的效果如何?尤其在經濟方面有何等的衝擊?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環境下,是否有不同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在一個勞動市場不自由的國家,必然存在剝削的現象,因而需要匡正該種扭曲,但在一個勞動自由流動的國家裏,任何的立法限制是否反會造成扭曲呢?以美國而言,固然有各種勞工法令,但其施行效果卻不斷的遭受批評,反對的聲浪從未止息。有些法令雖明顯呈現不利,卻因既得利益者或其他的政治原因,在確立之後而無法撤除!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別人的經驗應仔細予以考量,不要重蹈覆轍。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看我們的《勞基法》,該法所揭示者乃「勞動的最低條件」,所要保護者,乃是那些邊際勞工。筆者已說過,台灣的勞動市場屬於自由競爭,而低層勞工的市場更是可能接近完全競爭,外力的干預將不利於他們。我們的《勞基法》若認真強力徹底實行(由上文分析是很可能的),就會有此種現象。詳細的經濟分析已由張清溪(1985年6月)、吳忠吉和張清溪(1985年11月),以及林忠正(1987年9月)分別做過。後一篇只做經濟理論的分析,而前面兩篇文章,不但有嚴謹的理論分析,尚有詳盡可行的修法建議。輿論的批評,也由立法院圖書館(1986年2月)加以整理。若主管當局有心修法,當不難找到豐富的參考意見,筆者勿需在此多加補充。不過。筆者卻願意再強調:儘量去除個人行為的管制,讓個人自己去做本身的最適抉擇,政府不應該促成供方或需方的獨佔,而要維持中立的仲裁者地位,創造和保持一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
在該篇1988年的文章里,我的結論是:大體而言,我們的社會,在自由勞動市場的維護之下,享有了高速的成長,使我們的生活水平及福祉皆有提升。這種自由市場的存在,系因勞動供需雙方都無獨買或獨賣力量。以及政府勞工法令的未認真執行,勞動者有其自身的自願抉擇權利所致。如今,由於社會進步以及勞工意識的覺醒,再加上人民知識水準的提升,以往視為奢求的某些需要,如結社權、罷工權等,很自然的都在要求的項目之內。過去所存在的那些不合宜的限制應該儘量去除,給個人自主權,由而《工會法》的修訂乃勢在必行,而其方向則應朝向開放。此外,為了維繫既有的成果,甚至於更進一層,勞動市場邁向更自由,系一必要條件。因此,政府的現行法令中有礙市場競爭的條文,必須予以修訂;而1984年頒行的《勞基法》,除了對保護最低層勞工的神聖目標無法達成外,尚會對競爭市場造成干擾。如今已成立的勞工委員會,必然身負認真執法的重責大任,為使該法不至於窒礙難行而形成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建議該會參照學者專家們的批評及建議,儘早修法以臻可行的地步。此外。有關美國欲將自由工運的勞工權益,以及其他關於勞動條件,要求依照遵行,以加重我們的生產成本,由而降低競爭力一事,只要我們「真的」尊重價格機能,維護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我們就有堅強的理由,足以抵抗其壓力。
之所以將我這篇十多年前(1988年)的文章大篇幅引用,旨在指出今日台灣所面臨的困境,就是該文所預言的,而關鍵也就是市場自由度遭到公權力的破壞,殺傷力最大的就是《勞基法》。我們也了解,如該文所言,贊成訂定該法者基於保護勞工,尤其是弱勢邊際勞工的立場,「好意的」藉由「最低勞動條件」的訂定,逼迫業者遵守,否則罰則侍候。他們以為有了法令就能逼人就範,其天真及不可行由上文所引的張五常之論點已可清楚明白。如果不信而硬要實施,企業家或業者的創業精神和環境就會遭到扭曲,楊小凱所說的失業這種後果就會呈現,而最先遭殃的就是生產力相對低的邊際勞工,中高齡者也就在該行列中,且是該族群的主要份子,於是「愛之適足以害之」的俗話,以及「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西諺也就赤裸裸地應驗了。此中的道理我在該文里已作了非常清楚的交待,而當前台灣所面臨的失業潮,尤其中高齡失業就是活生生的印證。
其實,在《勞基法》剛頒佈實施時,有識之士就開始擔心並陸續為文大聲疾呼趕緊修正,特別對該法中的「退休金制度」直言將遺禍無窮,而勞委會官員也並非不知不覺,「修法」準備更早就付諸行動。可是十多年過去了,依然還停留在修法階段,國民黨五十年政權轉移,如今新政府也緊鑼密鼓地修法。
新政府會比較可能有辦法將《勞基法》扭正嗎?由「兩周八十四小時」的修法結果,以及「公務員周休二日」的施行來看,情況恐怕不樂觀。因為勞動條件是往愈修愈高方向走,法令阻礙勞動市場運作的程度也自然是增加而非減少。主因在於立法委員們在虛幻膨脹的「勞工選票」壓力下,不敢將勞動條件拉低。
除了退休金、工時、假日這些勞動條件外,「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辦法」也是自由勞動市場的殺手,而且它的對象就是中高齡等邊際勞工所屬的市場,以產業別來說,就是「傳統產業」的範圍。除了直接影響低工資、低生產力勞工的就業外,基本工資與勞保、外勞工資等掛勾,也加重殺傷力。特別當1999年《勞基法》擴及所有業別之後,嚴重性更大,因為服務性行業也涵蓋在內。
有人或許會問:為何《勞基法》實施十二年之後(迄1996年),台灣失業率才有所影響。一來勞委會素來就不敢嚴格要求業者需依法提撥退休金;二來十多年之後員工退休期已紛紛來到;三來國際經濟環境、尤其是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環境的變化,形成台灣產業的競爭壓力。
如果台灣的產業都能巧妙地適當升級,因而與繼四小龍之後採用相同方式發展的開發中國家之產品有所區隔,台灣的傳統產業就可繼續存活。不過,由於中國大陸佔盡「後開發的優勢」,幾乎不必費吹灰之力就快速全盤習得四小龍的生產方式,加上其地大、人多、物博,而且又可隨意以優惠政策作誘餌,於是致命吸引力逐漸形成。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在1978年開啟門戶,其環境的不安定為其最大罩門,加上人民在大鍋飯浸久了,工作態度一時難以扭轉,非有一段艱辛路途不可,那個時候台灣若能采開放政策,中小企業台商得以名正言順登陸探索,台灣內部在「比較利益」的自然演化下,「兩岸分工」易於形成,而台灣產業的升級腳步在市場競爭壓力下也能及早邁開大步,連帶地台灣本地勞工也早能充實知識資產或人力資本,以求在生產力競爭上居上風,或者彈性調整勞動條件取得適當差距。
然而事實是,政治性因素主導一切,一來禁止業者赴大陸,但中小企業主卻發揮一貫冒險犯難精神不絕如縷地登陸;二來直至1989年才合法引進外勞;三來勞工法令愈趨嚴格。這幾種管制政策都對產品和勞動市場的自由度多所限制,也讓台灣的企業家和勞工們無法對環境的變化提高警覺,因而不能充分發揮高度的靈活彈性。當十多年後大陸人民在外資(不只台商)的教導和本身學習下,實現了「後進國家的比較優勢」,環境的安定性和人力資源的品質都有高度提升,台灣縱然祭起戒急用忍政策,也阻擋不了大企業的西進,甚至於我們保守的大陸政策讓兩岸的分工合作大打折扣,再因台灣內部自由化、鬆綁政策開展的不順遂,致兩岸間的自由度呈彼長我消局面,勞工法令的緊箍咒於是扮演「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加速傳統產業的消亡,而高科技產業也面臨衝擊,關廠歇業成風潮毋寧不意外,千禧年下半年全球經濟的下滑又來湊熱鬧,失業率的節節升高也更順理成章了。不過,若能在十多年前就像上文所引的我的那篇文章所說的方式未雨綢繆,或者如劉克智和張五常所提倡的自由市場,經由個別行為人在自由市場中的調節威力,台灣也許就不至於面臨當前的嚴竣失業情勢了。
勞動市場是落後指標,失業一旦來到,即使因應得當,也需一段時間才可改善,如果無法對症下藥,恐怕情勢更不妙。那麼,我們做對因應對策了嗎?自從媒體大幅且頗醒目報導失業率月月上升,以及經濟不景氣訊息普遍散佈以來,政府就宣佈多項因應措施,諸如失業給付、以工代賑津貼、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措施、促進中高齡者就業措施,以及《勞基法》修改等等,表面看面面俱到,但仔細檢視卻存在諸多問題,我跟鄭凱方已在另文(吳惠林、鄭凱方,2000)里詳細說明,本文不擬再述,只就攸關長遠的《勞基法》之修正方向再予引述:「勞委會所提的《勞基法》修正方向,我們認為在變形工時與延長工時的限制方面,執政者已朝法規鬆綁的方向努力,值得肯定,但是鬆綁的程度可能不夠,例如,僱主與勞工的權利義務上仍多有限制,例如在休假、適用期間、平均工資的計算與退休金的提撥費率等。我們懷疑這些管制是否真能發揮效用,事實上由過去的經驗來看,《勞基法》之所以被稱為惡法的原因,是因為法律訂的再詳細,都無法滿足每一個僱主與勞工的需求,而且愈詳細、確定,束縛力就愈大,彈性也就愈疲乏,市場競爭程度當然愈低,窒礙難行也愈嚴重,如今雖朝鬆綁之路前進,但其艱辛比法之訂定和實施更困難百倍,此由立法院對每周最高工時下降的修法結果可以看得清楚,不但對失業問題的紓解沒助益,反而更加速邊際產業關廠、進而波及邊際勞工的就業。值得再強調的是,勞動條件最好是經由僱主與勞工雙方不斷地協商來自然形成,任何法律的外加限制,一定增加雙方的交易成本。至於退休金提撥制度的改變是值得肯定的,因為過去僱主為員工所提撥的退休金,事實上是員工薪資的一部分,僱主只是延後給付而已。如果因為員工轉換工作而無法支領已提撥的退休金,但是勞工已經付出勞動,僱主沒有理由不支付勞動報酬。至於提撥的費率,理應由勞雇雙方協調而定,一來政府的規定很難讓大家皆大歡喜,二來不應再讓大家養成依賴政府的習慣。因為勞雇雙方協調都需要付出成本,而協調成本可能隨着時間的拉長而遞增,因此雙方為了讓自己的協調成本降至最低,均衡的協調時間應不致太久。而這協調成本,極有可能低於因政府介入所產生的交易成本,這不就提高大家的福利了嗎?」
除了仍然認同這樣的陳述外,我還要強調立法院在2001年4月初擬將《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發條例》等五項被稱為「錢坑法案」通過,又有在「社會福利」上加溫的跡象,這些行為都十足反映「法令促進勞工福祉」觀念的深入人心,特別是掌有權利者似更深信不疑,這不但對中高齡弱勢勞工的失業潮有促進作用,更會產生波及效果,讓生產成本在調整彈性缺乏及推高下,產業外移腳步更快,「制度性失業」的現象將更明顯。畢竟自由市場這隻「無形手」的力量最可靠,妄想操控、扭曲市場勢必受傷慘重,而失業的升高就是一項最明顯的代價,先進國家斑斑經驗早已提供啟示了呢!
參考文獻
1.立法院圖書館編印,《勞動基準法》,立法院報章資料專輯中第一輯,1986年2月。
2.林忠正(1987),《勞動基準法對勞動市場影響的評估》,《當前經濟問題研討會》,中國經濟學會,頁57~69。
3.吳惠林(1984),《我國基本工資辦法評介》,《台灣經濟》,96期,頁25~32。
4.吳惠林(1988),《當前台灣勞動市場所面臨的課題》,《自由中國之工業》,69卷第二期,頁1~10。
5.吳惠林、鄭凱方(2000),《中高齡失業與政府政策》,《劉克智教授榮退研討會-台灣勞動市場相關問題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
6.吳忠吉、張清溪(1985),《如何促使勞基法對企業發展產生正面效果》,《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報告書》,第四冊,頁244~297。
7.張五常(1984),《重要的知識資產》,收錄於《賣桔者言》,遠流出版公司,頁203~207。
8.張五常(1984),《知識與共產政制》,收錄於《賣桔者言》,遠流出版公司,頁208~212。
9.張清溪(1985),《中華民國勞資關係》,《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專論》。
10.楊小凱(1998),《減少失業的政策》,《信報財經月刊》12月號,香港。搜錄於楊小凱(2001),《楊小凱經濟學文集》,翰蘆出版公司,頁155~160。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