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就喜歡過年。
後來,雖然隨着年齡的增長、過年難免逐漸變得複雜,但每當被問起時、略加思考之後,我的答案還會是——「很喜歡過年」。
於是,幾十年活下來,我的心裏、慢慢「捏」出一個若有若無的小人,每隔上一年左右的時間,就會蹦蹦跳跳地自己走出來、對着農曆的春節翹首期盼——然後,和他已經等了一年的東西終於再次相逢,滿心快慰、幸福喜樂。
七年前,到了加拿大之後,每年到了那個大概的時節,心裏的這個小人還會按照幾十年的習慣定期出現——左等右等、滿懷期待。
不過,他終究什麼都沒有等到。
於是——他安靜地坐在BC省Burnaby中央公園的那片深山老林里,雙手托着腮幫子,透過樹冠的間隙、看着遠遠的天空,只能靜靜地去想、想那個每年都會讓他去等待的春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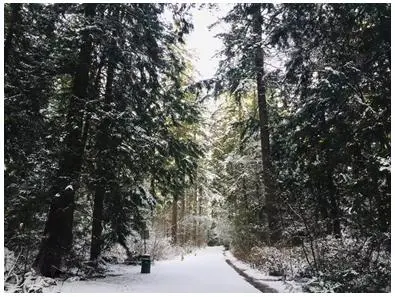
上、「來,把時間撤掉!」
可能大家會對中國節日的一個細節,因為熟視而「無睹」——有些節日,會把人類社會和正常世界裏一個重要的度量衡從人們的生活里暫時「撤掉」、從大腦里暫時「屏蔽」。
而這個被撤掉的度量衡是如此之重要,因為它叫做——「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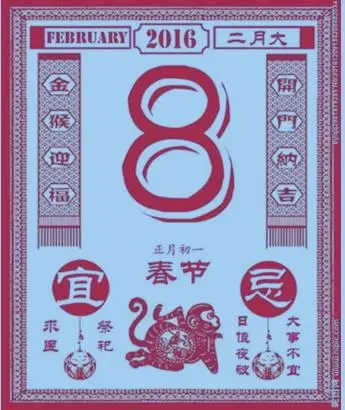
比如十一黃金周的那七天,你只會記得今天是「十月幾號」——如果有人問你「今天是禮拜幾」,你會撓撓頭,發現平時被你掰着指頭從周一數到周五的「星期」這個概念,居然被遺忘了。
照例,這還不是最牛的——最牛的是到了春節,所有人會把「星期」和「月日」全都拋在腦後、而只記得今天是「農曆初幾」。
在那幾天裏,也許還有人能夠經過回憶和推算、說出當天是公曆的「幾月幾號」,但是你要再問「今天是禮拜幾?」的話、那就真的要大家一起打開手機看日曆了。
在那幾天裏,無論你是對「農曆」純熟的50後60後,還是對「農曆」有印象但一直搞不太清的70後和80後,抑或是壓根兒把「農曆」當成出土文物的90後00後,全都要把自己日常的時間概念撤掉、然後翻箱倒櫃找出常年被「塵封」在犄角旮旯里的「農曆」——
因為過年的幾天,周圍所有人只論這個、全國上下也只提這個。
以前,我只會把這看成是一種技術層面上的特殊計時方式、僅此而已——但是,直到遠在加拿大、直到與中國隔着半個地球,我才開始好好地去琢磨和品味這個以前不曾留心的細節。
也只有這時,我在過了四十多個春節後,才感覺到中國人過年時,把日常的時間撤掉、另換一套計時方式的這個「細節」里,究竟包含着怎樣的一種傾情投入與極致浪漫——
來,讓我們過年——把日常的時間統統撤掉!
來,讓我們過年——把所有人用來上班的「禮拜幾」撤掉、把平常計算着發工資和值班、休假的那些「幾月幾日」撤掉!
來,讓我們過年——把所有人,從平時有那些關於繳手機費、繳按揭、繳水電費、給孩子繳贊助費或者高價學費的「年月日」等等這些周期和輪迴中,先「放」出來!
來,讓我們過年——把整個世界從「根兒」上開始改天換地、偷去日月,把所有正常的秩序和輪迴,從腦子裏屏蔽,讓它們暫時有多遠滾多遠……
來,讓我們過年——把所有人放進一種專門用來讓人「專心」過年的時間和宇宙里!

為了能夠瘋狂、為了能夠狂野,地球上的人們一直都有自己的方法——狂歡、派對、瘋狂的喝酒、喝酒不過癮於是嗑藥……
而人到中年,我才發現,曾經在自己身邊的那些春節里,普天下的人們,從時間這個「根兒」上把日常那個世界和宇宙「撤掉」,帶着家人、背着責任,從柴米油鹽的日子輪迴中走出來、把日復一日的生活瑣碎屏蔽掉,暫時忘卻一切——這才是一種深在骨子裏的狂放。
而所有這些,是我在中國度過的將近四十個春節里、所從來不曾想到的。
而我之所以會有如此的感覺,我覺得僅僅是因為我身在中國之外,當然——也因為加拿大並不會有連時間都要「撤掉」的節日。
下、「我要見你,怎能預約?」
前幾年某個春節的一天,我經歷過一個讓我至今還印象很深的事兒。
其實,整個經過很簡單——那天不僅是過年,而且也正好是個周末,於是我想「貿然」電話約一個老朋友看他能不能跟我喝酒。結果不巧,他正好有事兒,於是只好作罷。
如果是在中國——這壓根兒不是個事兒。

可是在加拿大,這還「確實是個事兒」。
因為,任何一個在加拿大社會裏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應該都已經覺察到我剛才這種操作的些許「不妥」——無論喝酒也好、其他事兒也好,哪有象我這樣當天才直接打電話問的?為什麼不提前預約呢?
是的,這是一個「萬事要預約」的社會——看醫生要預約、做客要預約、請人吃飯要預約、見經紀要預約、洗牙要預約、開家長會要預約、打疫苗要預約。我一直很驚訝,在這個每個人業餘生活看上去似乎都很「平淡」的社會,怎麼除了買菜和去商店、幹什麼都要預約?
當然,奇怪歸奇怪,我平時倒也覺得「預約」是個能為大家節省時間和帶來方便的好習慣。
於是,在這個「預約」性社會裏,我這個臨時「約酒」的電話就顯得有些「不妥」——拋開對方可能正好沒時間不說,主要在於會讓對方感覺有些唐突和不適。
因為大家在這個「萬事要預約」的模式下呆久了之後,在「無預約」的時間段里、往往會自動進入一種「時間安排不會被別人打亂」的「蟄伏」模式,或者說「安排不想再被臨時改變」的「保護」模式。這時候如果有突然的請求「降臨」,如果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兒,大家的「第一反應」一般會傾向於「排斥」、或者說「能推就推」。
所以,即使是在「華人移民」這樣的外來人口圈子裏,對方接到我這個電話之後首先會感到驚奇,而在通話結束後、心裏應該還會掠過一句話:「他是不是腦子裏哪根弦搭錯了?」

雖然有着這些「困難」,但我略加猶豫,還是決定貿然電話我的老朋友——我們哪怕有364天都是按照常規和理性去生活的,也至少應該「劃拉」出一天、和其它的日子不同。
比如,今天是在「過年」。
更何況,我是約他喝酒——喝酒這種臨時起意、完全憑興致的事兒,怎麼能預約呢?
電話的結果是我邀約失敗——雖然他確實有事,但還是很高興我突然給他打電話。
因為他和我一樣,雖然覺得預約這個社會習慣蠻好,但是日子久了、也很期盼一次「不期而遇」的貿然相約。
於是,帶着這麼多思前想後的糾結,這麼一件在中國壓根「不算個事兒」的事兒,在這個「萬事要預約」的社會裏被整出了「開天闢地」的效果——因為這居然是我移民這些年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無預約的情況下,貿然電話約人當天見面。

這個「相約未遂」的事情,本來到這裏已經結束了。
可是,在兩天後(還在春節里)我下班的陰雨里,我順着這件「開天闢地」的事兒、連帶着又想起了一件過去的事——
那是很多年前在中國、一個春節的晚上——那天晚上、我其實是因為一個聚會因為意外臨時取消、而「意外」呆在家裏的。
就在日常已經吃完晚飯、已經不算太早的時刻,忽然傳來了敲門聲。
是的——在這個電話、手機、微信早已普及的年代裏,我又聽到了「久違」的敲門聲。
然後,我打開門——面前忽然站着一位跨過許多年份的朋友、懷裏揣着一瓶酒來,站在我面前,一身風塵僕僕、帶着清冷夜風。
看到是我開門,他象個孩子一樣高興地說——「直接來你家敲門、打開門才見面的感覺真是太爽了……」
我保持着開門的姿勢看着他,已經驚訝和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我們的交情先擱一邊兒,過年也擱一邊兒,我的激動首先在於——已經有多少年沒有朋友敲開門、然後站在我面前了?

我們喝酒的時候,當我問他為什麼不提前打個電話、如果我不在家、他豈不撲了個空?
他帶着醉意的回答十分有成就感、也十分堅決——
「撲個空?那就撲個空!我就是想要突然站在你面前的感覺,要是提前打電話、這效果就徹底沒希望出現了……」
這個很多年前的故事,在中國過年的時候、其實並不算稀奇——無論是各種社交媒體都已經玩得純熟的年輕人、還是早已經玩轉微信的老年人,在過年的那幾天,至少在我的親友圈子裏,他們中的有些人,依然會「固執」地選擇提前不打電話不發微信、而是直接貿然上門。
如果撲個空,那就撲個空!
即使撲個空,也不能破壞「忽然見到你」的那幅寫意——甚至,只是不願破壞那個畫面出現的「可能性」。

可以想像——當我在前兩天剛剛為一個電話約酒而被「萬事要預約」的社會習慣整得「十分糾結」之後,再想起這個很多年前的故事時,心裏是多麼感慨和熱烈。
想到這些,在加拿大的淒風冷雨里,我覺得象有暖流奔涌於周身,似有電流輻射過雙頰,我雖然面無表情,但在心裏已經想要潸然淚下。
潸然淚下——並不是因為此時的我在春節時分、身處異域他鄉和冷冷清清,而恰恰因為我的心裏是熱熱乎乎、滾燙滾燙的。
以前在中國的時候,我並不理解——過年的時候,為什麼有的人登門之前「笨拙」地不知道提前打個電話,為什麼有的人在臨時起意忽然決定去見另一個人的時候、說走就走、卻「倔強」地在一路上都不會提前發一條微信。
那時候,我甚至覺得他們有點兒傻——
而直到另一個「過年」的夜晚、當我身在「萬事要預約」的加拿大,在風吹雨打中再次想起他們,我覺得自己才將將有些懂了他們的「笨拙」和「倔強」。
那笨拙,那倔強——是一道埋在心底深藏千年的浪漫,是一幅懷揣執念行走萬里的詩意。
尾聲
小時候過年,我曾拿着窗花和剪紙貼在臉跟前兒看了又看,卻只覺得眼花繚亂、看不出來個啥。

然後奶奶說——「放遠一點兒再看看。」
然後,我兩手拿着窗花,雙臂伸直,再一看、才很有成就感地說——「呀,原來是一隻大老虎!」
如今,只有隔着半個地球,我才看到了以前沒看到的「過年」、理解了以前沒有理解的「過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