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可笑,像我這樣一個從事抑鬱症研究工作的人,竟然患上了抑鬱症,頗有監守自盜的意思。各種方法一一試過,才明白箇中滋味,才知道以前很多時候都是站着說話不腰疼。於是,在這裏以散文小說的形式分享出來,為大家揭開抑鬱症的面紗,而對於患有抑鬱症的朋友們:如果地球不快樂,今夜就讓這些文字來陪伴你吧!
前南斯拉夫導演庫斯圖里卡在他的回憶錄《我身在歷史何處》中寫道,當電視裏播放薩拉熱窩的動亂時,貝爾格萊德人漠然地換了台,後來戰火燒到了貝爾格萊德,其他人也都冷眼旁觀時,他們明白這怪不得別人。

我也曾經這樣冷漠,面對那些對抑鬱症的誤解與歧視,我別過臉去,選擇了沉默。有人說抑鬱症就是矯情,有人說想不開的人才得抑鬱症、想開了就好了,也有人說抑鬱症患者都不夠堅強、過於軟弱,甚至說這是無病呻吟。當我聽見那些尖銳的話語、刺耳的聲音,我公事公辦地想「公眾對抑鬱症的歧視還有待改善」,但這不屬於我的工作,於是我轉身離去,懶得花心思、浪費口舌。
而今,自己站在了被歧視的陣營中,迎面而來的鋒利話語被我一一輕巧地避開,與它們擦肩而過時卻深切地體會到徹骨的寒意。於是,明白了波拉尼奧的那句話:「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言語甚至緘默承擔責任。」
後來,當我發現身邊的人對抑鬱症有所誤解時,就開始柔弱地反擊。像《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被老師誘姦的中學生房思琪,假裝不經意地試探她母親的口風「我們學校有個女學生跟老師好了」,結果得到無情的回應「小小年紀怎麼就這樣」。我說「抑鬱症的表現之一就是精力不足,情緒低落,對社交活動提不起興趣,很多事情上他們也是力不從心、身不由己」,卻換來一句「我覺得誰誰誰肯定也有抑鬱症,動不動就不搭理人,太奇葩了」。沒能給抑鬱症批上一件雨衣,卻惹來了傾盆的暴雨。
於是,我改變了策略,在必要的時候公開自己的病情。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很多人因為身邊有了這樣一個「關係很好、人不錯、看着挺正常」的患者,而對抑鬱症更加包容、更加善意。可是,傷口一旦被揭開,便意味着它失去了保護,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難免會遭受二次創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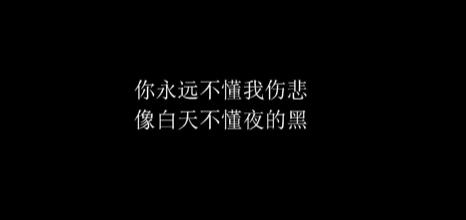
有時,我會眼睜睜地看着事態走向不可控的方向,卻無能為力。有時甚至會覺得雞同鴨講,明明兩個人說着同一種語言,卻無法溝通。就像李翊雲在小說《千年修得共枕眠》裏寫得那樣,同樣都講國語的父女之間無話可說,而初到美國、不會說英語的父親卻每天都在公園裏跟一個波斯人用各自的母語互訴衷腸。
巴別塔建造之初,人類被上帝剝奪的那門共同的語言,我想它的名字叫同理心。而今,人與人之間的理解竟是那麼得有限,有時你甚至會覺得你們之間仿佛有一堵無形的牆,隔開了兩個世界。一個人永遠不懂另一個人的傷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那些沒有被心理疾病「翻牌子」的幸運兒,他們的人生或許就像正午的太陽,那樣的光亮、那麼的晴朗,過慣了那種明媚的日子,又有幾個人會真的在意那些在黑夜中掙扎的人們。
「夏蟲不語冰」,不能與只存活在溫熱時節的生命去談論冬天的寒冷,這讓我覺得有些悲涼,畢竟我們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啊……
這些無奈與傷感曾經困擾過我一陣子,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為這種現狀感到悲哀。可後來,終於漸漸地明白:同理心如同美貌與智慧一樣,是一種極其寶貴的資源,而它並非均勻地分散在每個人的身上。在同理心的帝國,有些人如羅斯柴爾德、如美第奇那般富可敵國,有些人卻一窮二白、身無分文。

所以,當需要別人的理解時,就要找准那些具備這種能力的人。你無法從一個人身上得到他沒有的東西。
這樣想着,心情似乎釋然了一些。
正午或許不懂夜的黑,但是黃昏和黎明沒準兒會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