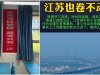本文作者(後排右1)與車間技術人員師傅們
1972年大學開始恢復招生,方式是基層推薦逐級政治審查,這種方式一直延續到1976年。大中專招生,讓知識青年又多了一個跳出農門的機會,不過,那些具有灰色乃至黑色家庭背景的知青,依然和招工一樣是沒有多少希望的。到1973年,我們突然聽說招生恢復了文化考查。當然,國家層面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不可能知道,但能不能通過文化考查,成了能不能被錄取入學的一個重要條件,這個事實讓許多沒有「優質」家庭背景的知青很興奮。那一年,名額也放寬了,我們公社一下子推薦了近20名知青參加考試,好像是自開始招工招生以來推薦知青最多的一次,我也在被推薦的知青當中。
當時,距離考試大約還有一個星期左右,生產隊並不能給知青特別的照顧,白天我照樣出工,只能在晚上突擊複習一下。夏日裏,成百上千的蚊子轟炸機一般在身體周圍嗡嗡盤旋,已經不是魯迅所描述的那種「文質彬彬」的「發表一通議論」了,那簡直就是徹頭徹尾的威脅恐嚇。飢餓的蚊子輪番攻擊,密密麻麻地叮在裸露的手臂和小腿上,一直吸到它們自身體型翻番膨脹也不離開。就是在這麼惡劣的條件下,點一盞鬼火般的煤油燈,我複習了一個星期,主要是突擊學習以前從未學過的幾何,準備應付考試。
考試題目簡單到出乎意料,我輕輕鬆鬆就完成了答卷,提前交了試卷。據招生的老師告知,我的成績很好,已經被確定在錄取名單里。
回到生產隊等待錄取通知的時日,某一個晚上,公社有線廣播裏傳出了播音員高亢激昂的聲音,播出「白卷英雄」張鐵生的事跡。我知道自己完了。果然,政治風向急轉,考試成績不再算數,我再次因政審落榜。1974年初,剛剛創辦的四川維尼綸廠技工學校到蒼溪招生,他們打算在經過了文化考試的知青中挑選。公社再次推薦了我,而且傾力相助,其間經歷了難以言說的諸多周折,我最終回到了城市。先在技校學習,而後進入四川維尼綸廠儀表維修車間當了一名工人。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開後,我並沒心動。倒不是因為1973年的挫敗造成了心理陰影,而是因為:第一,我技校畢業入廠不到兩年,按國家的規定不能報考;第二,在當時,儀表維修確實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不存在通過考大學謀求更好前程的問題。
不過,我們車間有兩名青工報考了,而且都考上了,他們一下子被罩上了斑斕的光環,成為了我們所有青工仰慕的「明星」。開歡送會的時候,我只說了兩句話就哽咽了,淚水在眼眶裏瘋狂聚集,我埋下頭竭盡全力控制,眼淚卻丟人現眼地奔涌而出。
他們考上大學對我是一個巨大衝擊,瞬間激活了我早年的願望,我無法再對考大學冷眼旁觀;也激活了我對自己的信心,我暗暗發奮,決心在第二年招生時參加高考。
和1977年相比,1978年高考改為國家統一出題,考試的科目也增加了,文科有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此外,無論文理科都增加了外語考試作為參考。這一屆對外語尚未作硬性規定,沒有學過外語的可以不參加考試。這個規定讓我感到十分慶幸,我把自己列入沒學過外語的考生,免去了十分頭痛的外語複習,還省出了時間複習別的科目。
我就職的四川維尼綸廠,是當時國家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的三家大型化工廠之一,因其設備的先進性,聚集了許多文革前的大學生。我所在的儀表維修車間更是人才濟濟,每一工區都有數名大學生做我們的師傅,教給我們應該掌握的技術知識。那時,設備陸陸續續運來並等待安裝,廠里沒有足夠的倉庫,有不少設備堆放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由各分廠各車間派人員輪流值班看守。
記得有一次值夜班,師傅們在一起閒聊。印象中,我的師傅們閒聊也極有檔次,幾乎沒聽過他們聊八卦。他們在一起,要麼討論工作中的技術問題,要麼交流一些當時科技進步發展的最新信息。那個時候,即便是作為工程技術人員,他們各自的信息來源也十分有限,這樣的交流就顯得很有必要。
那一次他們討論基因,我從他們的討論中第一次聽到了基因這個概念,神秘的基因使我對知識淵博的師傅們由敬重升級為高山仰止,我在自慚形穢的同時,也獲取了奮發向上的強大動力。
雖然工廠尚未投產,但工作卻多而繁雜,外出學習的任務也很重,並沒有什麼閒暇。我們車間因為有了77年兩位工友考入大學的榜樣,青工們都躍躍欲試,有10餘名青工報名參加1978年高考。受過高等教育的師傅們對我們這些當過知識青年卻實在算不上有知識的年輕人特別理解,給予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那段時間,我們上班可以把複習資料帶到車間辦公室去看,師傅們主動承擔起平時由我們承擔的工作,儘可能地留出時間讓我們在辦公室里複習,還在工作之餘為我們答疑幫我們解題。師傅們無私的支持和不求回報的幫助,讓我至今感銘於心。
與師傅們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宿舍里的技校同學。時至今日我依然不明白其當時的動機,也不願意把別人想得太齷齪。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裏,居於同一寢室的技校同學,每每看到我吃過晚飯拿出書坐在床邊準備複習時,就邀約一幫人在宿舍里引頸高歌,或者故意嘻嘻哈哈地擺龍門陣,鬧騰到10點多甚至11點鐘。
據說,還有人在背後無比蔑視地挖苦:蔣蓉還想考大學,哼,不自量力!我當然不想與這些人作任何計較,寢室里呆不下去,我就去到宿舍外面光線昏暗的路燈下複習。好在我考文科,除了數學以外,其他都不需要伏案做習題;而且,我有師傅們的支持,白天可以在車間辦公室複習數學。
據說,1978年報考大學的考生是史上最多的一年。有了77級的榜樣,很多77年因各種原因沒敢或沒能參加高考的人們,都報名了。川維廠遠離市區,廠里沒有條件為考生設立考場,考生們都安排在長壽縣的晏家鎮中學參加考試。學校里每一間教室都擠得滿滿的,還是兩個人一張桌子,做點小動作十分容易。不過那時的人把考試看得很神聖,考生們也都非常自律,那麼擁擠的考場也沒聽說有什麼人作弊被抓住了。
考場條件差,考試結束後還沒地方休息,只能在學校的操場邊枯坐,等候下午的第二場考試。因為考試緊張,中午即便有地方休息,估計絕大多數人都沒法入睡,所以不休息也算不得什麼問題。
印象中特別深刻的一件事,是中午沒地方吃飯。別人怎麼解決的我不知道,第一天我是毫無準備,只好餓着肚子挨到下午考完,回單位宿舍才能吃飯。
那天回到宿舍,剛推開門的那一剎那,我眼前一黑差點倒在地上。還好腦袋沒糊塗,趕緊抓緊了門的把手,雙目緊閉,堅持了一會,然後迅速撲向距離門口不算遠的床。那時年輕,扛過來了,沒發生意外。第二天我自帶了乾糧。
我的考試還算順利吧,除了考數學一直做到鈴響,別的幾門都提前交卷出去了。答題時,我眼角餘光瞄到旁邊那個女孩,寫的時候少擦汗的時候多,內心還對她滿是同情。考完試回到車間上上班,師傅們問考得怎樣?我回答還馬馬虎虎吧。師傅們就笑着說,一般答「馬馬虎虎」都比較有勝算了。
等待公佈成績的日子是焦慮的,雖然和知青需要「躍農門」不同,但既然參加了考試,就是給自己設置了一個較高的期望值,要說不焦慮那肯定不真實。
極具戲劇色彩的事情,發生在公佈成績那一天。
與我一起從蒼溪農村調出來,又一起進入技校儀表班學習的朋友周午丁,進廠後在宣傳部門工作。她接觸人多,各種消息來源廣。她也參加了1978年高考,和我們一樣熱切關注着有關高考的各種消息,而且總是考生中最先知曉的那一個。那天中午我們剛下班準備去飯堂吃飯,她來電話了。
周午丁是個女高音歌者,我是聽她的嗓音才對文學作品裏描述的「銀鈴兒一般」有了具體真切的感受,可此次,電話那端沒有銀鈴兒,她低了嗓門,語氣沉重得讓我心驚肉跳,她說蔣蓉,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千萬不要着急啊。我心裏「砰」的一聲,像一塊巨大的玻璃被打碎了。她在電話那端繼續,成績公佈了,你是一百八十多分(當年的錄取線,理科是二百八十分,文科大約高十分或是二十分)。末了她還特別強調消息來源十分可靠,是原來技校的羅書記從縣招生辦帶回來的。
我愣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放下電話往桌子上一趴,雖然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緒,但還是管不住漫涌的淚水,因為壓抑着,就變成了全身的顫抖,很痛苦的樣子。
車間的幾個青工分外同情,和我一樣也在等待公佈成績的王亞希、楊渝菱幫忙打來了午飯。但我吃不下,只是哭。哭歸哭,我的腦袋卻一刻也沒閒着:考場裏瞄到旁邊人艱難答題的情景,我自己比較輕鬆地完成了各科考試的情景,考試結束後對答案的情景……有關高考的所有情景都迅速地在腦子裏划過一遍,再划過一遍。慢慢地我就冷靜了,也堅定了對自己的信心: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只有一百八十分!我向值班的師傅請假,我準備下午去縣城查分數。一定是他們搞錯了!
剛剛請好假,周午丁的電話又來了,她一連聲地說對不起、對不起,蔣蓉,搞錯了,你是成績上了重點線了。不到兩個小時,我被從山顛拋下深谷,又被從深谷直接提溜上山巔,暈死了!上了重點大學的分數線,原本只打算考西南師範學院的我,一下子有了進入四川大學的資格。拿着電話一時間啼笑皆俱,我再一次說不出話來,愣了半天才回復她兩個字,謝謝!
我成了當年廠里成績最好的一個考生,在全廠的考生中第一個接到了錄取通知書。通知書下來的時候,我的名字像插上了翅膀一樣,飛遍了廠機關的每一個部門。每到一個地方辦手續,首先聽到的都是這句話:你就是蔣蓉啊!這是一種讚揚,這樣的讚揚讓人喝湯都醉!
我在廠辦拿到通知書時,雙手因激動而顫抖,打開一看,卻呆了!通知書上赫然寫着——四川大學哲學系。我覺得自己的雙腿好像被取掉了骨頭,綿軟得根本無法站立,只好急忙伸手扶着樓梯的欄杆,勉強把自己的身體支撐住,腦袋裏卻聚集着飢餓的蚊子集團軍,一片嗡嗡嗡地轟響。
川大哲學系並不是我的志願,估計是因為我沒有哪一科特別突出,加上那時哲學系少人填報,錄取時就把填寫了服從分配的考生調劑到了哲學系。經歷了那麼艱苦的奮鬥,承受了那麼大起大落的情感折磨,換來的卻是一個「學政治的」哲學系。我突然不想上大學了。
那時,我對哲學的認識非常浮淺,哲學究竟是個什麼玩意兒,根本不知道;也從來沒聽說過「哲學是關於智慧的學問」,這個能讓人產生美好憧憬的對這門學科的判斷。和幾乎所有人一樣,在我心目中哲學就等同於政治,而「政治」因幾十年的「政治運動」變得十分令人厭惡,唯恐避之不及。
盯着那份來之不易的錄取通知書,沮喪像湧泉一樣四處流溢,徹底覆蓋了我內心本來若狂的欣喜——學政治,太沒意思了!又想,我已然考上了大學,考的是全廠第一,能力已經得到證明,也有力地回擊了那些對我的蔑視,就是不去上大學,也可以揚眉吐氣了。放棄吧,放棄吧,我努力在心裏說服自己。
可是,我還是非常糾結,很想徵求一下家裏的意見,無奈那時家裏沒有電話,寫信吧,時間上來不及,就是拍電報也來不及,我必須克服選擇困惑,儘快做出決定。還是要感謝我的師傅們,他們都說,好不容易考取了,機會難得,應該去,上大學總是好的。師傅們說的也是他們自己的切身體會。我決定了,聽師傅們的。
無論如何,我作最後的決定還是有幾分勉強,只是,去廠里各相關部門辦手續的時候,人們羨慕的眼光不加掩飾的讚揚,又一次滿足了我的虛榮心,讓我在離開川維廠的時候,情緒還比較高漲。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人在考取大學之後也如我一樣,差點把「去還是不去」糾結成了哈姆雷特王子「活着還是死去」那個著名的追問?
大學畢業後,調動工作和舉家幾次大搬遷,我把值得珍藏的准考證、錄取通知書等都弄丟了,能夠找到的只有一枚校徽。還好我的同學們在記錄他們這段經歷時,都亮出了他們珍藏的這些文物。屬於時代的紀念,都是一樣的。
2017-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