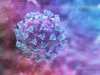自從疫情數據出現了大變動,感覺瘟疫得到降服,某種心境也稍有舒緩。但願這場天災人禍進入告別式,接下來談論的,將是災難的後遺症。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各式各樣,重在療傷與康復的群策群力。而相對生理的感染,那潛伏在人們心理間的病毒則更難以消除。比如,眾生曾圍觀閱讀一個女作家的災難日記,本來屬於特別的好事一樁,即中國人有了公民之間某種命運共同體的覺悟。然而,卻跑出一干無恥之徒,或譏諷、炮轟,欲加其罪。
在一場大災面前,人們難免要驚慌失措,其中不外也包含着對問題嚴重性的意識自覺,補救的舉措也在明里暗裏地進行中。顯然,沒一個現代組織是不要面子的。就當地的武漢而言,政府的官員早就表現出要「謝罪天下」的態度,並有了道歉之說。社會的問責之聲時有呈現,這更在常理之中,相較於造成的社會後果實在不成比例,也微不足道。而我眼下要涉及的話題,卻是一種忍不住,只為另一類道義倫理的喪失,也為一個公民與作家的尊嚴着想。
就在昨日,看到一篇署名「唐山水」的文章:《瘋狂攻擊方方的「四大惡人」,都是什麼來歷?》,令人頓生鄙夷與憤慨!該文開頭寫到:「方方日記儘管已經終結,但對她的爭議似乎才剛剛開始。總有一些人看方方不爽,彷佛方方把他家孩子扔井裏了,把他家祖墳挖了,對她進行瘋狂攻擊。其中有四個人,對方方的攻擊最厲害。那種沖天怒火,刻骨仇恨,令人不寒而慄。」我只得這樣安慰自己,這幫人大概患了精神分裂症,惡毒到了人格無解!
儘管如此,最讓震驚的還是張頤武先生,因為他是北大的人物!張教授是在置疑作家方方紀實日記的真實性,重點是「編造」了「殯儀館一地手機的照片」。結論是:「最關鍵是作家應該有最起碼的求真之心,不能喪失做人的底線。」這真的好搞、好可笑!一個武漢外的人,竟可以對身陷災區、含淚記敘的另一個人做如此「斷章取義」?即便那張滿地手機的照片,也是作者當地醫生朋友提供的。其真實性與否,他張頤武就更有資格來憑空武斷?
如此拙劣的品頭論足,我想會有更多人心生厭惡的反應。我尊敬的友人、文史學家史仲文先生迅速發表了對「此等陰暗小人」的譴責:「罪名好大咧!但究竟是誰失德,誰的良知喪失?······當然,張大教授可能不是湖北人,也不是武漢人,他沒有親身經歷那種苦難。但他畢竟是中國人吧!再退一步,畢竟應該是人吧?以一個人的良知,對因疫困居危城者的日記,竟然全無同情與共感,還要反感、厭惡與指責,如此種種,我對其人格深表懷疑!」
而另一個則是自稱北大博士的王誠卻更是生猛(原來也是「四大惡人」之一)!不知他是否同出中文系或張教授的博士生,總感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態勢。其出格的、幾近歇斯底里地發飆,是要將方方徹底地污名化、罪犯化,欲置死地而後快!一個作家,或作為身陷瘟疫重災區中的千萬民眾之一,她只是最集中的披露者。其所記錄的日常間接或直接的經歷,訴說許許多多災民:不幸的突如其來,苦難的家長里短;殘酷、脆弱以及「戰疫」艱辛!
近日,研究日本歷史的馬國川先生發給我《武漢疫情手記》。我又補了其中許多未讀過的篇章,感覺更是感慨萬千!這是她在內外的壓力下形成的文字,或說是一部當代「史記」。它超越了簡單文學的範疇,一種社會沉重的非虛構,彰顯知識份子的良知。除自己不時在近期文章中提及方方的疫情日記外,有數位平時與文學無涉的學者朋友,也都情不自禁地參與了評述。顯然,這些介入,說白了就奔一個方向:對事實真相的尊重,對污名者的厭惡。
人類品行中的低劣之一,是從不設身處地地為他人着想思考,哪怕對方處於苦難絕境當中。也只有自己或相關的親朋陷入險境,他們才有所慌張,方覺必要博得同情的相助與呼喊。我以為,先不論這場武漢災難責在誰身,首先對同類的不幸抱以關懷、呈現最最基本的憐憫與善意,難道不是人所必備的德行嗎?如果博士教授們的知識積累和文化滋養,都不能還原一種辨別是非、與人為善的起碼認知與行動,那我們是否必須崇尚野蠻,回歸自然的叢林法則,或從頭來過?
在武漢的官員中,有哪個親自出來否定過方方日記了嗎?人們似乎沒看到。並且,堅信他們即便參與隱瞞,那也一定深感後悔了——都是人,面對如此慘烈的局面,如此眾多的家庭與生命。就連最具代表性的胡錫進先生,也都有如此公允的評價:「我的主張是,把方方日記現象也納入進來,讓它成為這個時代旋律的一個音符。」而我們極少數遠離重災區的先生們,卻非要將自己整成一副不近人性的模樣,感覺是一群站立天門俯視人間的看客,欣賞着人間的一片風景。
緣於文道,還是讓人想起了魯迅先生。我們這個歷史文化的悲哀,在於難以延續、拓展和充實現代性的思想資源。因文明的本質沒大的進化,一旦遭遇現實困境,一細看,也全都是無法脫舊的老問題。所以,感覺一個魯迅的思想遺產就管夠。先生在世時,面對社會,面對民眾,面對官場或面對文人,他老先生真是不遺餘力,只要是野蠻的破敗面相,只要是愚昧的奴顏婢膝,只要是陰毒的權力心計,只要是戴着面具的虛偽道學,他一個也不放過!
魯迅有一個很著名的演講,就是為北師大的師生發表的——《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他這樣說:「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閒幫忙的人物。有人說文學家是很高尚的,我卻不相信與吃飯問題無關,不過我又以為文學與吃飯問題有關也不打緊,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閒就好。」先生的這等概括,就眼前狀態也的確說不上過時的。我倒不認為像張頤武人等,是真的為誰在「幫忙」或「幫閒」,而實在是充當了一種流行「病毒」的「幫閒」。
幾天前,張頤武抓住「滿地手機」不放,再次攻擊方方:「醫生們和我這樣的讀者都沒把你當敵人,只是希望你的日記真實······我們憑什麼被你這樣污名化,用最低級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來誣陷。」所謂「棍子」就是被指「極左」。的確,正是張頤武以「敵人」、「民粹」在自證「左」毒。他很藝術地綁架幾個所謂「求真」的醫生來一同狙擊作者,另一面又將千百萬讀者輕蔑為「民粹癲狂的粉絲」。在似乎誠懇的言辭中,側漏出的正是一股亦武式的霸氣!
為他的時代「爭取言論自由」,魯迅也是殫精竭慮。民國伊始,他就為故鄉《越鐸日報》點明該報宗旨:「抒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到了北京謀職,便發出「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熱風·來了》)這樣的言論,說明當初的民主與自由很成問題。這種吶喊,自然同屬於「向上的車輪」。如果遭遇武漢這樣的瘟疫之災,魯迅能不比方方有更激憤的話要說,或也更讓某些人覺得「討厭」或「險惡」嗎?
作為思想家的魯迅個性鮮明,中國現代史上,也難得有這麼一位對所有黑暗和腐朽都充滿憎惡的明白人。正因如此,他連古人身上的那點瑕疵也不放過。在他眼裏,司馬相如和屈原,都不過是統治者的幫閒或幫忙,都缺乏正當性。當代中,也總有人費着牛勁想當師爺的,這並非有什麼不光彩。但確實又有幫而不得,就容易落成等閒之輩,然後另闢蹊徑的。倘若魯迅今日轉活,遇上一類眼高手低的,不知他會是怎樣地一副反應,奚落抑或是批判?或許兼而有之。
文學與現實,如同文人與社會,彼此間的關係似乎已變得越發模煳了。所以,武漢遭遇災難,一個正常做出反應的作家,便在人們的心目中感覺突然發現了劍齒象。這等被暴露出的作家群體與人生現實的距離感,實際上是一種文明退化的症狀,也是人文精神掉入社會瓶頸的表現。彷佛能思想的動物已進入休眠期,人們偶然才驚訝於回歸人類思考行動的「蛛絲馬跡」。難怪向來直率的易中天先生要感歎:「至於文人,則是沒有擔當的,也別指望他們有。」
當然,文化可多元,觀點亦可多種甚至別出心裁。但無論如何,為人者說話要有起碼的人性自覺,尤其是尊為名牌大學的教授。張先生連方方的日記或許都不耐煩去認真讀,卻匆忙下了很歹毒的定論:「關鍵的事情上面的編造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是沒有良知的,是一個作家一生永遠的羞恥。」如此看得出,他是要將一位在蒙難中,儘自己的道義記錄真實生活的作家,一錘子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種準確地抨擊,大概不歸於學術或藝術的多元範疇。
對一個作家記錄發生中的事件,則無論揭露或讚美,都屬於個人權利,對於作家更是天經地義!作者可以文責自負,也能自我承擔個人的道德責任;若觸犯了法律,則更應該由司法機構進行審理認定,而非某些遠離現場的人們以主觀猜忌,或自以為佔據了某種至高或制高點,可以實施社會道德甚至刑事罪過的先行推定!出於人文學者的社會評論,這些年就一直鮮有「百尺竿頭須進步」的境界,眼下冒出如此奇葩異彩,委實是對苦難與良心的一計嘲弄!
魯迅先生若地下有知,該是如何隔土驚詫於這地面上的怪誕飛舞?我倒堅信張頤武這樣的文人,自有一套生存的理念支持。他們無需考究哲學常識,或尊重文學價值。那些抽象或形象,也絕不可同自己堅硬的現實相提並論。本來,一個曾「掛職」的學者,理應有更多的民生與世態的體驗,領悟更細微的社會矛盾與人生冷暖。但不知何故竟陰差陽錯,導致違背很普遍的人倫常識,不願去理會與同情災難中那種壓抑與痛苦,或將自己弄成了「半仙文人」?
近日一篇《不說人品,只談學術:看張頤武教授如何給北大丟人》,其中列舉了被批評者十數篇十分可疑的「論文」,僅標題就看出學術品相的偏差。作者認為:「單就2019年來說,張頤武教授實在是喪失了學者的底線,幾近墮落到如他的那幾位著名同事一樣,已經不止在公眾情懷的基本價值判斷上,甚至在大學教授最基本的學術研究這一層面,也影響到北大中文系和北大聲譽了。」想必這絕非空穴來風,證明張教授所以行為怪異也並非偶然。
這自然絕非一樁小事。在轉發推薦該文時,我的短評也難掩感慨:北大中文系有幾個「學術」怪胎,實在令人看了頭暈目眩。以個人的簡潔瞭解,大概北大的昔日光環早已不再。官僚體制化的越發成熟,使教授們學會或適應投機鑽營的空間幾率大大提高。其實,社會對其期待依然是很高的。只是,看不到人文的教育新希望的增長點在哪兒?胡適、魯迅、陳獨秀的,或嚴複、蔡元培、傅斯年的——那一個個影響大學與社會的巨影又在哪裏?
讀者由此看出的不僅僅是某種個人的不堪,也同時感受到某種作為高等學府北大的難言之隱。所謂「幾位着名同事」,這麼多年了教育界或加知識界也是有目共睹。他們不是在維護北大曾經擁有的那些前輩的榮光,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將那幾張試圖刷新中國歷史的面孔,一點一點地玷污着。至於「新文化」,似乎百年之後依舊是一副曲高和寡,這當然是與教授們的作為不無關聯。而張頤武們尤其執教於中文系,相對於魯迅先生,該是更具羞愧之意的。
實際上,從張頤武教授的言論系列中,人們或可大約估摸出他的某種生存氣性來。也許,他的文章做是做了,自覺能靠近去幫的忙也幫、也忙了,但顯然表現尚不到止境,或心理所預期的影響與高度還沒凸顯出來?這樣的自我要求或期待也並不值得太較真,人各有志。但處於觀察疫情中的張教授肯定既不會等閒,也一定不能平靜。若不能心沉於悲劇,那就一定要琢磨精準的事態方向感。他終於發現了暴露在千萬人眼中的獵物,毫不客氣地撲了上去!
張教授的學術究竟如何,這不是本文要去追蹤評價的。但這其間出現對他人的尖酸刻薄,顯然是讓旁人實在看不下去,也的確有失學者的本分。我與張教授有過直接與間接的接觸,勉強也屬「同行」。雖之前,對這位北大的文學評論家,圈子裏的人們就頗有微詞了,但也僅僅是感覺「蘿蔔青菜各有所愛」這一層。如不是發生眼前匪夷所思的「插曲」事件,也只限於有所聯想,覺得北大的氛圍有些大的退步,還有幾個人文學科的教授有些大的毛病。
關於張頤武,在方方的封城日記中還有這樣一段話:「張教授編造一向很勐。夸讚周小平是中國的如何好青年時,張教授用的也是非常生勐並且還相當熱烈的言詞,誇得好像周小平比張教授更適合在北大任教。」周小平何許人?一個不惜一切聲譽代價,以淺薄、捏造、撒謊之能事,來不斷攻擊詆毀他眼中的「西方民主」,屬於低劣的愛國廢青。張教授能如此不惜北大學者的大面子,為人稱「周帶魚」的周小平喝彩,當是「物以類聚」的表現一種。
處於轉型中的國家,民主與法治的基本面難免存在缺陷。社會的文化生態也未必會完全正常,方方面面都需要去不斷努力完善。面對一場國難級的災禍,就是尋求真相,就是嚴厲問責,就是刮毒療傷,就是痛改前非這又何妨?身為北大教授,即便面對現實難題,寫不出一篇振聾發聵的醒世雄文,張頤武也不該對有限乃至可伶的民意抒發,來一陣如此地「當頭棒喝」。感覺澹化現場災難為能事,充當冷漠且冷血的評論角色,這又屬於哪門子的看家本領?
一個民族面臨殤痛,大家都覺得要設法投入,不論情感還是理性。但因不同的職業,或還有涉及個人的能力與操守,人們都可能從中表現出複雜的姿態來。那些已被輿論詬病譴責的現象,人們也看到太多;悲痛乃至失望,和許多人一樣,我也在心中形成了無法柔軟的結痂。也許未來,隨着社會各方的反省,人們會痛定思痛,也會逐漸找回應該找回的教訓,獲得應該獲得的藥方,來療治共同的創傷與病態。雖需要時間和耐心,也需要理性與勇氣。
中國要真地在人類地球上文明崛起,也還需有諸多的「民族嵴樑」來支撐。而身置其間的千千萬萬文化人,即便不能成為其中的一根兩根,則起碼可努力以知識、以智慧、以精神或以認同良善與正義的勇氣,使自己成為一旁的推動者、助威者。否則我們對不起曾付出生命代價的前輩們,包括那些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在內的、為了某種真的信仰與理想獻身的先驅們。換句話說,要談真理、大道理,也須先從人性着眼、從常識入手。否則,便是扯澹!
2020.3.28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