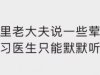對於這個擅長舞文弄墨的集團,要撇開它的自我吹噓和堂皇表白,才能發現其本來面目。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後,我發現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覆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則。這是一些未必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規矩。我找不到合適的名詞,姑且稱之為潛規則。
官場內部有許多層面和方面的潛規則,我想先寫一個「淘汰清官」。這一個「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兩篇短文就能說透徹的,我想分開掰碎了慢慢說。幾篇能說清楚,我也不敢確定,也許四五篇,也許七八篇。
讀史只是我的業餘愛好,不敢冒充專家。我所寫的,都是一些我在讀史的時候冒出來的心得,很可能見笑於大方。但我願意姑妄說之。能姑妄發之,且有姑妄讀之者,則幸甚。
《明史》上記載了皇帝和監察官員之間的一個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禎元年(1628年),朱由檢剛剛當皇帝。當時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心想把國家治理好。朱由檢經常召見群臣討論國事,發出了「文官不愛錢」的號召。「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這是宋朝傳下來的一句名言,國民黨垮台前也被提起過。據說,如此就可以保證天下太平。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對這種號召頗不以為然,就給皇上寫了份上疏,問道:如今何處不是用錢之地?哪位官員不是愛錢之人?本來就是靠錢弄到的官位,怎麼能不花錢償還呢?人們常說,縣太爺是行賄的首領,給事中是納賄的大王。現在人們都責備郡守縣令們不廉潔,但這些地方官又怎麼能夠廉潔?有數的那點薪水,上司要打點,來往的客人要招待,晉級考核、上京朝覲的費用,總要數千兩銀子。這銀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地里冒出來,想要郡守縣令們廉潔,辦得到麼?我這兩個月,辭卻了別人送我的書帕五百兩銀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餘的可以推想了。伏請陛下嚴加懲處,逮捕處治那些做得過分的傢伙。
戶科給事中是個很小的官,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股級或副科級。但是位置很顯要,類似總統辦公室里專門盯着財政部挑毛病的秘書,下邊很有一些巴結的人。韓一良所說的「書帕」,大概類似現在中央機關的人出差回京,寫了考察紀行之類的東西自費出版,下邊的人巴結的印刷費。那500兩銀子,按照如今國際市場上貴金屬的常規價格,大概相當於43000多元人民幣。如果按銀子在當時對糧食的購買力估算,大概有現在的20萬元人民幣[注1]。那時的正縣級幹部,每月工資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多塊錢人民幣,四萬或二十萬都要算驚人的大數目。
崇禎讀了韓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見群臣,讓韓一良當眾念他寫的這篇東西。讀罷,崇禎拿着韓一良的上疏給閣臣們看,說:一良忠誠鯁直,可以當僉都御史。僉都御使大致相當於監察部的部長助理,低於副部級,高於正司局級。韓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這時,吏部尚書(類似中組部部長)王永光請求皇帝,讓韓一良點出具體人來,究竟誰做得過分,誰送他銀子。韓一良哼哼唧唧的,顯出一副不願意告發別人的樣子。於是崇禎讓他密奏。等了五天,韓一良誰也沒有告發,只舉了兩件舊事為例,話里話外還刺了王永光幾句。
崇禎再次把韓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來。年輕的皇上手持韓一良的上疏來回念,聲音朗朗。念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這兩句,不禁掩卷而嘆。崇禎又追問韓一良:五百兩銀子是誰送你的?韓一良固守防線,就是不肯點名。崇禎堅持要他回答,他就扯舊事。崇禎讓韓一良點出人名,本來是想如他所請的那樣嚴加懲處,而韓一良最後竟推說風聞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興,拉着臉對大學士劉鴻訓說:都御史(監察部部長)的烏紗帽難道可以輕授嗎?崇禎訓斥韓一良前後矛盾,撤了他的職。(參見《明史》卷258,毛羽健列傳附韓一良)
韓一良寧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職,斷送了當大臣的前程,甚至頂着皇帝發怒將他治罪的風險,硬是不肯告發那些向他送禮行賄的人,他背後必定有強大的支撐力量。這是一種什麼力量?難道只是怕得罪人?給事中就好像現在的檢察官,檢舉起訴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職工作,也是他獲得聲望的源泉。怕得罪人這種解釋的力度不夠。
細讀韓一良的上疏,我們會發現一個矛盾。韓一良通篇都在證明愛錢有理,證明官員們不可能不愛錢,也不得不愛錢。韓一良說得對,明朝官員的正式薪俸確實不夠花。而他開出藥方,卻是嚴懲謀求俸祿外收入者。這恐怕就不那麼對症下藥。
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史上最低的。省級的最高領導,每年的名義工資是576石大米,折成現在的人民幣,月工資大概是11780元[注2]。正司局級每年的名義工資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當於3930元人民幣。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幣。韓一良這位股級或副科級幹部,每年的名義工資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幣月薪1350元(參見《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
我反覆強調「名義工資」這個詞,是因為官員們實際從朝廷領到的工資並沒有這麼多。那時候發的是實物工資,官員領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蘇木,還有銀子和鈔票。不管領什麼,一切都要折成大米。於是這個折算率就成了大問題。《典故紀聞》第十五卷曾經詳細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戶部(財政部)是如何將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價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場上值多少錢?至少值二十兩銀子!假如按照這種折算率,完全以布匹當工資,縣太爺每年只能領三匹粗布,在市場上只能換一兩銀子,買不下兩石(將近200公斤)大米。這就是說,朝廷幾十倍上百倍地剋扣了官員的工資。至於明朝那貶值數百倍,強迫官員接受的紙幣,就更不用提了。
總之,明朝的縣太爺每個月實際領到的薪俸,其實際價值不過1130元人民幣[注3]。
請設身處地替縣太爺們想一想。那時候沒有計劃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個,多的十來個。那時候也沒有婦女解放運動,沒有雙職工,平均起來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位縣太爺每個月1130塊錢的工資,人均170多塊錢的生活費,這位縣太爺的日子並不比如今的下崗工人寬裕多少。更準確地說,這位縣太爺與如今最貧窮的農民階級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國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還有一點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沒有社會福利。公費醫療不必說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連退休金也不給。成化十五年戶部尚書楊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個月仍給米二石。這兩石大米,價值不過500元人民幣,就算是開了大臣退休給米的先例。戶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部長,退休金才給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參見《典故紀聞》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當時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財產,可能會對明朝官員的實際收入產生更悲觀的估計。
海瑞是一個肯定不貪污不受賄,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捨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消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里。第二天,總督發佈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兩斤肉!」(參見《明史》卷226,海瑞列傳)
海瑞最後當到了吏部侍郎,這個官相當於現在的中組部副部長。這位副部長去世之後,連喪葬費都湊不齊。監察部的部長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見布衣陋室,葛幃(用葛藤的皮織的布,比麻布差)還是破的,感動得直流眼淚,便湊錢為他下葬。當時有一個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來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四句可以作為海瑞真窮的旁證:「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這就是辛勤節儉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員應得的下場麼?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萬曆年間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間,有個叫秦(音HONG,絞絲旁+雄字的左偏旁)的清官。秦為人剛毅,勇於除害,從來不為自己顧慮什麼。士大夫不管認識不認識,都稱其為偉人。正因為他清廉,堅持原則,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鬧得妻子兒女「菜羹麥飯常不飽」,家裏人跟着他餓肚子。
成化十三年,秦巡撫山西,發現鎮國將軍奇澗有問題,便向皇帝揭發檢舉。奇澗的父親慶成王為兒子上奏辯護,同時誣陷秦。皇帝當然更重視親王的意見,就將秦逮捕,下獄審查。結果什麼罪也沒審出來。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來的只有幾件破衣裳。宦官報告了皇帝,皇帝嘆道:他竟然能窮到這種地步?於是下令放人(參見《明史》列傳六十六)。
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證明正式工資不夠花了。
請留意,比起普通官員來,清官們還少了一項大開銷:他們不行賄送禮,不巴結上司,不拉關係走後門。韓一良說的那數千兩銀子的費用――打點上司、招待往來的客人、晉級考核和上京朝覲等,就算是兩千兩銀子,即20萬至80萬人民幣的花銷,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覲,不過用了48兩銀子。由於他們真窮,真沒有什麼把柄,也真敢翻臉不認人地揭發檢舉,而且名聲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險敲詐他們。但是腰杆子沒那麼硬的小官,不僅會被敲詐,還會被勒索――當真用繩子勒起來索。為了證明這類開支是剛性的,決非可有可無,我再講一個故事。
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總督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驛吏招待得不夠意思。驛吏相當於現在的縣招待所所長兼郵電局局長,而總督是省部級的大幹部。我猜想,這也不能怪驛吏不識抬舉,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銳意改革,整頓幹部作風,禁止亂收費,把下邊的小官收拾得戰戰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樣的東西來。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氣,叫人把驛吏捆了,頭朝下吊了起來――這就是節省開支的下場。
海瑞接到報告,說:過去胡總督有過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許鋪張招待。今天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於是將胡公子扣押,從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數千兩銀子,一併沒收入庫。這數千兩銀子,也像前邊一樣算作二千兩吧,根據貴金屬價格和購買力平價的不同算法,其價值在20萬至80萬人民幣之間。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開,期望值也被培養得很堅挺,到了窮餿餿的淳安,諸事都不順心,理所當然要發發脾氣。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沒收了他的銀子,再派人報告胡總督,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請示如何發落。弄得胡宗憲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過,此事供說笑則可,供效法則不可。試想,天下有幾個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後邊豁出命頂着,那位驛吏會有怎樣的下場?痛定思痛,他又該如何總結經驗教訓?
驛吏屬於胥吏階層,比入流的有品級的正式「幹部」低,相當於「幹部職工」中的職工。這些人更窮一些,平均工資大約只有幹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個月一石米,價值不過250元人民幣。但在人數上,職工自然比幹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級別更低,人數更多的,是胥吏領導下的是衙役。這是一些不能「轉正」的勤雜人員。譬如鐘鼓夫,譬如三班衙役,即現在的武警、法警和刑警。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雜人員,最初都靠徵發當地老百姓無償服役。既然是無償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員,政府也不發工資,只給一點伙食補貼,叫做工食銀。這些錢,用清朝人傅維麟的話說,「每日不過三二分,僅供夫婦一餐之用。」他問道:一天不吃兩頓飯就會餓得慌,這數十萬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側,為國家效勞麼?(參見《皇清經世文編》卷二十四)
無論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個等式:一生總收入等於一生總開支。節餘的是遺產,虧損的為債務。官員們要努力把這個等式做平,最好還要做出節餘來恩澤子孫。而明朝規定的工資註定了他們很難做平。韓一良說了,工資就那麼一點。我們也算了,縣太爺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幣。這樣一年也不足1.4萬,十年不吃不喝也攢不夠14萬。而孝敬上司、送往迎來拉關係和考滿朝覲這三項,就要花費20萬至80萬。韓一良沒有說這筆巨款是幾年的開銷。孝敬上司和送往迎來是年年不斷的,外地官員上京朝覲是三年一次,考滿則需要九年的時間。即使按照最有利於開銷者的標準估計,九年花二十萬,這個大窟窿需要縣太爺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還沒有計算養老和防病所必須的積蓄。
相差如此懸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強去做,當然不能保證相對體面的生活,不能讓老婆孩子不數叨,不能留下像樣的遺產,弄不好還有頭朝下被領導吊起來的危險。另外,在開支方面還有一個比較的問題。人總會留意自己的相對地位的,都有「不比別人差」的好勝心。而縣太爺每年的那些收入,並不比自耕農強出多少。手握重權的社會精英們,能心甘情願地與自耕農比肩麼?
考慮到上述的收支平衡問題,崇禎向韓一良追問五百兩銀子的來歷,便顯得很不通情理。這位在深宮裏長大的皇上畢竟年輕。在邏輯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處罰送銀子的官員,而是計算整個生命周期的賬目,把顯然做不平的預算擺平,然後再號召文官不愛錢。當然,明末財政危機,官吏的人數又多到了養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資,純粹是痴人說夢。但這屬於另外一個問題。並不能因此說,造成官員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這種政策就好比牧人養狗,每天只給碩大的牧羊犬喝兩碗稀粥。用這種不給吃飽飯的辦法養狗,早晚要把牧羊犬養成野狗,養成披着狗皮的狼。
現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撐韓一良對抗皇上的力量了。這是現實和理性的力量。整個官吏集團已經把俸祿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預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個生命周期的預算,沒有俸祿外收入的生活和晉升是不可想像的。韓一良沒有力量與現實的規矩對抗,他也沒有打算對抗,並不情願當這樣的清官。作為最高層的監察官員,韓一良公開向皇上說明,朝廷的正式規矩是無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視為理所當然,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明確信號:在皇上身邊的心腹眼中,俸祿外收入已經在事實上獲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數量收授財物,已經成為未必明說但又真正管用的潛規則。這就意味着清官從上到下全面消失。與此同時,正式的俸祿制度則成了名存實亡的制度。這套正式制度也確實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它就像善於將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樣善於逼官為盜。
總之,從經濟方面考慮,清官是很難當的。那時的正式制度懲罰清官,淘汰清官。硬要當清官的人,在經濟上必定是一個失敗者。當然,這裏算的都是經濟賬,沒有重視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團自始至終賣力揮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滾得如此奪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視。我完全承認,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剛直不阿可以為證。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以為證。
[注1]:國際市場上的白銀價格波幅很寬,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圓。這裏以每盎司8美圓計算。1盎司為28克多一點。明朝的1兩,大約相當於現在的37克多一點。銀子的購買力,在明朝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的波動很大,有1兩銀子買7石大米的時候,也有1石大米賣1兩6錢銀子的時候。崇禎年間的米價普遍較高。整個明代平均起來,每石粳米似乎在0.7兩上下。
[注2]:明朝的1石,大約相當於現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祿米一般是稻穀還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還是糙米,還不清楚應該用現在大米的收購價、批發價還是零售價。京官領到的俸祿經常是加工好的大米,當時叫做白糧。根據加工好的白米每石160斤,明朝的一斤為590克的說法,一石白米為94.4公斤。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價在2.6元人民幣左右。本文的計算就是根據這些一概從優的假設。
[注3]:實際上,當時每月只發給1石大米,每年發12石,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這麼點。其餘部分要折銀、折鈔、折布發放,這叫折色。按照常規,這位正七品的縣太爺每年實際領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銀子,360貫鈔(參見萬曆《明會典》卷39)。這360貫鈔,名義上頂了36石大米(十貫鈔折俸一石),但是較起真來,由於鈔法不行,貨幣嚴重貶值,這筆錢在市場上未必能買到4石大米。這樣計算起來,明朝知縣每個月的工資只有1130元人民幣。按照明朝的規矩,官越大,折色所佔的比重越大,吃虧越多。
節選自《中國官場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