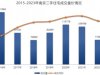"我們還活着,因為我們一直在抵抗"
這是南京!南京 海報中的話,這話,更像是對正在上網的我們說的——我們還活着,因為我們一直在抵抗,抵抗謊言,抵抗遺忘,抵抗逃避……
南京!南京 不是一部仇日電影,而是一部真實再現歷史的非凡嘗試。
南京!南京 不但再現國軍、國人在南京的英勇抵抗,洗刷南京城「軟弱可欺」的歷史誤解,也從普通日軍的角度回憶歷史,揭露人性在戰爭狀態下的異化,顛覆對日本的簡單仇恨,帶來更多理性思考。
《南京!南京!》不僅僅是南京題材、抗戰題材迄今最好的影片,並且從手法、技術、思想性多個方面講,都是中國電影的轉折性坐標(把張x、陳x、馮x等以「偽」為核心的「山寨大片」的畫皮 毫不留情地撕下),從此——中國有了可以回饋世界的真正大片藝術。
南京!南京 陸川拍了整整4年,而南京上空的魂魄等了整整71年。
看電影也好,看盜版也好,讓我們鼓起勇氣,抵抗內心的懦弱,勇敢地坐到這部電影面前……
(以上為樓主按,大家看完2、3樓再發言)
南京!南京!在製作拷貝的前夕,作了數場內部放映,引起熱烈反響。有影評人用「傳世之作」來形容該片的藝術成就。
美國獨立電影「教父」哈維溫斯坦在不斷用「太震撼了,太震驚了!」這樣的詞彙來表達他對影片的敬意,他說,影片在戰爭場面等動作場面上的呈現水準讓他十分驚異;戰爭場面的風格是他在以往的戰爭影片中從未看見過的,是全新的戰爭電影風格。他對導演陸川的能力感到非常吃驚。除了要購買《南京!南京!》的全球版權,他還提出要和陸川合作拍攝影片。
《南京!南京!》即將破冰咆哮而出的巨獸,難以置信的史詩巨片!
文/藤井樹
2009年的第一天,我在陸川工作室里看了《南京!南京!》的樣片。當天恰是陸川一個朋友的生日,陸川把這次觀影活動作為一份禮物送給那個朋友。開看之前,大家都興致高昂,開了紅酒,捧着爆米花,席地而坐,準備邊看邊吃邊聊。
誰料,此後的放映,現場始終靜寂無聲。
當第一個畫面開始,我們就知道,這是一部與爆米花徹底絕緣的電影。儘管尚未做完後期,諸如配音、配樂、混錄、特效、字幕等等都沒完工;儘管看的是刻成三張光盤的粗剪版本;儘管在電視機上看電影的效果差強人意。可近三個小時的觀影,還是讓在場每個人都深陷其中,難以抽離。影片結束後,大家繼續沉默。好似有千言萬語,卻又不知從何說起。
「太牛了。」過了很長時間,有人低聲說了一句。
很多人問我,《南京!南京!》好看嗎?
我說,好看。
它是那種讓你的眼球和神經一刻不能分離的電影,不知用什麼力量,時時刻刻緊緊牽動着你的所有感官。我完全被陸川營造的空間所征服了。戰爭場面呈現出的真實質感令人毛骨悚然,完全顛覆了《拯救大兵》的中韓模仿者們建立的毫無節制的戲劇性路線。那台破舊的電視屏幕上輻射出強悍的真實歷史質感,震懾了在場的所有人,無法想像,這部電影在銀幕上會有怎樣的力量。
但它不是用「好看」可以概括的電影。
我甚至至今也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詞語來形容這部電影---
因為無論是敘事結構,還是劇情脈絡,抑或影片所呈現的獨特質感,都有別於我們以往所看過的任何一部中國電影,你甚至無法在世界電影中找到可以和它類比的影片---我的意思是,《南京!南京!》太獨特了。它有一種強悍而原始的力量,無論場面還是表達,直指內心。
這部電影完全超出了我所有的預期和觀影經驗。
如果硬要我描述《南京!南京!》是一部怎樣的電影,那麼我的回答是,正如它的英文名字一樣,《生死之城》,它是一部超乎想像的關於愛與恨,生與死,穿透了希望與絕望,超越了憐憫與寬恕的電影。每個人都必須親自去看了才能感受到電影中洋溢着的那種時而粗曠蠻霸,時而悲天憫人,時而冰寒刺骨,時而溫暖纏綿的複雜且微妙的情感。
如果硬要我形容這部電影,我想說,它是即將破冰而出的龐然巨獸,在陸川辦公室那台破舊的電視上我已經感受到了它即將震撼這個電影世界無法抑止的奔騰咆哮的力量。如果我沒有看錯,它將成為中國電影史上坐標性的里程碑。 
著名影評人周黎明的博客
我們終於有了一部可以跟《盧旺達飯店》《鋼琴師》《辛德勒的名單》媲美的故事片。
這是一個很值得拍、但很難拍好的題材。我一直覺得我們缺少審美的距離感,但陸川拍好了。不僅感人,而且經得起推敲。
詳細影評將刊登在《看電影》專欄。
敬請關注《南京!南京!》的相關文章
「我不擔心《南京!南京!》的票房,因為它就是一部商業片。」這是之前陸川對媒體說的一句話。
隨着《南京!南京!》進入首映倒計時,陸川再也不會像當年《尋槍》《可可西里》上映那樣輕鬆了,他不擔心這部電影的口碑,甚至面對幾乎同期和《南京!南京!》上映的相同題材的電影的競爭,陸川也顯得非常自信。相比人們對他這部電影的溢美之詞,他更希望看到一個讓他滿意的票房數據。他開始和很多大片導演一樣為票房焦慮了,這可能是很多導演必經的心裏磨練過程,小眾的口碑已不再是陸川對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個大眾層面上的認可。因此,在一夜之間,陸川的臉上就起了多粉刺。即便在過去這部電影從立項到開拍過程中經歷的曲曲折折,陸川的臉上也沒有長過這麼多的包。三個星期之後,票房數字將決定他的容顏以及他在未來中國導演中的新位置。這部耗資一個億的電影,對任何導演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你很有誠意地去跟這個體制交流的時候,它不是一個對壘的感覺。」
《三聯生活周刊》:《南京!南京!》在立項審查的時候遇到了很多麻煩,這種題材的電影和別的電影審查上有什麼不一樣?
陸川:我不知道別的電影是什麼樣的,但這個電影除了電影局之外,□□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幾個部門領導的意見下來才能決定。
現在回憶起來真是一個特別長的故事。等到我們真的去送劇本的時候才知道,那一年關於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殺」要上,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兒了。而且當時日本大使館聽說這事兒也有過反應,後來這些項目就都擱着。籌備到2006年底,劇組常備人口已經五六十人,兩支選景隊伍在中國轉着,各種各樣包括很多槍械和服裝的設計圖都在做。可是傳來的消息好像說這事兒要黃,內部給我們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為你們不是最早的,論先來後到也不是你們,憑資歷的話也不是你們」。我聽到要拍這戲的導演就有唐季禮、嚴浩,德國人和美國人也都要拍,橫着豎着都輪不到你。記得那段時間我跟投資人覃宏出去喝悶酒,他說的最悲壯的一句話是他家裏所有的錢一共有一百多萬,「陸川我支持你到把這錢花光,然後咱們就散了。」年底,電影局當時給了我們一個消息,說劇本已經給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確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經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過了。但是跟組裏的人怎麼交待?那都是一幫小伙子,二十多歲,每天無憂無慮,去了就是幹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後坐在倉庫外面聊天,說電影拍下來會是什麼樣,特嚮往。我突然覺得這是一個夢,只有我和覃宏知道這夢做不下去了。
《三聯生活周刊》:後來怎麼峰迴路轉的?
後來我們倆覺得不能這麼着,於是就決定死磕,我們倆就把自己認識的各種人開始碼。他認識好多人,我們就去和各種各樣的領導見面。最傳奇的就是12月份,記得是晚上11點,我們倆站在中南海的門口,被一輛車接進去,見了一個老大。這是我第一次進中南海,還是半夜進去的。那領導就問我為什麼想拍這戲。我說:「外交跟文化是兩碼事,我覺得不管外交需要什麼,民間得有聲音。如果等外交特別需要民間有聲音的時候我們沒準備好,那這聲音從哪兒來啊?我們現在是不需要聲音,可是當我們需要聲音的時候,那聲音不是立刻就有的。如果說《南京!南京!》這部電影是來自民間的聲音,我不是想拍一個指着自己臉上的傷疤或者頭上的包說你打過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別的東西出來,因為我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歷史。」我不能說那次見面是關鍵的,但它一定是最後推倒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個,因為第一張牌是特別巨大特別沉重的,那個領導肯定是幫了忙的。
後來又見了三四個這樣的領導,還見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長,有一個司長見我們,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你為什麼要拍這戲,告訴我」。我大概也是類似這樣的話,「其實不是想給這國家找麻煩,但是我確實不認為咱拍這一個戲就真找麻煩了。另外我覺得,我們是唯一能拍好的。」我說,「其他本子我也看過,都是在哭訴,恰恰是我們這本子沒有在哭訴,我們是在講中國人是怎麼回事,因為這個歷史裏面沒有中國人。您翻翻我們所有的教科書裏面沒有中國人的事兒,中國人就是被殺,這不叫事兒。中國人到底怎麼回事?沒有!而且其實也沒有日本人的事兒。這麼一個核心的事兒上,進入公眾記憶的就只有德國人,就德國人救了中國人。最後被我們孩子記起來的就只有一個德國人救了20萬中國人,就這麼一個好人好事兒。這對我們有用麼?下次再出事兒還得再找一個救世主?」反正那天說得很激動,什麼都說了,顯然我們是愛國者,只是想法跟別人不一樣而已。那司長非常好,他說願意幫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通過了。我拿起電話就給電影局打,說外交部通過了。當時電影局的領導覺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東西居然還會有緩兒,挺吃驚的。隔了一天,那個機要轉換的函就真的過去了。3月22日,拍攝許可證拿到了。我記得外交部那個司長曾經到我們籌備的現場來看過。所以經過這個事兒,我覺得這些官員其實挺可愛的,他們真到現場來看你們,想幹嘛呢這幫人,這麼激動非要幹這事兒。
還有一個挺特殊的人來過,賀龍的女兒賀大姐。因為前一天有個朋友說「賀大姐來看看你行麼」,我說行,來吧,沒去想是哪個賀大姐 。第二天突然就一輛車停我們門口了,賀大姐來了,道具啊什麼的看了半天,給我們特別大的鼓勵。她說了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在中國不是你想為國家辦事,你就會理所應當的很順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時候往往是相反的。」往往是沒什麼想法的人過得挺滋潤,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鬱悶。她說「只有你們堅持了,很多願意幫你們的人才會站出來。因為很多人都想這麼做事,但他們不會去做這樣的事。但是你們只要堅持,慢慢地你們這支隊伍周圍就會有人願意去伸手了。」當時我們特別難的時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沒有哪只手伸出來。確實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種人伸手,給我們推到了終點,就包括這次審批的事。到了拍完之後,伸出來的都是特粗壯的手了。看過片子之後可以想像它通過是有多難。我相信這確實是一次進步,是一次標誌性的進步。
我真是覺得你在做一個很有誠意的東西,並且你也很有誠意地去跟這個體制交流的時候,它不是一個對壘的感覺。其實體制也在變化,因為體制是人構成的,人構成的體制,其實有很大的彈性,這裏面就在於你怎麼去面對它,怎麼去跟它交流。當然我希望有一天電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過,而不是我們花費了這麼大的精力,前後大概有一年在裏面。但是我覺得我經歷的這些東西,對於我拍這個戲,從創作者的角度說是有幫助的。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後面在等待的時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時間我都沒糟蹋。
《三聯生活周刊》:拍攝完之後在審查上有什麼改動嗎?
陸川:現在這個版本比那時候少了25分鐘,我覺得這25分鐘都是必須剪掉的,不是誰逼着我剪,而是我認為這25分鐘讓這片子顯得特別漫長。那是我喜愛的,不一定是觀眾喜愛的,也不一定是這個電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給韓總(韓三平)看了個粗剪,他看完之後挺興奮的,跟我說咱們得好好想想怎麼保這個片子過去。一周之後開始進入審查,一直到今年1月8日通過 ,審核過程中間我也在不斷修改,不是局裏的意見,而是我自己覺得片子不夠好,不夠凝練,很多東西過於手軟了,就一直在剪。到意見下來的時候,反而是讓我特出乎意料,就兩頁紙,十幾條意見,而且沒有重大修改,都是點狀的,沒有面狀的說摘掉一個什麼。
有些領導看完之後覺得特激動,發短訊告訴我,認為這是出乎他們意料的一部電影。意見快出來那幾天我確實也着急,挺怕的。有幾場戲我特別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第一次審的時候有一個意見說日本人戲太重,說把日本人的戲拿掉。這些意見到最後成文的時候都沒了,只是說長度縮一下。我能感覺到,很多人在保護這個片子,沒有這一雙雙手去擋在這個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瘡百孔。這部電影是這麼過來的,它雖然漫長,我能在裏面感受到的其實是幫助。
有很多演員的戲被我剪掉了,那些戲只對演員有幫助,不對這部電影有幫助。當時我剪的時候其實有些私心,因為這些演員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們都是腕兒,我在想能幫他們就幫他們。我在開始剪戲的時候就沒有《可可西里》那麼狠,剪《可可西里》的時候演員都不認識,本身它也沒有什麼大演員,我完全就根據對素材的需要。而《南京!》演員跟我相處了一年,我剪的時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別疼。因為我知道媒體在公映的時候會數的,誰有多少場戲,怎麼回事,我突然覺得這麼一個殘酷規則中間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戲,我有點心軟。現在這個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後剪定的。因為有時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時候,你的這個門檻就高了。
「沒有這一雙雙手去擋在這個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瘡百孔。」
《三聯生活周刊》:王朔給你提過什麼意見?
陸川:我記得有一天有幾個朋友來看,那個是2小時15分鐘的版本,沒想到王朔來了,我就比較緊張,因為他比較銳利,他看的時候都不用說話,我就突然發現有很多東西是不應該屬於這部電影的,因為他是最挑剔的人。他也看過《可可西里》,看完後跟我說:「我以為這是一好人好事兒呢,你給拍成這樣了」。這次他又說:「我發現你回回我覺得肯定拍砸的事兒,都讓你給鼓搗回來了,你怎麼老走險招啊?」看完《南京!》他先跟我說:「我特別喜歡後半部分,我特別熱愛這結尾,像我喜歡的歐洲片,情懷、觀點還有你的拍法都鬆弛下來了,特別好。」前半部分呢,說實話,雖然拍的不錯但是我有點看不下去,因為這是中國人的公眾記憶,你沒有找到新的視角。但是你也沒轍,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這事兒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漢奸。在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難的。但是日本人這條線太好了,我沒想到會有這條線。這條線是決定這部戲的藝術價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撐起來了。」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兒,把剪輯師叫來了,重新捋了一遍。那時候投資方說,短點的話一天積累下來能多放一場。我就一直在1分鐘2分鐘那兒卡着,剪不了。可那天我和剪輯師大概用了四個小時,我問他剪了多少,他說你剪了12分鐘。12分鐘啊,其實就我給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經定版了,那時候動一剪刀的話,所有的工序都會重頭來一遍。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碼是十天的一個特別複雜的過程,DI那邊要重新對點,聲音這邊要重新對點。王朔沒有告訴我哪場戲他覺得不舒服,只是那種感覺,你是在跟文藝圈裏面比較挑剔的一個人在一起,他是很難被打動的,世俗情感對他已沒多大意義了。比如說,我個人挺喜歡屠殺然後喊萬歲那場戲,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代人可能會激動的東西,可能對他就不會激動。但是我覺得是最終跟他看完那場戲之後定下了這部片子,因為有些東西是只屬於陸川的,它不應該屬於這部電影。就是那天晚上特別清晰,我剪片子的時候給朋友發了一個短訊說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變得六親不認了。愛誰誰,誰都不認識了。所有的戲,是能跟這電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沒勾上就剪掉了。
《三聯生活周刊》:當時寫這個劇本是怎麼寫的,可能兩個鏡頭需要你看半本書那種信息量。在你去查閱這些資料的時候,哪些東西出動你之後讓你覺得必須把它們表現出來?
陸川:太多了,一下說不清。首先我得感謝我在學校學的專業,我們看書都是反着看,什麼叫情報,從公開渠道去搜集就叫情報。怎麼從公開搜集的情報中找出真實的信息呢?比對。同樣一件事你得聽四個人描述,比對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南京的資料是一樣的,我記得我當時先看中國人寫的,完全沒感覺,除了塞一肚子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斷胳膊斷腿,全都是哭訴,我覺得那種就特弱者。70年了我們還以一個弱者的姿態聊這事兒太傻了,真的。等我開始看日本人的日記,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兒,我突然發現,中國人挺牛逼的啊。我記得有個日記里寫了一事兒,他們小隊進了南京之後,發現一個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來要炸,後來說這挺好的就是履帶壞了,就留着給後面補上吧。因為日本人特崇拜德國,德國玩意兒都好,他們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國坦克沒法比,就沒炸。但這小隊一過去,從坦克裏面伸出一架機關槍噠噠噠噠就把這小隊全乾了,後面的小隊就趕緊圍在地上對着這坦克射擊。最後就是日本大部隊過來給他們包圍了,讓他們投降。最後這哥兒幾個打到沒彈藥了,日本人還是不敢上,最後是澆上汽油把這哥兒幾個活活燒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就覺得,這太牛了。而且日本人是懷着崇敬的心情在說這事兒,寫日記的人是說他沒趕上這個事,看見前面倒了一批戰友的屍體就問,才知道是怎麼回事。還有一個在日記里看到的是叫「街頭巷尾的冷槍」,窗台那邊叭的一槍打死一個日本兵,把那人拖過來一看,說是一個完全沒發育好的一個小男孩,然後一刀就給砍了。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槍,也是穿的國民黨士兵的衣服。就這種事看多的時候,你就會想這歷史學家都幹什麼吃了,我們的歷史學家為什麼把這些抵抗都給抹殺了。我就開始看他們以前的邏輯,他們的邏輯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抵抗,所以你不該殺我」。我覺得這是一狗屁邏輯。我抵抗是天經地義的事兒,我抵抗了被俘虜了,你不能因為我抵抗了而殺我。
然後就是難民營舉手的事兒,我以前都有點想放棄了,大概是2006年中間的一段時間,覺得這戲沒什麼意思,拍它幹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東西之後,我突然發現了大批的新鮮的東西。比如妓女這事兒,拉貝和魏特林的日記里都有記載,我們一個叫陳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記里也有記載,拉貝和魏特林的日記都這麼寫:今天日本人到我們難民營要妓女,說你們這兒有沒有妓女我們要帶走。拉貝的日記里寫的就是「我們讓他們帶走了」。魏特林的日記里寫說「有些妓女自己站出來,我就讓他們走了。」你要想像一下她們走時是什麼時候,那是滿城都在說日本人怎麼強姦、輪姦、姦殺婦女的時候。那個不是好事,不是她們一天掙五萬塊錢的事兒。拉貝輕描淡寫了一句話,我在看的時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場的,再幫助我們,他也是德國人,他不會站在這是我們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場說讓她們去走。如果都是中國人,可能他敘述就不是這樣。我在想這事兒的時候就挺激動的,她們自己就主動站出來了。然後我在另外一個日本人的日記里看到另外一句話,說「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別掃興,從難民營過來的這幫女人中間突然有一個女人瘋了,拔出刺刀要殺我們一個士兵,結果我們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婦拼命搶一把刺刀,不是殺我們的人,而是拼命搶這刺刀自殺。」所以他覺得去趟慰安所碰見這麼一個事兒很晦氣,一個婦女可能被欺負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傷了一個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調部隊過來的時候這些婦女就搶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這些感觸讓我覺得這個戲在中國人這一方面開始有做頭了。我在想,中國人走到今天,其實一定是有一些東西去支撐這個民族去生存的。就像這個電影的副標題——生和死的城市,在這麼一個極致環境下,人是怎麼面對生死的,這個事是可聊的。因為我看到了這些事,我不想編事,我想到《南京!南京!》其實有很強大的一面東西,而且是支撐這個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東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如果我們在這件事上只記得德國人救了20萬人,這對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中國人這條線上開事清晰了,讓我覺得這事兒開始變得有意義。

「最後澆上汽油把哥兒幾個燒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覺得,這太『牛』了。」
《三聯生活周刊》:劇本的初稿是大概什麼時候寫完的?後來是怎麼修改的?
陸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寫完了,但是那個跟現在是天壤之別。之前那個劇本是挺商業的,裏面有姜老師(高圓圓飾)和陸劍雄(劉燁飾)的愛情,有劉燁的脫逃,還有那種想當然的期望。但是事實上,我覺得拍攝的過程就是對這個劇本的一次顛覆的過程。因為我們要求絕對真實,所以拍攝的現場成了去批判和顛覆我的劇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並不覺得這事兒我沒有面子,這個事就得這麼做。因為我是一個沒經歷過生死的人,我在家裏寫劇本,我雖然看了很多資料,但很多東西都是想當然的。可是現場,我們每天現場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話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練,你就知道很多在劇本上寫的事是不允許發生的。比如劉燁,劉燁一到現場我就知道讓這麼一個兄弟活出去太難了,到最後下決心給他半道幹掉的時候,確實內心是很掙扎。你知道像這麼一個1米86的帥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幾乎不可能,那是屬於拉網式的對青壯男子的屠殺,而且反覆地篩,就是差不多看見適齡的都殺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像這樣顛覆性的這種寫作,基本上都是在現場完成的。
《三聯生活周刊》:當時確實是有逃出去的。
陸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經歷,但是都是那種極不起眼的人,顯然是可以裝扮成商販的,到了比如3月以後、6月以後,有的最長埋伏了六個月才跑掉,甚至還有一些沒跑,就是在那裏娶妻生子。但是像劉燁這樣的,還得是在劇情最激烈的時候讓他跑掉,其實就面臨着很大的問題。基本上沒有一場戲是沒改的,都發生了這種質的變化。
《三聯生活周刊》:你說這部片子的核心是關於中國人自救,那在結構上發生了哪些變化?
陸川:其實我一直是想拍中國人和日本人兩條線,我以前在接受採訪時我不敢說日本人怎麼着。而且我從沒放棄過這條線,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張紙的兩面,缺了任何一面這都不是一個完整的事件。最大的變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殺」這個具體的事了,我覺得我們可能在拍關於人如何認識戰爭本性的一個東西,而且我們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國人和日本人,去能夠觸摸到一個一般規律的東西——就是人在戰爭面前和人和戰爭的關係問題。
我不是那種一上來就給它一個特別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為一個戲特別衝動地想去拍。《南京!南京!》有那麼兩三場戲是我在拍戲之前眼睛裏就看到的,比如那場祭祀舞蹈,可以說我有一個特別巨大的欲望想把這舞蹈拍出來,但為什麼想拍這個舞蹈,我很難給你一個明確的解釋。我覺得這事有特別大的意義在裏面,這個意義會讓我睡不着覺。當拍這場戲的那天,那倆鼓手下飛機了,那是日本最棒的兩個鼓手,我請我的日本輔導員把他們請過來的。當時那個鼓也從河南運過來了,為了讓這個鼓敲出我們想要的聲音,我們拿12K的燈一直曬這鼓面,讓這個皮緊起來。我讓他們敲一遍,他們就「哇」一聲開始,敲了四分鐘。我在外面看着,心裏面充滿了那種……突然就覺得這件事做得特別值得。我們必須把這段鼓和這段祭祀帶到所有中國人面前。因為這種威脅,這種被征服的威脅從來就沒有消失過,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兒繼承着呢。他們可能不沖中國,就隨時的。現在讓我們漢族,或讓我們中國人拿出一段震懾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東西,我覺得已經沒了,我們就剩秧歌了,我們真正的東西在哪兒呢?戰爭的本質說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種文化在你的廢墟上舞蹈。那天聽完那哥倆敲鼓之後,我們所有人都特別悚然。那一瞬間,我覺得我們做了一件特別對的事兒。
《三聯生活周刊》:這個片子是由兩個國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經在歷史上有過仇恨的事,你是種什麼心理狀態?
陸川:在拍這個戲時一個職業的工作要求就是讓我自己在拍中國這段戲的時候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在拍屠殺的時候我會恨他們入骨,他們在那兒喊中國不能亡的時候,我在監視器前流淚。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戲的時候我會要求自己是日本人。因為我覺得從來沒有在中國電影中把日本人當人去想過。前兩天在北大有一個記者問我,聽說你把日本人拍成人,為什麼啊?我說,他們不是人麼,人家本來就是人啊。說白了,這電影我可以把他們拍成貼着人丹鬍子的跳樑小丑。可這是我們對自己的一個侮辱,70年前你是敗在這些人手裏,你敗在小丑手裏?不是。我們看資料也知道,70年前他們是多麼強盛,他們一個步兵單兵,一年可以有1800發子彈的實彈射擊訓練,我們能有10發就不錯了。在他們回憶錄里,在1943年以前我們拼刺刀拼不過日本人,後來我們專項進行強化訓練,可能才可以一對一,以前必須是二對一。日本人在日記本上對自己參加的每一場戰役都畫有戰略圖,很多人兜里還揣着小相機。他們的教育程度是什麼樣的?我們的軍隊文盲佔百分之九十九。所以當你去把它污衊,你永遠不能去正視歷史的時候,這些事就有可能再發生。所以我想給中國觀眾知道,在70年前我們輸給了一個什麼樣的對手。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讓情感奪取自己的理智,那就變成自娛自樂的事兒了。
所以關於仇恨的問題,我一直在告誡自己,不要因為仇恨失去理智,然後在跟他們接觸的過程當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種無知的狀態撞進了這個題材,一個朋友告訴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戰期間蘇聯紅軍快勝利的時候去德國的轟炸,然後再去想想屠殺跟戰爭的關係。後來我發現,確實是這樣,當時紅軍對完全不設防的德國城市進行毀滅式的轟炸,最後從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個一個環形坑,一夜之間十幾萬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爾有一句話說的很對:「即使是正義的戰爭,多走一步也是邪惡」。
我以前是真的覺得南京大屠殺是一個個案,因為我是在這個環境下呼吸這個空氣長大的,我認為是日本人特別仇恨中國人,是一次仇恨的釋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將中國土地上發生的屠殺和世界上發生的屠殺做了一個比對之後,我才發現,戰爭中的基層執行者,他們心理和肢體權利的高度獲得,當生殺予奪的權利獲得成為戰場上的神之後,暴行擴大,屠殺成為必然,因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決的物化的東西,人與人之間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惡劣的行徑被高度默許,因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懲罰,所以屠殺成為必然。當將這個事與整個屠殺史聯繫起來之後,我不認為它的意義變小的,我認為它的意義反而變大了。我們應當重新看待這些發生的事情,從這段歷史當中我們得到的結論不應該僅僅是日本人有多麼殘忍多麼愚蠢,這就太簡單了,我們應當悟到的東西是對當下有作用的東西,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態度。
還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攝過程當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殺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繩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槍決之後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這段戲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這才是他們屠殺的本質。原先我們一直以為會是一個家庭被拖出去殘忍的殺掉,會認為日本人是盲目的見人就殺,但是其實不是這樣,他們的殺人計劃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驟按計劃很有效率的成批處理,到城裏見人就殺只是之後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種批量的屠殺才是核心,他們就像是機器一樣在絞殺,把那些俘虜在成批的滅絕,這才是真正的屠殺的主題,而這樣的故事由於他們的滅絕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從日本人的日記里才了解。一百人被拖出去殺掉,餘下的還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後眼睜睜的看着再被帶走,這特別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這才是屠殺。
《三聯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員合作,他們是什麼樣的一個反應和狀態?
陸川:這是一個特別複雜的事情,我特別理解他們的情感嗎?我不理解,我請的這些日本演員,他們陪了我九個月,但同樣的事情讓我陸川去做,比如叫我去東京拍一個這樣的戲,我絕對做不出來,給我一千萬我也不去,我覺得我受不了,但他們就在這兒。這次有很多場戲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為日本演員有一點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會說他幹不了這事,但是我要說服他,告訴他們必須要這麼做,因為當時你們的人就是這麼幹的,所以逼的我們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後來就不是說服的問題了,有一場戲是一個叫水上的年輕孩子,他的結局是在城裏被人勒死了,這也是有真事的。但是後來這個戲就沒用,我記得拍完這場戲的時候有工作人員告訴我說他躲在一邊哭,覺得很崩潰,要回家。
還有一些是很微妙的東西,比如拍打鼓那場戲的時候差點變成一場群架,事情當時是這樣,鼓一抬起來的時候,底下有的群眾演員還在說笑,然後敲鼓的日本演員就不高興了,覺得拍這麼嚴肅的戲怎麼能夠說笑呢,下來「梆」的一聲給了這個群眾演員一拳,這幫群眾演員都是武校的,然後立馬就圍起來打那個日本演員,我們的工作人員趕緊過去幫忙拉架,保護那個日本演員,當時我不在現場。但是我想說一個很敏感的話題,日本演員在現場對這部戲的尊重程度要比我們的演員高,他們會特別認真的畢恭畢敬的站在一邊,如果看到別人說笑打鬧,他們會很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們的演員有時候會很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但是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員看不下去我們的不敬業,雖然他們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細想想,在日本,他們經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決問題,這就是他們的方式。
其實我心裏很複雜,我看到日本演員演戲,真的是特別的投入,我常常告誡我們的演員,我們曾經在戰場上輸給了日本人,現在在演戲上我們不能再輸給他們了,我們要拿出我們中國演員最好的狀態,但是日本演員的狀態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寬了我對這部戲認識的跨度,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撐起了這部戲。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爺爺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參加過南京大屠殺後來回日本自殺的,那麼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員更多了一種家族的感受。
在拍戲的過程當中,他們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好幾次都差點被中國演員打,但他們很好,記得拍一場強姦戲的時候,他們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體上,然後我跟他們講,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話,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這麼裸着,然後我就告訴他們該放到什麼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時候,他們立馬就結束然後把衣服給她們合上,然後對着女孩子鞠躬,這是我親眼看到的。反而是我們有些工作人員是嘻嘻哈哈的,為了這件事情我還給他們開過會,這些女孩子們都是自願來的,她們特別偉大,我們應當認真對待。
還有就是日本演員讓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有一場戲是伊田殺了唐小妹之後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個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場戲不是我編的,當時我們都愣了,因為這不是本子裏面有的,而是這個日本演員小黑自己演出來的,然後伊田過去「梆」就給他一拳,這一拳打的特別狠,到了晚上之後那個小黑臉都腫了,特別委屈的跟我說:「他怎麼那麼狠啊」,我就覺得那個時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實很強大支撐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東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電影裏有一段約翰·拉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了。
陸川:對,他中間就走了。他是1938年2月18號離開的,那個時候整個南京剛剛陷入到水深火熱之中,而且南京國際安全區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為主席,最早是一個中國教授提出的。關於拉貝,這個人的歷史其實要看的是他以後,後來南京市市長千方百計想要找到他,當時二戰之後歐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對納粹黨徒進行過一次梳理,拉貝差點被判,他回德國的時候確實幹過一些好事,就是他寫過一個報告,發表過一次講演,就是講述在南京發生的這些迫害,在這方面我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因為當時他被納粹警告不許再胡說八道了,並且在之後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計,這個時候南京市市長輾轉的聽說這個事情就寫信邀請他說請他們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會提供全部的費用,就跟猶太人對辛德勒一模一樣,當時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還是籌集了巨額的費用給他買吃的,給他寄過去,每月一次,在拉貝日記寫到當他第一次收到從南京寄來的罐頭等等物品,他很激動,這種行為一直持續到拉貝去世。
《三聯生活周刊》:你為什麼要去拍這樣題材的電影?
陸川:從《可可西里》開始,我有一種感覺,拍電影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了,它會記錄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記錄了我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對愛情的看法拍出來了,對於我來說它不僅僅是南京大屠殺,是一個關於人的片子,是我對自己的一次挖掘,裏面蘊藏我對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滿意的我最終找到了並且表達出來了。
《三聯生活周刊》:角川最後自殺是你對戰爭的反思?
陸川:角川最後那場戲是我最後想出來的。我認為到最後的時候對一場戰爭的反思應該不用再分什麼日本人、中國人了,角川這個時候應該是代表我們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僅僅代表他自己。
張純如吞槍自殺這個事情,我曾經找過很多前前後後的文獻記載包括驗屍報告,那個給她驗屍的美國驗屍官說過這樣一段話:「女人自殺的我見過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氣、上吊,跳樓就是極致了,但是很少會選擇吞槍自殺的,因為起碼會對自己的容顏有一個保留,但是張純如用一個大口徑手槍把自己打死了,她內心經歷過怎麼樣的黑暗?」她的長相是非常罕見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卻選擇了這樣一種方式,把車開到了一邊然後自殺。我在想很多人自殺到底是為什麼,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紐約的船上跳海自殺被救起來了,但是在回去之後還是自殺了,這都是南京大屠殺的結束之後幾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這樣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後受不了內心的煎熬自殺,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誰?像張純如,她顯然是為了這件事死的,要不她為什麼會選擇在這樣的一個年華在她名聲到了那樣的一個階段的時候她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顯然是因為這件事情就像陰影一樣侵蝕到她的身體,她擺脫不了。
我拍到那會的時候,我雖然沒想過自殺尋短見,但是我確實感到特別崩潰,但是我也想表現一種釋然,最後釋放小豆子就是對生活的一種釋然,一種解釋。拍角川死的那場戲,我沒有去寫分鏡頭,就是講戲完之後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場戲,但是拍這場戲的時候我找到了一氣呵成的感覺,那會戲已經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會拍電影的感覺了,我覺得我自由了,不同於一開始我跟自己很較勁的狀態。
《三聯生活周刊》:結局雖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個過程很壓抑,現在觀眾已經習慣了娛樂消費了,你覺得觀眾能不能接受這部電影?換句話來說你對票房有沒有什麼信心?
陸川:我在上海的時候投資方匯集在一起,他們對於我的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別害怕,在同代導演當中我算是特別幸運的,因為有投資方能給我這麼多錢讓我做這麼一夢,大家拿錢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動靜來,我們在上海做了兩場試映,口碑不用說了,但是我一個朋友跟說我:「你們怎麼能給觀眾一個理由讓觀眾進來看?你們只要能讓觀眾進來,餘下的事情就交給電影解決了,但是就怕觀眾不進來,那麼陸川這兩個字還不夠。」這三年半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力氣和責任,如果這片子票房不好的話,我覺得我也無所謂,會有很多人通過人通過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這個片子會長腿走到比我們想像更遠的地方。
(實習生長萌萌、郄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