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最近打開社交媒體,應該可以看到很多像「成功加入羊圈」「如何照顧三隻羊」之類的內容分享。你很可能會對這樣的表述一笑而過,但過後又覺得有地方不對勁,卻又沒法準確地說出到底有哪裏讓你感到不適。
不少人會辯解道:「這只不過是玩笑罷了。」 然而,很多經典的著作和經驗告訴我們,讓人無足輕重的覺得不對勁的事物,最後會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果。對某一群體進行語言矮化也是如此。對特定群體的語言歧視和污名,不僅是給他們貼上一個區別於所謂「正常人」的標籤,還會作為社會過程對他們產生持續性的負面影響。被戲稱的病患不僅要承受病症本身帶來的生理性痛苦,還要承擔稱呼額外帶來的病恥感。
歷史上,很多疾病都有被污名化和被詬病的先例。在醫學尚未發達的19世紀,肺結核曾經被認為是因為病人意志薄弱的偏執意象造成的病症。而把陽性患者稱為動物的「羊」更甚,這種非人化通過將群體他者化、動物化,從而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痛苦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思考,把同為人類同胞的陽性感染者說成「羊」的戲謔式表達,到底冒犯了什麼?
疫情3年來,你大概也常看到有人把陽性感染者戲謔地稱為「羊」,又或是「兩腳羊」,後來還出現了「公羊」「母羊」「老羊」「小羊」這樣按性別、年齡區分的稱呼,某些大白甚至還在自己背上畫上黑白無常「捉羊」的圖案和字樣。

這種將病患矮化、去人性化的傾向,已引發不小的爭議,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曾表示,這種語言羞辱危害不小:「污名化的網絡環境不僅對無辜染病的新冠患者的名譽造成傷害,也會阻礙流調過程中的誠實申報,害怕公佈自己的行程,受到道德譴責,形成越歧視,越欺瞞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一歧視性的污名,非但沒有消退,在疫情防控放開之後,又再次捲土重來,因為很多人根本沒意識到這有什麼問題,甚至還滿不在乎地反問:「有什麼說不得的,那陽了不叫『羊』叫什麼?」
這就需要重新認識一下:為什麼「羊」是對陽性感染者的污名化?
01 難以被察覺的污名化
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原本是一種非正式的稱呼,通俗地說,「羊」其實就是「拐彎抹角地罵人」。
這種諧音梗在單音節的中文裏極為盛行。我向幾位在歐美生活的朋友詢問過,他們在疫情期間都沒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通常也只有兒語、寵物的擬人語中才會使用,尤其像德語這樣非常嚴謹的語言中極少這樣的語言異化現象,不像中文經常放棄正式的說法不用,轉而曲折地影射、諷刺,甚或是同一個詞可以表達截然相反的意味。
這一污名標籤最值得警惕的,是它將受害者非人化。歷史無數次證實,這是社會排斥、敵視的徵兆,往往又推動、激化了這一進程。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936年就發現,多數人都不會折磨和自己一樣的人,「但當別人說此人好像不是人」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有絲毫顧慮了」,因而鼓吹敵視別國的宣傳常常都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勸服一類人相信另一類人並不是真的人類,因此自己有權利對其進行搶奪、詐騙、欺凌甚至謀殺」。
在盧旺達大屠殺中,受害的圖西族長久以來都被蔑稱為「蟑螂」,這使得後來胡圖族民兵在殘酷對待他們時,輕鬆跨過了心理障礙。有個人甚至毫無內疚地將自己的圖西族母親交給那些兇手,說:「我把我的『蟑螂』交給你了。」
肯定會有人說,國內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沒那麼嚴重,有一次,甚至還有人和我辯解說,「非人化」不一定就不好,比如把兒子稱為「犬子」,把才俊稱為「人中龍鳳」,這也算侮辱嗎?他堅持認為,這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羊」在中國文化里也沒什麼負面含義,和「蟑螂」這種一看就讓人厭惡的昆蟲不能相提並論。
孤立地看待一種稱呼,很容易產生這樣的錯覺,因為詞彙的含義取決於社會語境。
「支那」一詞原本也沒有任何歧視中國人的含義,它最初是佛經對梵文里Cina(中國)一詞的音譯,唐宋時日本僧人學到了這個詞,但直到近代才被廣泛用於對中國的蔑稱。決定這個詞彙歧視性內涵的,不是它原本有什麼侮辱性,而是使用它的社會語境。「社會青年」本來也僅指社會閒散人員,但後來卻與一系列負面含義連結,幾乎是「流氓」的代名詞。
更進一步說,歧視與否,要以受歧視者的感受為準。大學裏,我曾聽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說,20世紀80年代她年輕那會兒,「農民」是個形容詞,用來指稱別人土氣。她說完,笑得花枝亂顫,底下也哄堂大笑,但我們幾個農村出身的學生實在笑不出來。「農民」乍看只是一種身份,她似乎也覺察不到這是在污名化,但對農村長大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就是歧視。
02 污名是一個社會過程
將新冠陽性感染者稱為「羊」也是如此:對那些陰性的未感染者來說,或許覺得這只是個戲謔,辯稱並無惡意,然而對那些陽性感染者來說,這意味着自己被降格、區別對待。
很多這類措施,起初乍看都像是無害的,但後來卻污名化了,例如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時,有人建議按武漢身份證開頭的號碼來排查疑似的感染者,連我的武漢朋友都認為這作為權宜之計無可厚非,然而後續的發展卻出乎她的意料:這很快發展為對武漢籍身份證的歧視。也就是說,歧視、污名化不只是一個標記,說到底是一個社會過程。
什麼是污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其開創性研究《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中指出:英語的「污名」(stigma)最初指代身體記號,而做這些記號是為了「暴露攜帶人的道德地位有些不尋常和不光彩」,因而人們通常本能地假定「有污名的人不是什麼好人」,而有了這種假設,「我們就會運用各種各樣的歧視,以此有效地減少他的生活機會,即使這樣做時往往沒有考慮後果」。也就是說,關鍵在於將貼標籤的人區別於「我們」這些「正常人」,並將負面社會特徵與之聯繫起來,然後使他們遭受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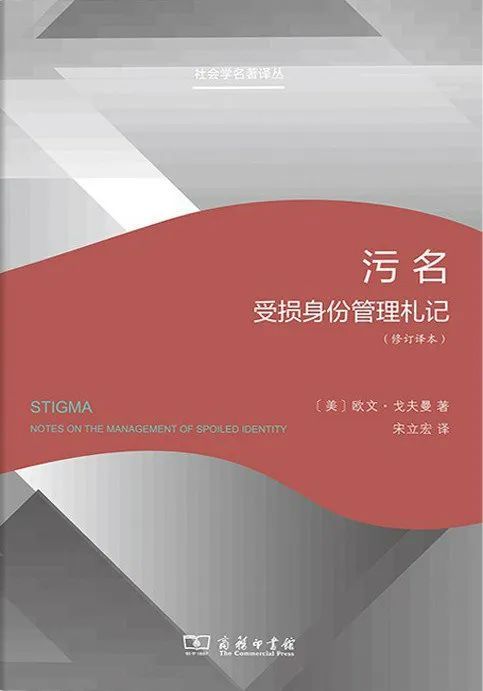
《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美]
這種負面形象只要沒甩掉,就會不時地限制他們正常的社會交往,因為他們已經成了一個有污點的人,受到社會共同體的嘲謔、排斥乃至嚴重傷害。
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回憶:「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會之外,連一般人的社會權利都沒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觸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會成為右派,就像傳染病一樣,所以要把右派分子從正常社會中孤立起來。使得他不至於感染人家。……實質上來講,就是社會隔離問題,這個社會不准許他進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
正如歐文·戈夫曼指出的,「突然蒙受污名所造成的痛苦,其根源不一定在於此人辨別不清自己的身份,而在於他太清楚自己已經成了什麼」,更糟的是,「無論有沒有客觀依據,我們常人都會形成一些概念,認為某人特定的污名起了主要作用,讓他沒有資格勝任某些社交活動」。
將陽性感染者稱為「羊」的行為完全符合這些定義。雖然一個人感染陽性未必是自己有什麼不良習慣的過失,但在管控最緊張的時刻,他們幾乎就被視為「罪人」。
作家鄧安慶在2022年春感染了新冠病毒,結果被物業管家辱罵:「你這個害人精!我們小區本來什麼事情都沒有,都是你害的!我們整個物業都被拉去隔離了!整個小區的人都不能出去!我真的想打死你!」在那個「談陽色變」的時期,這些人很難不被另眼看待,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段屈辱性的經歷。
03 如何才能擺脫污名?
要擺脫污名,僅靠譴責污名化是不夠的,有時甚至適得其反。
人類學家劉紹華發現,在四川的涼山地區,彝族鄉民們原本不存在對愛滋病污名化的問題,然而因為有很多提醒標語,用典型的說教口吻勸告「不要歧視愛滋病人」,結果諷刺的是,鄉民們反倒開始對愛滋病產生了負面詮釋,出現了污名化現象——原本不覺得這是啥大事,但既然上面一直強調反歧視,就有人開始疑惑:是不是這病其實很可怕?
由此也可以看出,污名是和社會語境緊密相關的:一個社會認為是污名的行為、特質,在另一個社會可能根本不當回事。嬉皮士在美國可能被視為時尚、頹廢,但他們來到巴西一個小社區阿倫貝皮後,卻因為穿着打扮異於常人而被認作盜賊——盜竊在別處或許也不算什麼嚴重的罪行,但在當地傳統中,這是一種被高度污名化的反社會行為。
因此,只有認清污名的社會根源,才能有效地消除它。對「羊」的污名從何而來?一言以蔽之,這是因為人們想要通過對被排斥者的污名化,來恢復社會共同體的純潔。
這差不多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能反應,早在19世紀對微生物和感染有科學認識之前,人的厭惡情緒就已經演化為一種下意識的抵禦生物污染的手段。通過將一部分異類排斥出去,主流人群至少在想像中洗刷掉了「污點」,達成了心理學上所說的「自我淨化」(self-purification)。
這種恐懼污染的情緒最尖銳的時候,是「害怕不完成社會的自然界的秩序淨化儀式將會招致災禍的時候,或是有可怕的事發生而大家尋找原因的時候」。被污染的威脅越大,仇恨也就越強烈。
全球化帶來了眼花繚亂的流動,也因此造成了兩種相反的心態:一種是歌頌混雜、互動、交纏,這體現在對「文化雜交」的讚美,很多人相信「混血兒更聰明」也是對以往推崇種族純潔的逆反;但常為人忽視的是,這種大規模的混雜,也讓很多人感到懼怕「被污染」,而試圖排斥移民和異質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對環境污染的關心也有類似的功能:保護社會秩序賴以持續的道德秩序。
只要我們對「純潔性」和「淨化」抱有強烈的偏好,恐懼「污染」,那麼排斥就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過程,而那些被排斥的社會成員勢必就會被污名化。即便陽性感染者痊癒之後,仍然逃脫不了被另眼看待,這就像犯過罪的人即便出獄後重新做人,也仍然是有前科的,換言之,他們仍不能獲得完全的正常地位,而是「從有某種污點的人轉化為有某種污點糾正記錄的人」,就像有一度招工啟事都會標明「陽過的不要」。
既然要消除這種社會根源如此之難,那怎樣才能消除污名?歐文·戈夫曼指出,如果蒙受污名者的道德生涯永遠無法洗白,那至少有一種辦法,就是找到同類,「這時他很可能會突然發現,他與其他也擁有這種污名的人有了一種新的關係」。這就好比殘疾人雖然難以消除社會對自己的歧視,但他們自己在一起時可以獲得一種特殊的紐帶,在這個新群體裏,自己就沒什麼特別了,也不用擔心遭到另眼看待。
不過,更重要的或許是這種經歷的社會共享。科幻電影《第九區》裏,管理外星人事務的官員威庫斯對待這些外星難民相當惡劣隨意,但當他自己被感染後也慢慢變成外星人模樣時,他終於體會到了被歧視的滋味,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
當下出現的情形或許也將與之相似:隨着疫情防控全面放開之後,感染陽性已經不再特殊,對每個人來說恐怕都是遲早要經歷的事,更沒有什麼相應的排斥,這樣一來,對所謂「羊」的歧視也就自然消散了。現在或許需要擔心的倒是一個新問題——會出現對沒感染過的陰性人員的歧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