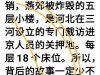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實驗室發生爆炸,致2死9傷。類似事故並不罕見,據媒體統計,僅今年就有3起。作為5年前此類事故的傷者,如今29歲的郭宏振覺得,活下來更艱難。
郭宏振將母校東華大學起訴至法院。今年10月,他等來了勝訴結果:案件終審判決維持原判,學校需賠付他162萬餘元。判決書寫道,東華大學「未盡到安全管理職責,對事故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面對這一結果,他顯得平靜,但那場事故早已將他從既定的人生軌跡里拋離。他圓圓的眼睛、清秀的臉龐被強硫酸灼傷,以致右眼失明,左眼視力0.01(正常人視力的1%),臉上、脖子、雙手等都有疤痕。
原本,他打算研究生畢業後留在上海,進入知名藥企工作,扶持自己的農村家庭,和相愛的女友結婚。事發後,他做了十多次手術,與女友分手,求職屢屢受挫。今年開始,他經人介紹在深圳一家外貿小公司做運營,月薪五六千元。他獨自住在城中村里,房間狹小,床頭越出門框,屋內沒有裝飾,衣物也是暗色。
以下內容根據郭宏振的講述與公開發文整理。
黑暗
如果事故發生時我沒了,那是最好的結果。事發後我經常這樣想。
在那之後,我輾轉多地求醫,並未取得良好效果。我的左眼視力0.01,右眼失明,面部頸部毀容嚴重。我第一次在治療後看見我的臉,是被迫看的。它貼滿了祛疤貼,眼角有黑色的痂,眼袋都是紅腫的,雖然看着模糊,但依然很恐怖。我很震驚,當天沒吃下飯。
從24歲至今,我在墨鏡和口罩下生活了5年。
這給我造成了很多困擾。我的眼前是白色的模糊一片:過馬路看不清紅綠燈,就跟着人流走;去火車站,用手機拍了大屏拿到眼前看,發現沒有自己要坐的那趟車,只能感覺到屏幕動了一下時,再拍一張;認路也很難,我搬來城中村那天就迷路了,晚上在巷子裏兜了半個小時找不到住處,買了瓶水才好意思問老闆,他說就在你旁邊啊。
我出門不會摘口罩,還必須戴墨鏡,幾乎不在餐館吃堂食,都打包帶走。有次我去北京看病,晚上撞到電線杆上,眼鏡掉了,蹲在地上找了半個小時。我這視力是沒法通過佩戴近視鏡矯正的,因為左眼做過角膜移植,上面有疤痕,眼睛不再是球面了。即使我湊近看手機,字體也是模糊、有重影的。
我之前常出去玩,也喜歡打羽毛球、看電影,後來很少出門。有次朋友約我打羽毛球,球掉下來我看不見,就再也沒去過。即使是巨幕電影,我也看不清熒幕上的字。最讓我反感的是人臉識別。換身份證之前,我刷臉進不去高鐵站,人工通道就在旁邊,但我看不到。
起初,生理上的痛苦蓋過了心理上的難受。事發後近兩年,我都沒辦法洗臉。臉上疤痕在瘋狂地長,像腫瘤一樣,我的皮膚變得很硬,打麻醉時針頭都插不進眼瞼下。我每天除了吃飯,都要戴3D打印的硬質面罩,壓着不讓皮膚增生,嘴唇邊墊上硬幣,臉都壓變形了。這讓我呼吸不了,睡不好。
我變得不耐煩,無緣無故朝我媽發火。這種時候我媽都不說話。我對不起她。事發後她趕過來,我只聽見她聲音是顫抖的。
我沒有勇氣輕生。醫院的窗戶也都是封閉的,只能開條縫。有時我站在窗戶前透氣,知道不遠處是上海梅賽德斯。爆炸前一個月,我剛去那裏當過志願者。但我看不清了。
我記不起上次開心是什麼時候了。精神最痛苦的是2018年,我獨自在東華大學延安路校區附近住了一年半。那時我取下了面罩,就讓我媽走了,也和女朋友分了手。我心情不好,失眠了半年。
那段時間我像坐牢一樣,焦慮,同屆的同學都畢業工作了,而我要延期兩年。東華大學是211,我在化學化工與生物工程學院學生物工程專業,很多同學畢業後會進入上海一家知名藥企工作,然後定居當地。
而我在20平米的小單元房裏,過着孤獨、無趣的生活,每天睡到快中午,起來寫論文,點外賣。偶爾傍晚到公園散步,或去買菜。
論文寫得不順利,修改了20多遍,都是錯誤的格式和文字。後來再回那個住處時,看到論文資料、上學時做的筆記,我心裏還是「咯噔」一聲,趕緊把它們都扔了。
第一次取下墨鏡是2019年。有天我早起趕火車,坐地鐵時實在看不清路,猶豫要不要換平光鏡。天還沒亮,車廂里人也不多,可我一直糾結,把手放到墨鏡腳架上,又放下來,反反覆覆。最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跨出了這一步,但全程不敢看周圍人的眼光。其實我也看不清。現在我出門都備着墨鏡和平光鏡,能看見了就馬上換上墨鏡。
那幾年,我在醫院和住所間不斷奔波,起初是每星期去,後來變成了兩周、一個月去一次。我沒有認識新的朋友,也沒有再回學校。我買了一套勵志暢銷書,沒看完,心裏不平靜。我打算學編程,但視力不允許,看一會兒眼睛就酸,眼壓高,偏頭痛。
失眠時,我反覆想,第二天一睜眼,我會不會突然就好了?現在走在路上,我還是會這麼想。但我知道,這是妄想。
悶響

事發時,我在讀研二。那天是2016年9月21日,導師安排研一新生做實驗,製備氧化石墨烯,叮囑兩位師弟如有不懂,可向研二的請教。當時我正在做自己的實驗,師弟問我,我就給他們示範如何將高錳酸鉀加入盛有750ml濃硫酸的錐形瓶中。
在添加了大約30g高錳酸鉀時,發生了爆炸。「砰」地一聲悶響,我嘴裏瞬間含了很多碳粉,眼睛剎那間就看不見了。我心想完了,這輩子差不多就完蛋了。很難描述失明帶來的恐懼,我害怕到除了呼救不知道其他。我發瘋似的往外跑,找不着門在哪裏,摸着牆壁費了好大勁才衝出去,嘴裏不停疾呼「救命」。
很多人趕過來,慌成一團,幫我脫衣服,還說我身上在流血。很感謝隔壁課題組一位老師,一直幫我握住腕部5cm左右的傷口。

上了救護車,我緊張得血壓都兩三百了,醫生一直在說你深呼吸,要不然止不住血。有人不斷拍我的臉,怕我睡過去。我問旁邊的人,我是不是毀容了?他們說,沒事兒,就是有些發黑。聽到這話,我以為住上十幾天院就好了。
但醫生給我清洗時,說我的眼睛「像白煮蛋一樣,熟了」。第二天做手術,我問醫生,我的眼睛能恢復嗎?他說了句,「我儘量」。我沒說話,也沒有哭。後來我才知道,當天我很快被送進ICU。我的手上埋了個針管沒法動,且呼吸困難,護士說沒辦法,已經把氧氣調到最大了。躺在床上十天,我知道問題變嚴重了。
ICU是個噩夢,太壓抑了。我的眼睛能感受到光,但是啥也看不見,只聽見隔壁床住的是個燒傷的老頭,哭着喊爸爸媽媽。後面來了個兩三歲的小孩,也一直哭着要出去找爸爸媽媽。我沒有哭。
臉也變得嚴重,起初是通紅,後來皮膚不斷增生,眼皮拉扯着往外翻,閉不上眼睛。脖子也受了傷,我抬不起頭來,嘴巴也張不開,一個餛飩都塞不到嘴裏。
我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是我,我畢竟只是幫忙做實驗的。
我挺不順的。我老家在河南安陽農村,從初中就開始住校,學校那時教育條件落後,一個小教室擠了120多個人,雙人桌要坐4個人,宿舍3個床板睡上9個人。有的人還沒地方住,晚上直接睡課桌上。
我復讀了一年才考上縣重點高中,全校同屆考上的4個人中有3人是復讀生。到了高中,我的成績在班裏排前十,但高考太緊張了,考語文時填錯了准考證號,接下來都懵了,我感覺完蛋了。
復讀一年後還是沒考好,我去了廣東的一所二本院校讀輕化工程專業。我想上個更高的平台,了解到全國只有東華大學研究生有這個專業,我就報考了,但面試後我被調劑到了生物工程。
爆炸後我只哭過一次。2016年11月,我再次回醫院複查,醫生說我右眼沒希望,可能會萎縮掉,左眼也可能失明。在回去的出租車上,我哭了一路,就靠在椅背上流淚,沒有出聲。哭了半個小時,沒想什麼,就是覺得無助,感覺比宣告你即將結束生命都難受。
我媽說,這個醫生說話太嚇人了,我們換別家看。但結果都一樣。直到幾個月後的一天,我爸扶我上廁所時,我的左眼突然看見了他的衣袖,我頓時十分興奮。但我不敢看我的樣貌。幾年來,我做了十幾次手術。最痛苦的一次來不及麻醉和推進手術室,直接在病房裏做的。那是第一次做完擴張器手術,就是把疤痕邊上皮膚好的地方切開,埋個氣球一樣的東西進去,再不斷地往裏注水,讓皮膚擴張,把旁邊壞的部分去掉。當時左右兩邊臉頰刀口6cm左右,各放入了一個100ml擴張器。
幾年來,我做了十幾次手術。最痛苦的一次來不及麻醉和推進手術室,直接在病房裏做的。那是第一次做完擴張器手術,就是把疤痕邊上皮膚好的地方切開,埋個氣球一樣的東西進去,再不斷地往裏注水,讓皮膚擴張,把旁邊壞的部分去掉。當時左右兩邊臉頰刀口6cm左右,各放入了一個100ml擴張器。
但術後大出血且引流不暢,為此我前後經歷了三次手術。第二天凌晨開始,我的臉部不斷出血,左邊臉頰腫脹,開始發高燒,不停說胡話。當時情況危急,心電圖等各種東西都監測上了。
早上,醫生直接來到病床前搶救。先是拆線,用手擠壓,把擴張器從傷口取出,直接把手插進去摸裏面的血塊,但取不出來,換手術鉗夾棉球在傷口裏攪動,還是沒取乾淨,就往裏邊注射雙氧水,最後重新埋好、縫線。
臉頰兩邊各進行了一遍,持續了一個半小時。我緊緊地閉上眼睛,雙手都在抖,感覺自己臉上切了個洞,皮膚被分層了,他們拿着棉球在裏邊攪來攪去。我一直在大聲地喊,不是因為疼,而是因為恐懼。隔壁床的病友事後說,我的叫聲像殺豬一樣,整棟樓都聽見了。
讓我媽回去後,我都自己一個人去做手術。有時會有些心酸,有次剛做完手術,醫生叫患者家屬來一下,我就自己過去,對方愣了一下。
我覺得打麻藥讓我記憶力下降,認知也不行了,有3次處理臉上疤痕時,我都堅持非全麻。起初醫生不同意,說你受不了的,我說我受得了。那次處理了七八個傷口,我雙手握着拳,疼得全身都是汗。
後來我每次經過醫院,就感覺渾身發抖,各種不舒服。
起訴
事發到現在,我最生氣的一次是學校說停止支付一切費用。
那是2019年7月,我剛做完一個手術。我當場就崩潰了,他們之前不斷地承諾,會負責到底,結果我畢業才20多天就不管了。我從醫院打車到學校,直接去了校長辦公室,校長不在,有人說你再不走就叫保安了。後來一些領導來了,打了幾個電話後說同意支付費用。
我回去後直接睡倒了,渾身沒有一點力氣,從傍晚6點睡到第二天中午12點。很快,校方說解決我的工作問題,讓我辦理殘疾證,之後不用上班,每月領上海市最低工資2000多元,也有社保。
校招我是沒有勇氣去的。那時我每天在各個招聘APP刷簡歷,專業相關的工作不敢再找了,我投的都是教培行業。讀本科時,我就開始做兼職,在輔導機構教過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還在一個職高代過政治課。可當時一直找不到工作,HR打電話時,我都會如實說我的視力很差,然後就沒有後續。
從小我父母就去廣東打工,一兩年才回來一次。他們在五金廠工作,什麼髒活累活都干。我去過那裏打寒假工,手經常被鐵上的刺颳得流血,環境也差,各種機器整天「咚咚咚」地響。幹了12天,我只掙了1100塊。
父母這麼多年也沒攢下什麼錢,除了在老家村里蓋房,剩下的都是給我弟弟報輔導班。他不喜歡學習,現在在廣東讀職高。父母不懂學習上的事,我上學他們就沒有管過,考大學時就說過一句,「你可別考個學費好幾萬的學校」。
我想給家裏減輕負擔,而且我覺得我能工作,可以通過努力工作贏取生活,自然不同意學校的安排。
繼續支付費用的事也沒有解決。校方律師建議我走司法程序,說我們無論給你多少錢,你都會嫌少。2019年8月,我起訴了學校。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負法律責任。事故發生前10天左右,東華大學化工樓就發生過強酸灼傷學生面部的事故,但沒能引起重視。導師在QQ群提醒注意安全,別的什麼都沒說。
我認識這個學生,傷得不嚴重,我就覺得機緣巧合罷了,怎麼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我也知道濃硫酸危險,研一做這個實驗時,師兄就給我拿了雙黑色橡膠手套,再沒有別的防護。大家都這麼做,我以為這就夠了。
這幾年,我通過病友認識了一些有類似遭遇的學生,其中有學生也因為沒戴護目鏡,液體噴發出來,把他一個眼球弄沒了。有武漢高校的老師因為穿了防護服,戴了護目鏡,爆炸時人完全沒事。但我之前壓根兒不知道護目鏡這個東西,實驗室沒有,我們理所應當地認為我們所做的實驗不需要它。
這幾年,每個大學實驗室爆炸事故我都有關注,每次看到我都頭皮發麻。南航發生爆炸後,有人又在網上講學校制定了實驗規則。可關鍵是落實。
我們學校2014年6月制定了研究生手冊,我2015年入學時並沒有收到。手冊里關於實驗室安全管理的若干規定,大部分都沒有落實。比如新生進入實驗室要進行安全培訓,我們那會兒剛見過導師,老師說你以後周末就來實驗室吧。關於危險品管理制度,那個實驗室很隨意,危險藥品向來就是隨用隨取。實驗室之前是雜物間,三個通風櫥兩個是壞掉的,兩個水槽中的一個不出水,我們簡單打掃後就投入使用了。
我讀研一做這個實驗時,初期老師會在關鍵步驟進行指導。到了研二,導師一共帶了8個學生。那天,兩個師弟來問我,我建議他們先去導師處看教學視頻,他們回來後說導師在忙,拒絕了。
錯失
2020年4月底,一審在上海長寧區法院開庭,當月月初學校停止支付醫藥費、生活費。第二次開庭後,法院判決學校未盡到安全管理職責,存在重大過失,要賠付我162萬餘元。學校不服,上訴(編者註:判決書顯示,校方認為郭宏振存在過錯並應承擔責任,他知曉但忽視了本次化學實驗的危險性)。因為沒有對以後治療產生的醫療費用判決,我也上訴了。
校保衛處曾跟我爸媽宣讀調查結論:「郭宏振違規操作是此次爆炸發生的主要原因。」我沒有看到事故調查報告,事後仔細回想,應該是兩名學弟沒有監控好溫度(實驗要求,溫度需要控制在5℃)。
我覺得我應該有責任,畢竟是我在操作,跟我有關。但我又挺委屈的,我明明是在老師的授意下好意幫他們,所以我又覺得我是沒有責任的。
兩個師弟一個重傷一個輕傷,總體比我輕,都基本恢復了,正常畢業。打官司時我找重傷的師弟作證,他說他有苦衷,我就算了。我再找實驗室關係好的同門幫忙,他原本答應,很快又說不記得了,兩人關係就淡了。我不敢再找人,怕沒有朋友了。
我錯過了黃金急救時間。爆炸發生後,實驗室通風處側邊被炸出一個窟窿,我全身數處被玻璃劃傷。被強硫酸灼傷,原本我們需要用大量的水不斷沖洗,至少半個小時。當時我幾乎哭喊着說我要水,有人端過來了一盆水,我就洗了個手,有人給我擦了下臉,很快救護車來了。但上午10點半左右發生的爆炸,因種種原因,我下午三點多才住進醫院。
我之前對兩個師弟確實有怨言,但時間長了,不能老揪着不放。我們後來在醫院碰到過幾次,簡單聊過天,交流哪家醫院哪個醫生好。我從不怪導師,之前我們像朋友一樣,事發時她都快嚇哭了,她也很愧疚,在畢業論文上幫了我很多。
今年10月,二審判決書下來了,維持一審判決。學校連個道歉都沒有。我很平靜,我累了,不會再上訴。
我很感謝我的律師,在她之前我還找過三位,都拒絕了我。她是法律援助,沒收我一分錢。賠的錢我就用來治療,但也不夠支付我去國外做人工角膜手術——醫生說國內做不了。
這幾天我還在和學校溝通後續治療費用的事。我每個月醫藥費要2000多元,臉上修復傷痕的藥膏一支要800多元,太貴我就停了。
父母就更辛苦了,他們現在仍然在工廠打工,一放假就到酒店當服務員,勸不聽。我是爺爺奶奶帶大的,我一直跟他們說我沒事。直到事發3年後第一次回家,長輩才看到我的臉,當場就受不了,說好好的一張臉怎麼變成這樣。我沒跟他們說我的眼睛看不清了。
「殘疾」這個詞,我現在看起來仍舊很刺眼。殘聯不時給我發短訊,讓參加盲人電影、運動會以及領取一些福利,我都沒去。我希望別人把我當正常人,不要同情我。
家裏還很着急我的婚姻大事,給我介紹對象,我只加過一個推脫不掉的女生微信,加上後我就把情況跟她說明了,自然沒有後文。一個姑娘各方面很好,要是突然愛上了我,這是電視劇。
前女友我不想多談,她快結婚了吧。該失去的肯定會失去,你沒有能力阻擋。今年年初,我撿了一隻流浪貓,我一伸手它就過來了。它很黏人,晚上就睡在我旁邊。養了十個月,它最近意外去世了,我很難過。
我現在就想靠自己,努力工作,拼一把。現在的工作是朋友介紹的,在一家小外貿公司做運營,寫文案、給國外客戶發英文郵件等,什麼都干。員工有幾十人,大多是專科學歷。我上班時也不摘口罩,沒跟任何人講過我的事。
有工作需要在同事的電腦上操作時,我都得將鼠標靈敏度調下來。我自己網購了個24寸屏幕,可以左右轉動着看,鼠標指針是明顯的亮黃色,鍵盤還有燈。別人離遠點給我打招呼我看不見,後來人家就不理我了。工作交流時,我在微信上經常打錯字,他們叫我「錯別字大王」。有些同事問我近視多少度,我都不回答。
我現在住在城中村,一個月房租、水電等近兩千。而我月薪是五六千元,我想在上海的同學可能上萬都不止吧。工作強度接近996,但不加班我更焦慮。我希望能把交代的事情做得更好,自己的收入也可能會多一點兒。
我會在這裏待下去。但是人最寶貴的那幾年已經過去了,我的24歲到28歲「嗖」一下就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