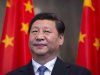多數的暴政自由的國家未必儘是民主的國家,而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會妨礙自由。歷史上有許多自由的國家,但其公民對政治的參與卻受到嚴重的限制。自由與民主,儘管是同為世人所追求的兩個目標,但卻有着各自的內在邏輯。一旦這兩種邏輯互不相容,兩者就會發生衝突。
這是我讀罷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的最大感想。因為,純粹民主的核心特徵是建立在平等主義的多數決定的原則基礎之上的。可是,多數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輕則滋生弊端,重則導致恐怖,最終混滅了自由。與多數決定相一致的原則是平等的原則。該原則認為,眾人的力量應該凌駕於個人的力量之上。多數人的智慧優於個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數比產生文法者的方式更為重要。一旦多數人的權力成為決定一切的權力,這時雖有民主,但卻沒有自由。然而,在這種沒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們充其量不過是心滿意足的奴隸,因為民主中孕育着新專制主義,其形式是中央集權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直接參與的多數專制的政治權力。這種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劇了自由在社會中的逐步失落。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論源自盧梭。
該理論認為,民主是一套以多數統治為原則的政府制度,人民的聲音即是上帝的聲音。
在表達這一聲音時,多數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最高的裁判者,少數總是錯誤的。除去生存的權利和成為多數的權利外,少數不能要求任何權利與多數對抗。這種"天使的蜚語"所產生的疑問是,假定全人類都持有一個觀點,而只有一個人持與此相反的觀點,那麼,全人類的觀點就一定正確,而後者就一定錯嗎?即使如此,全人類有理由讓這個人保持沉默嗎?若是這個人有足夠的理由,而且他的觀點正確,他有理由使全人類都保持沉默嗎?
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講,多數和少數都不握有絕對的權利。多數統治剝奪少數人自由和權利的可能性同樣體現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之中。可是,如果人民都是主權者,誰是主權的對象?要麼是他們自己,要麼是特選的少數人。與多數統治相比,托克維爾發現,對自由的珍愛有其獨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於,當人類精神不關心自由時,繼續當自由的後盾,並給與自由它固有的某種植物性生命,以便人類精神到時候能回到它那裏來。這些制度的形式保證人們即使一時討厭自由,也不會喪失自由。
我認為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優點。當人民執意要當奴隸時,誰也無法阻止他們成為奴隸;
但我認為,自由制度能使他們在獨立中支持一段時間,而無需他們自助。基於自立的自由是可以培養的,而對自由的真正熱愛則是不可傳授的,因為它來自所有偉大的人類的情慾的神秘處: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對自由的熱愛是由於人們只見到自由帶來的物質利益,因為這種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確確,對於那些善於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總會帶來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只有專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
在自由中只欣賞這些好處的人,從未長久保持自由。(第202-203頁)他也發現,多數人呼喚平等自由,一旦得不到,他們便呼喚平等的奴役。基於民主和自由可能存在的衝突,以及民主對自由可能造成的妨礙,托克維爾的困惑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自由還能生存嗎?若是能,自由又如何生存呢?常識告訴人們,民主與專制是相對立的。在歐洲的君主專制時代,民主的敵人是君主個人的獨裁專政。一旦民主取勝,它還有新的敵人嗎?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中令人信服地證明:有!這個敵人就隱藏在民主內部:即多數人的專制。美國的民主與法國的大革命從正反兩個方面表明:多數人的民主的確可以蛻變成多數人的專制。建立在多數同意之上的不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選政府,而且同樣可能是高高聳立的斷頭台。通過對美國民主的考察及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維爾發現,民主作為所有人都參與公共事務的政府參與形式帶有多數人暴政的危險。同樣,民主中隱含着平等主義的傾向,這又帶來了泯滅個性的危險,最終帶來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的共同特徵就是否定自由,因此,這表明,他是個始終如一的保守的自由派,而非民主派。他宣稱,「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第4頁)他毫不猶豫地把自由置於社會平等之上。儘管人們需要在自由上的一律平等,但是作不到這一點時,他們就會選擇奴役上的平等,他們寧願忍耐貧困,也容不得貴族。這就是他對大革命前法國人政治心態的寫照。基於對民主可能妨礙自由的擔心,自由主義提出了衡量自由的另一條標準,即政治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擁有權力者的人頭數,而在於對權力運用方式的控制和運用。
判斷政府的好壞,不在於該政府的權力是在多數人手中,還是在少數人手中,而是這種權力運用的方式、服務的目的和所受限制的程度。對托克維爾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權力,不論歸多少人所有,總是危險的。所以,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答案是,民主應該服從自由。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民主不是與自由同等重要的目的。民主更不僅僅應該是多數人的統治。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換統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國內和平的一種有用的工具。民主不僅在於主權者的人頭數,更在於運用權力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國大革命只是自由與民主的早期爭論的一個歷史記錄。在這場爭論中,焦點是多數的專制。在這一問題上,托克維爾像其他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樣,奮力為個人的權利免受國家的權力,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權力的入侵加以辯護。當代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也回應了托克維爾的觀點。
哈耶克認為,民主並不是多數人的主權,多數人的主權實際上很可能與專制或寡頭政體一樣,是專制主義的。在自由與民主問題上,托克維爾的觀點只不過是古典自由主義大傳統的一個縮印。托克維爾的思想可歸入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大傳統,或者保守的自由主義大傳統。這種傳統起源於柏克、斯密、休謨、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哲學家,與法國的孟德斯鳩、貢斯當,瑞士的布克哈特,美國的聯邦黨以及二十世紀的哈耶克、波普爾等一脈相承。對自由時代的保守主義者來說,還有什麼比保守自由更加至高無上呢?所以,托克維爾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一向認為,自由高於民主,民主不過是自由的一個手段。正像英國的著名自由主義者阿克頓所說的那樣,自由不是通向更高一級政治目標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根本的目標。當代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則把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的界限劃得更清楚,走得也比托克維爾更遠。哈耶克認為,不僅民主政治是個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濟自由的手段。
在哈耶克看來,個人自由的第一要件是經濟自由,而且有其內在的價值。民主的價值,只是一種工具性的。民主政治可以與伸張自由的自由主義並行不悖,甚至在反專制主義的長期鬥爭中相互融合,但是一旦民主成為現實,就有必要把兩者的關係重新區分開來。自由主義和民主是針對不同問題作出的不同反應。自由主義涉及的是政府的職能,而且特別要限制政府的權力。民主的問題涉及的則是,誰通過什麼樣的程序來進行統治。自由主義要求所有的權力,包括多數人的權力都應該受到約束。民主則把多數人的意見看成是對政府權限的唯一限制。民主的反面是君主,自由的反面是奴役。由這種相對應的差別,我們可以看到,自由主義與民主的差異。在自由主義要求限制政府權力的一般法則面前,民主並沒有豁免的特權。所以,意大利政治哲學家博比奧指出,若是把自由主義僅僅看成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思想工具,你可以不加思索地擯棄它,然而,自由主義被理解成致力於限制國家專橫的權力時,你還能輕鬆擯棄它嗎?根據自由主義主張限制國家權力的大傳統,個人在政治權力出現之前就已是特定權利和利益,包括財產權的擁有者。不論是什麼人掌權,甚至是由多數人產生的民主政府的權力,在這方面也應受到限制。在自由的民主國家,消極的自由最為廣泛。
所以,一切權力都有其危險性。因此,唯一公道的政府只是權力受到合法限制的政府。多數人的絕對主權並不比專制君主或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力更值得信賴。
因此,民主與自由的不相容之處,就在於當所有的人都參與決策時,個人就不得不服從於集體的權威,因此,也就有可能失去只屬於個人的自由。所以,民主的產生有其有利於保護自由的一面,同樣,也存在着妨礙自由的危險。如何使自由和民主相容呢?托克維爾把目光投向了市民社會。他認識到,市民社會是民主化和民主制度的一項重要領域,他強調的,不是公民參與政治,而是積極地參與自願的結社,否則就難以保證政體的自由性質和公民個人的自由不致失落。市民社會自身就是社會整合和公眾自由的最重要的領域。考慮到市民社會有助於限制國家政治權力,托克維爾情不自禁地欣賞法國大革命前普遍存在的封建的自由,即建立在封建等級基礎之上的自由,甚至對法國大革命把這種自由掃蕩掉都深為惋惜。
所以,在這一點上,他與柏克頗為接近,即都十分珍視傳統。他認為,舊制度正是大革命的起源和條件。他發現,法國之所以長期受害於威權傳統,是因為行政上的中央集權把社會原子化為個個孤立的個人了,即在社會中剷除了作為中介組織的等級和結社,因而在沒有市民社會的情形下使個人直接地暴露於國家的權力,這樣,個人就形不成民間的力量,也就難以對國家的權力構成有效的牽制。民主政治建立在介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獨立組織和社會集團的存在的基礎之上。若是沒有社會中介的存在,就會出現獨裁或集權政權。這種存在如果不能構成穩定的民主政治的充分條件,至少也構成其必要條件。像在柏克的著作中一樣,在托克維爾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與激進主義相對立的保守主義哲學路線。我們可以看到,兩人對自發的社會結構,如父權制家庭。地方社區、教會和行會等舊制度的尊重(見第二編,第十一章),而激進主義則視之為萬惡之源,並發誓要連根拔除,大有"即使毀滅世界,也要伸張正義"之勢。在挖掘大革命與多數暴政的思想根源時,托克維爾發現,十八世紀法蘭西啟蒙的理性主義難辭其咎:有人說,十八世紀哲學的特點是對人類理性的崇拜,是無限信賴理性的威力,憑此就可以隨意改造法律、規章制度和風尚。應該確切地解釋一下:真正說來,這些哲學家中有一些人並不崇拜人類理性,而是崇拜他們自己的理性。從未有人像他們那樣對共同智慧缺乏信心。······[這種理性]只不過發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第259-260頁)對於作為近代激進主義、極端理性主義、極權民主思想三重始作俑者的盧梭,柏克和托克維爾既欣賞他的天才,但又厭惡其政治與道德學說。柏克宣稱,盧梭是法國大革命的主筆;托克維爾則認為,激進的理性主義應對法國的大革命負責。
根據已知的事實,像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這樣的雅各賓派在革命的高潮期間,虔誠而頻繁地閱讀盧梭的作品。盧梭譴責一切傳統團體,如行會,教會和企業。托克維爾則認為,民主的最大危險就是把普通人擺在第一位,強調多數的價值觀。對大眾的過分依賴會導致平民專制。眾所周知,自由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但是,大革命中的自由不僅成了空洞的口號,而且成了少數人獨享的專橫的權力。因為,盧梭的自由思想本身就是空洞的。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有如說,「魚生來要飛,卻無往不在水中。」(赫爾岑語)
托克維爾則直截了當地指出了自由的界限,"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尋求過大的奴役。"(第179頁)所以,在托克維爾和柏克看來,法國大革命不是對自由的追求,而是對絕對權力的追求。
雅各賓派把法國大革命變成一個對傳統及道德的征服,以自由與平等的名義搞虛無主義,以人民的名義實行極權的專制統治。他們以為,通過對群眾進行說服和教育,必要時藉助強力和恐怖,可以實現對市民、知識分子和農民的改造。用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柏林的分類法,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口號不過是伸張性的積極自由、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而不是消極的自由和有序的自由。若是以為大眾民主,或是建立在代表大眾利益基礎之上的民主可以對人為所欲為,那麼,其所面臨的極權專制的威脅也最大。二十世紀以來,民主變得更加神聖。
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報告中這樣寫到,"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沒人再以反對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種主義。而且對民主的行動和態度的指責常常是針對他人的,但現實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論家在強調他們所擁護的制度和所主張的理論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卻不遺餘力。"
在當代,對民主的威脅,不再是來自公開的敵視,而是來自對民主的過分熱衷和頌揚。
這種熱衷與頌揚,不是給民主以恰當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與自由並駕齊驅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義變相地妨礙、抵消自由。所以,繼法國大革命之後,當自由再次讓位於極端民主的時候,當民主淪為僅僅是多數人的聲音的時候,當這個聲音已不再是正義的聲音,而是恐怖的咒語的時候,法國大革命中的大民主與大恐怖就註定要重演。試想,文革中哪一樁暴行不伴隨着振臂高呼出的多數聲音。這種聲音和暴行又曾令多少人心驚膽顫。受盡凌辱,乃至命歸黃泉。文化大革命聲稱摧毀封建舊制度餘毒,卻通過個人崇拜與全面專政使人受害更深。托克維爾對多數人暴政的擔心絕不是杞人憂天。因為摧毀舊制度不能靠大革命,同樣,"將巴士底獄片片拆毀,並不能使囚徒變成自由人"。追求民主只能緣着追求自由的路徑才能得到;若放棄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導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這或許是托克維爾為全人類總結的政治教訓,這也正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價值日久而彌新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