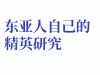主持人:你好,聽眾朋友,歡迎收聽「訪談錄」,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向大家問好!每期「訪談錄」,我們都會為您邀請一位專家學者和大家分享他們的人生感悟、思想精華。今天這一期訪談錄的嘉賓,我們為您請到是旅居德國的詩人、報告文學作家廖亦武先生。
熟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人,恐怕不會不知道作家王小波。他的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被稱為是「20世紀中國文壇最美的收穫」。而今天我們要給大家介紹的廖亦武先生,卻通過他的很多作品提出這樣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真的願意沉默嗎?不,如果你讓他們說,他們的嗓門說不定比天天發言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人,甚至昆蟲、螞蟻,都不是天生願意沉默的。」這麼多年,廖亦武一直在做的就是讓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我們開始今天的訪談之前,首先請嘉遠給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廖亦武先生的生平。
廖亦武,筆名老威。1958年8月出生於四川鹽亭,著名詩人、流亡作家和底層歷史記錄者。他曾榮獲德國書商和平獎等多個重要獎項。
廖亦武自1980年代開始發表現代詩歌。1990年3月,因為在「89」六四前夕寫下詩歌《大屠殺》等原因,廖亦武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監禁4年。出獄之後,廖亦武撰寫了大量中國底層小人物的紀實文學作品,其中包括《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中國上訪村》、《地震瘋人院——四川5月12日大地震記事》等。但這些書在中國或是無法出版、或是出版後立即被禁。
2013年1月和6月,他的監獄自傳《我的證詞》法文版和英文版相繼問世。2016年初秋,廖亦武的長篇小說《輪迴的螞蟻》德文版由法蘭克福菲舍爾出版社推出。
而他的另一本力作《子彈鴉片》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也將在2019年和西方讀者見面。
好,謝謝嘉遠。今天我們訪談錄的第一集呢,就要從廖亦武先生的這本《子彈鴉片》聊起。
記者:您好,廖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首先來談一下您的紀實文學作品《子彈鴉片》。我知道這本書會在「六四」30周年,也就是2019年,在英語和法語世界同時推出最新的修訂本。請問你的這本修訂本和之前出版的版本相比,有哪些補充和修改呢?
廖亦武:十多年前,大約是2005年的時候,當時我遇到一個「六四暴徒」叫武文建,他也是一個藝術家。武文建當時非常憤怒,他就對我說歷史就是你們這些精英所主宰的。我們這些阻擋軍車的人,北京的上百萬市民,這些應該是「六四大屠殺」的主體。也罵我、也罵劉曉波,也罵很多很多人。完全是喪失理性,罵了很多粗話。我當時非常難過,此前我對「六四」所謂「暴徒」的群體根本就不關注,我還沉浸在自己的坐牢、苦難里。然後我說那我的第一個採訪者就是你了。然後在武文建的帶領下,我採訪了十幾個「六四暴徒」。
記者:這個修訂版裏面收錄的人比之前是不是又多了一些?因為我數了一下,加上您有二十一位,是嗎?
廖亦武:對,後來又增加了很多。這個新的版本第一篇是我給余志堅寫的一個悼詞:「這個人死了,越過山巔」。第二篇就是「坦克人王維林傳奇」。之所以把這兩個人放在前面,我認為這是關於「六四」大屠殺的兩個悲劇英雄。
記者:嗯,我知道,王維林至今音訊全無,而被稱為「天安門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堅,您下定決心要在「六四」30周年的時候在西方世界推出您的這本書,很大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對嗎?
廖亦武:對,我個人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余志堅的死。我覺得應該給這些死去的人和倖存者一個交代。總之我覺得我對不起,至少對不起余志堅吧。余志堅他當時就在問我,他說現在也不會英文,在印第安那州,沒有人知道我,我就只能在這個地方做清潔工了。然後他就問我,你那個英文版《子彈鴉片》什麼時候出版?我當時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我說這個是經紀人的事。我當時都沒有想到余志堅、喻東嶽他們也不會英語,中國人知道,西方人不可能知道他們。3月30號,忽然在他妻子的臉書上,看到余志堅居然死了!我當時受了刺激太大了,覺得很對不起他。原來他給我打電話是這麼一個意思,萬一《子彈鴉片》在他生前出來的話肯定有很多人知道他,知道他他就會得到很多幫助。
記者:為什麼這本書起名為《子彈鴉片》?
廖亦武:子彈就是當年共產黨用子彈來對付這些人,然後鄧小平南巡之後就用了鴉片煙,這個麻醉品麻醉了這麼多年。是不是中國人整個被麻醉了?被金錢給麻醉了?然後西方人也被麻醉了,是不是啊?
記者:您說西方人被麻醉是不是說西方也願意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
廖亦武:對,我看西方人和中國人打交道只要中國人撒錢他們就興高采烈,就和吸了鴉片煙差不多。
記者:我看到您這本書里收錄的這群打引號的「六四暴徒」,當時大都只有二十歲上下。因為在「六四」前後幾個小時乃至幾分鐘的反抗,就改變了他們的一生。我很好奇在您的接觸中,他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廖亦武:不僅是北京,還有成都還有其他地方,到最後就已經不是學生了,是市民和共產黨的直接對抗。那當然是採取了一些極端的方式:燒軍車、扔石塊、扔燃燒彈。那個燃燒彈是自己製造的、汽水的瓶子灌滿了汽油,然後把布條塞進瓶子裏面,扔出去。就說「六四」、「六五」,這個最後的階段,包括王維林擋坦克,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學生了,主要是市民。這個我覺得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國的老百姓作為一個主體,直接和獨裁政權這麼地對抗。但是到最後,受到擁戴的只有這些學生領袖,當時他們全部逃到國外去了。吾爾開希還和我講過一個事情,說他們當時在法國,法國總統也接見他們。法國人特別浪漫,把他們當成英雄一樣的接待。拉菲的酒廠還以吾爾開希的名字和頭像,做了一個集裝箱的酒。
記者:所以和學生受到的英雄式的待遇相比,這些所謂的「六四」暴徒,他們的境遇還是非常悲慘,我想請教一下您這些所謂的「六四」暴徒他們平常是一些什麼樣的人?是不是象中共政府宣傳的那樣,十惡不赦?
廖亦武:沒有,他們就是普通的工人、市民。說實在的,就是89年當時成功了、推翻了共產黨,也沒有他們什麼事情。後來我明白余志堅他說的是什麼,他們當時做出了那麼一個壯舉,但是到最後這種人已經銷聲匿跡了,沒有人記得他們。
記者:那我看到您採訪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緩,有的被判無期,大多數坐了接近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長刑期。當然不包括那些已經被處死的。與之相比,在被捕的學生領袖和普通學生當中,很少有人被判處如此之重的刑期。您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廖亦武:這是因為(一方面)學生聚集在西方媒體的聚光燈下,(另一方面學生被)定性為「學生運動」。然後那些老百姓被定性為「社會閒雜」。「社會閒雜」是李鵬發明的一個詞,定性的就是一些流氓、社會渣子、小偷、惡棍。他們的定性是這個樣子,但是學生你沒法這種定性,學生就是學生麼。
記者:我看您這本書的時候真是觸目驚心,感覺一個個故事簡直象人間煉獄一般。您自己在採訪過程中,哪些受訪者的遭遇給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呢?
廖亦武:其實每一個受訪者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比如說判無期徒刑那個王岩,當時把他抓住的時候他正在上班,先把他暴揍一頓,然後帶進北京看守所「王八樓」。那也是大熱天,他擠進去完全沒有縫隙,大家只有站着睡覺,因為根本躺不下,抓了那麼多人。看守就說你們這些「六四暴徒」,(他)讓人拉了六根蛔蟲,那個人居然吧唧吧唧把這六根蛔蟲就吃下去了。還有餘志堅他最後說了一段話讓我很難過,他說這麼多人付出代價。我就問他你對未來有什麼想法,有什麼希望?他說未來沒什麼希望,這麼一個群體會被徹底忘記。我們也不會成為歷史的主角,說得非常絕望,他說中國的未來沒有什麼希望。他還說,反而我們的存在是一種恥辱,會讓那些精英,那些枱面上的人感覺不自在。當時聽了他的這些話我非常震驚。往往我們努力扭轉精英訴說的這麼一個歷史,但是直到今天我們也沒有扭轉。西方人注意的還是一些學生領袖,他們記得的還是這些人啊。
記者:您剛才提到余志堅說他們這個群體的存在甚至對一些精英們來說反而是一種恥辱,您個人的觀察呢?您覺得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為什麼會這樣呢?
廖亦武:那當然,這個世界永遠是精英主宰的。比如說2010年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有一個法國的叫劉偉明,他現在是中國民主黨在法國的負責人,這個人就非常底層。他當時也覺得這是一個很高興的事情,我們自己自費也應該去奧斯陸。當時他們就想進去,因為外面天寒地凍非常冷,他說是冰凍三尺。然後就被皇家衛隊給攔下了,因為他們不在名單以內。然後他說聽見裏面音樂的聲音,裏面精英們碰杯的聲音也聽得見,講話也聽得見,他們就是進不去。在外面兩個小時我差點凍僵了,他說。這些人不可能進得去啊,因為這些人太底層了。
記者:您覺得象余志堅們的悲劇,多大程度上是這種「精英論」造成的?您覺得這種「唯精英論」,是中國特有的價值觀嗎?還是說每個國家都會有、每種文化都會這樣?
廖亦武:這個其實很多年之前就已經發生過。中國人的思維里要努力成為精英,精英之後就很有發言權,這和西方的價值觀完全不一樣,西方的價值觀就說小人物也是有他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聲音。在哈維爾的著作里你就能夠讀到,無權者也有發言權。但是「六四」最早出國的都是一批精英,他們當時說實在還沒有這種意識。你可以從北島、老木他們的簽名,就是89年釋放魏京生的。33個人都是精英,只有精英才有簽名的資格。
記者:最早觸動您寫這本書的是「六四」畫家小武。但在小武跟您談這些之前您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牢獄痛苦之中,您也沒有關注到這個群體,所以您現在譴責別的一些精英沒有關注這個群體,是不是也有些矛盾呢?
廖亦武:對,但是我最起碼有這個自知之明。因為我當時被抓進去的時候我也沒有受到什麼精英待遇,我受了很多折磨。包括用電警棍、筷子捅我的屁眼。象這種我都受過啊。我還和20多個死刑犯關在一起,看着他們上路拉出去槍斃。
記者:我知道您的這本修訂本是為「六四」30周年準備的,您希望讀者通過這本書得到什麼?
廖亦武:總之我覺得出這本書的英文版也許是引起注意的最後機會。30年,西方媒體會注意到這個事情。
記者:您說「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是說讓這些參加「六四」的普通民眾得到一個發出聲音的最後機會,是不是?
廖亦武:對啊,要不然他們又會按照原來的軌跡、每年紀念,他們還是會重溫那個重溫了很多遍的歷史。這些普通老百姓、這些「六四」抗暴者真正的歷史還是會被掩蓋,真相還是會被掩蓋啊。我作為一個時代的錄音機、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是在這個階段起一個作用,就已經足夠了。
聽眾朋友,您剛才收聽的是廖亦武訪談錄的第一集:「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廖亦武說他是時代的錄音機、歷史的見證人。而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廖亦武則是一個非常活躍的詩人。1989年到1990年間,因為在風聲鶴唳中傳播有關「六四」的詩歌《大屠殺》,廖亦武最終身陷囹圄,坐牢4年。在下一集的訪談中,我們將和廖亦武一起回到他吟詩唱歌的1980年代。好,非常感謝您收聽了這一期的訪談錄,我是主持人唐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