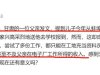父親離開我,已經十年了,十年來,我始終覺得,他一直在的,一直在看着我,猶如他在看守所首次探望我的時候,手撫着我的頭,慈祥的看着我的那個目光……
父親對我是基於厚望的,我中學剛畢業,沒能考入大學,他堅決的拒絕了母親要求我再次復考的想法,把我送到了部隊,四年海軍航空兵的生涯,給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歷練,這應該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大學」。
退役後,我分配至南京某汽車集團公司,進入了人事科擔任人事幹事,因為不是黨員,又沒有學歷,面臨淘汰,所以父母親幫我聯繫了江蘇教育學院的老師,日夜補課,使我終於考入了江蘇省商業管理學院,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大學專科學校。這應該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學」。
臨近畢業那一年,爆發了八九,青春熱血的我,沒有任何遲疑,投入到了這場運動中去,幾個月的腥風血雨,一場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民主風暴,一個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民主夢想,被鄧小平,李鵬的坦克車和機關槍,無情的擊碎了。
我被沒收了畢業證書,我被南京公安局通緝,我被冠以反革命集團首犯,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這應該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學」。
從我被逮捕到宣判,歷經了二年時間,很清楚的記憶,在一個下午,隨着哐當一聲號門被打開,管教老王頭喊了一聲:吳建民接見。我終於等來了見到父母的那一天。
那是關押以來的首次接見,父親,母親,弟弟,妹妹,還有六四南高聯的戰友都來了,因為很多戰友曾經在這個看守所關押過,所以老王管都不給他們進來,只有二個老王頭不認識的同學長鵬和王立隨我父母一起進來看我了。
長鵬和王立蹲下來,往我的襪子裏面塞錢。叮囑我要加強營養。
媽媽,弟弟,妹妹看着剃了光頭的我,都忍不住哭了。
父親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用他的手,撫在我的頭上,我能感覺到,他得手在顫抖,我仰望着父親,沒有看到他的淚,但是我能看到他的心。
關押在龍潭監獄的那些歲月,父母每個月都要坐整整一天的班車來看我,父親是一個軍醫,是二野秦基偉部隊的老戰士,八十年代正師職離休幹部,按照離休待遇,他是可以使用軍車服務的。但是自我出事後,每周我父親的政治學習會議,就是這些經歷過文革的老幹部們,對我父親的冷嘲熱諷會議,說我父親培養了一個反革命,父親很倔強,他一次也沒有使用過軍車來看我。在批准接見的日子父母總是風雨無阻來看我,儘管有的時候,探視的時間只有幾分鐘,他們把帶來的水果和食物交給管理員,和我還沒有說上幾句,就被阻止繼續見面了。
有一次父親來看我,他摸着我的臉,問我:孩子,他們打你了嗎?
我說沒有,
爸爸是當醫生的,你認為爸爸看不出來嗎?
我說爸,這些都過去了,
孩子,告訴爸爸,疼嗎?
我說,不疼,我挺過去了,
孩子,爸爸多麼願意替你,
我聽到爸爸這個話,淚如泉湧……
刑滿回來的那一年,我已經三十五歲了,父親一個人在家門口的小巷等着我,見到我時,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輕聲的問我:回來了?我說爸,我回來了。父親拉着我的手,挺直了他軍人的胸膛說:咱回家。
十年前,父親走了,在他七十八歲的年齡走的,走的太早,
沒有來得及看到我的一對雙胞胎兒女,
沒有來得及看到我六四蒙受苦難的昭雪,
沒有來得及看到中共的垮台,
沒有來得及看到他反革命兒子對中共再次發起的奮力衝擊。
我會記住我的責任,我會在專制滅亡的那一天,來到父親的靈前告慰他,兒子不負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