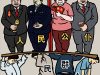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
在1980年代前出生的國人對於四川大地主劉文彩是絕對不陌生的,其「臭名昭著」的「水牢」以及反映其對農民「殘酷壓榨」的群雕「收租院」迄今還刻在不少國人的腦海中,而且迄今還有不少國人並不知曉,「水牢」和「收租院」都只是當局出於政治需要而炮製出來的謊言,真實的劉文彩恰恰是一個大善人。
提到「水牢」,就不能不提及由此「聲名鵲起」、曾「僥倖從水牢裏活着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四川大邑縣農婦冷月英冷媽媽。據說早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愛國模範」冷月英就提出了水牢說:「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劉文彩的侄子)五斗租谷,剛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七天七夜……。」在此,冷月英並沒有明確認定她坐的一定是劉文彩家的水牢。然而,冷月英的經歷讓上級主管部門深受啟發,遂於1954年移花接木設計了「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方案。根據上報大邑縣委的《農業合作化展覽總結》一文,設計這個方案的目的是通過冷月英「解放」前後的鮮明對比,「以達到『想過去,看現在』的目的」。毫無疑問,這個目的達到了,由於在「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環境的佈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圖片也都刻畫得很慘」,所以每個觀眾都能「觸景生情」,「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傷心的眼淚,甚至有引起回憶自己或自己爹媽解放前受地主壓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聲的。」劉文彩水牢就這樣橫空出世。
不過,因為當時的政治大氣候尚稱平和,劉文彩水牢還只是轟動一個小小的大邑,沒有引出更大波瀾。1958年階級鬥爭升溫,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便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以它無聲的恐怖接待來自四面八方的觀眾。冷月英也開始由愛國勞動模範一變而為「階級鬥爭活教材」,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其演講稿則完全由主管部門提供。「黨叫幹啥就幹啥」的冷月英此時大概已是身不由己,講台上的她成了一個徹徹底底的演員,演講稿雖然不是出自她的筆下,她卻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講時能馬上進入角色,簡直是字字血,聲聲淚。她在台上邊講邊哭,哭得像個淚人兒,而台下的聽眾也隨之淚流不止。通過冷月英「活靈活現」的演講,人們知道:「在劉文彩的佛堂側近一個角落裏,秘密修建了水牢。據說,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究竟水牢裏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這個人間地獄裏灌滿了水,屍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裏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佈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而冷月英是僥倖從水牢裏活着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
而冷月英演講的水牢故事,也有多種版本。不同的版本中情節各有不同。一會兒她說自己是1943年被關進劉文彩水牢的,一會兒說她早在1937年就被關進了劉文彩水牢;一會兒說她是劉伯華的佃戶,一會兒說她是劉文彩的佃戶;一會兒說坐水牢期間她沒有見過劉文彩本人,一會兒說坐水牢期間劉文彩提審過她。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訴,讓聽眾們感同身受,特別是那些「一顆紅心向着黨」的筆桿子們紛紛從成都、重慶、北京等地來到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來切實體會水牢。水牢和冷月英從此走出四川,成為了全國人民關注的熱門話題。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為素材的文藝作品相繼問世,關於水牢和冷月英的新聞報導、宣傳畫、連環畫更是不計其數,後來水牢還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成為了劉文彩抹不去的「罪惡」。而水牢的主角冷月英「紅」透全國,其身份也隨之發生了變化。1964年莊園陳列館改館之前,冷月英任唐場蔬菜農場場長兼黨支部書記;改館之後她被提拔為唐場公社黨委副書記,並辦理了「農轉非」手續,從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變成了國家幹部。不過其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充當「階級鬥爭活教材」,文革十年,據說她在全國各地演講了一千多場,聽眾上百萬。
文革結束後,中國由「階級鬥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階級鬥爭活教材」的「冷媽媽」也就永遠地失去了利用價值。1981年9月15日,冷月英正式隱退,同年在接受陳列館人員調查時稱,「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此時,喧囂一時的劉文彩水牢真相也由於知情人的披露、陳列館的進一步調查而開始鬧得沸沸揚揚。最終,水牢的存在被證實是子虛烏有,所謂的「水牢」不過是劉文彩存放鴉片的倉庫。如今地下室門口的一塊木牌上,只寫着四個大字:「鴉片煙室」。
《收租院》的故事就是這樣在當年一些人倚仗強權憑空捏造出來的。
為編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到民間去「訪貧問苦」,他們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橋村14組(原建興村4組)先找到劉文彩的長工呂忠普,用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啟發他,讓他說劉文彩的壞話,呂忠普卻實話實說,說了許多劉文彩的好處,那些藝術家們不想聽,生氣地走了。他們又找到呂忠普對門的鄰居谷能山,他也是劉文彩家的長工。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強健的身軀,對他那副壯實的形象產生了興趣,藝術家們立刻圍着他作起草圖,準備把他樹成反抗劉文彩剝削壓迫的英雄,讓他來出來訴苦會有很大的煽動性。藝術家們用革命理論來動員他出來訴苦,谷能山不願意。藝術家們又說劉文彩每天過着奢侈腐朽的生活,你們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牛馬不如的生活,你應出來控訴他。
谷能山回答說: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個小牙祭,七天一個大牙祭,肉隨便我吃。藝術家們接着給他作了許多工作,後來又對谷能山說:你是貧僱農,是無產階級,是好人;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剝削階級,你要給他劃清界線。谷能山斬釘截鐵地說: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槍斃,我也說他(劉文彩)是個好人!這下藝術家翻臉了,他們很快叫民兵來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兒子對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說:把我父親像關勞改犯一樣關起來,每天給他送飯去。另一個長工呂忠普的兒子呂宏林告訴劉小飛:他父親呂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嚇得連夜步行到50公里外的大山深處的天宮廟煤礦里躲起來(他有個兒子在那裏)。這些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如此恐怖,與他們自己編造的《收租院》裏的打手狗腿子沒有兩樣。
更可笑的是,由於谷能山堅持實話實說,沒有順從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這些藝術家就把谷能山充滿正氣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劉文彩的幫凶,即《收租院》裏的「風風匠」。
《收租院》裏有一個因為交不起租而丟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給劉文彩餵奶的羅二娘的故事。羅二娘在訴苦會上說她給劉文彩餵奶,劉文彩把她的奶頭咬了,還說劉文彩要強姦她。羅二娘第一次訴苦是在安仁的星廷戲院,當她說到上面那些事時,加之她使用的語言很污穢粗俗,本地聽眾當場吐口水,口裏發出鄙視的嘖嘖聲,還有的人說:「你(羅二娘)洗乾淨沒有?」。
安仁的許多民眾說,當羅二娘訴完苦走到街上,她的長子羅學成當眾說她:你不要臉,你去亂說別個(指劉文彩),過去我們的鍋燒壞了還是別個送給我們一口鍋,別個看我們窮還送一頭豬給我們餵。羅二娘的親侄子羅大文說:羅二娘從來就沒進過劉文彩家的大門,她怎麼會去給劉文彩餵奶?羅大文還說解放初羅二娘沒這樣講,土改時也沒這樣講,是「四清」運動時大邑縣朱部長(組織部副部長朱賓康)住在羅二娘家幾個月以後羅二娘才這樣講的。羅大文還說過去每到過年,他們家和二娘家都得到過劉文彩發的錢糧,而羅二娘是本地長相最丑最不愛衛生的婆娘,本地沒一個人答理她。正因為受人冷落,有一種發洩慾,羅二娘才為當局利用。1960年前後,羅二娘的丈夫羅吉安餓死,羅二娘的小女兒餓死,羅二娘的大孫子餓死,羅二娘的大兒媳餓死,一共餓死了四口人。劉文彩卻從來沒傷害過羅二娘。更可笑的是,當局還把羅二娘的故事放在《收租院》裏。
《收租院》裏說劉文彩的鐵板租把農民一年的收成剝削得乾乾淨淨。採訪片《大地主劉文彩》中有採訪者問本地老人:劉文彩收的租多不多?老人回答:「不多」。四川是天府之國,一年收兩季,劉文彩收租只收一季穀子,平均一畝一石,也就是一半,另一季麥子農民全部自得,民安三隊的老貧農李福清說算起來交租佔總收成的30%。而眾多的老貧農,老佃戶都說後來在毛時代交的公糧比給劉文彩交的租多許多。安仁的一個生產隊長羅友志講那時上公糧上米每畝350斤,上麥子200斤;劉文彩只收一石穀子,折合米只有290斤。
從四清運動開始,每個生產小隊就安排一個工作組的人來與農民同吃同住,監視農民,每天不停的給農民洗腦,搞大批判,批判劉文彩剝削壓迫農民,但在那恐怖的歲月依然有人公開說真活,如安仁合興二隊的羅建庭當時說:過去沒吃的時候去找劉文彩,一去就把米要回來了,現在去找公社,這個批那個批,人餓死了都沒批下來。他說了大家想說又不敢說的話,於是大家就幫着傳這句話,傳得非常廣,非常遠,後來傳到當局那裏,就派民兵去把羅建庭抓起來開大會批鬥,會完後當局威脅群眾,誰再講這種話抓住了後果自負。
《收租院》的解說詞的笫一部份是:送租;第二部份是:交租;第三部份是:算賬;第四部份是:逼租;第五部份是:組織起來,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鬥爭。把這些文字讀給本地的老佃戶,老貧農聽,他們都說是瞎球編的,90歲的李福清還說:劉文彩在的時候,這一帶沒有餓死人的事。劉文彩故事的幕後策劃者之一的馬識途,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不慎透露了人民公社時期四川農民交公糧的情況:「據社員說,那幾年徵購糧食徵得太多,把他們的口糧也搜颳得沒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簡直是翻箱倒櫃,整得雞飛狗跳。有的地方關係緊張到社員反抗,不得不派武裝去鎮壓,有的社員對我說,連機關槍都對他們架起來了。」這些場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實寫照,卻被拿來栽在劉文彩的頭上。
馬識途的文章還說:「中央就向四川多徵購20億斤糧食,向中央說了大話,就要兌現,不得不把社員的口糧也徵購了一部份,這樣一來,哪有不餓死人的。」既然馬識途的文章提到餓死人的事,那麼那幾年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據說省檔案館記錄的是810萬人。但據老幹部鄧自力(鄧小平的兄弟)的回憶文章《坎坷人生》中的記載:「老陳說:『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萬,據公安廳統計的還不止這個數,不敢上報。』」1983年出的大邑縣縣誌上有歷年的人口統計:公元1950年303350人;1958年346770人;1959年317673人;1960年295188人;1961年281491人;1962年280906人。由此看出,從1958年到1962年間人口負增長了65854人。
而劉文彩的罪惡故事就是在大饑荒年代中着手編造的。也正是那個民眾大量餓死的歷史背景,編造出來的劉文彩故事才拿來瘋狂炒作,推向全國。
《收租院》裏曾有一篇這樣的文章,題目是《以階鬥爭為綱將革命進行到底》文章有段是這樣寫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步劉少奇,林彪的後塵,否定黨的基本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拼湊反革命的還鄉團,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使『收租院』的悲劇重演,萬惡的地主莊園再現,他的黃梁迷夢,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斗爭中,被革命人民擊得粉碎。歷史豈容逆轉,復辟不得人心。今天我們正沿着社會主義的金光大道,高歌猛進。」
當局把《收租院》的故事編進中小學的教科書,又拍成電影在全國各地反覆放映,更在各種報刊媒體上大肆炒作,煽動民眾的仇恨情緒。為四川和平解放立下汗馬功勞的劉氏家族成了宣傳的犧牲品。劉文彩的二孫子劉世偉,被迫遠逃他鄉,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庫爾勒上游公社獨立大隊落戶。他為人友善,從不與他人結怨。由於《收租院》的宣傳,說劉文彩迫害農民,那裏農民便把劉世偉全家殺了。他的老婆和兩個小孩(大的兩歲,小的還在吃奶)被斧頭劈死,劉世偉被勒死。劉文彩的小兒子劉元貴被成都鐵路局弄去勞改,也死在外面。
《收租院》中還有一個殺人霸產的故事,說劉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三個正在田裏栽秧的貧農打死在田裏。這個故事編出來後官方強迫曹克明承認,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認」了。當藝術家把這個故事塑好後,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15年徒刑。鄧小平上台後法院以量刑過重改判5年把他放了。他不服,他到縣法院去申述,法院的辦案人員對他說我們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們就不敢給你平反。曹克明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鳴,1982年走投無路的曹克明到大邑縣人民法院門口服毒自殺。曹克明死前,一再對兒子曹登貴說:「你要為我伸冤啊!」
據《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3期報道,當年的地主小少爺劉小飛如今已為花甲老人,仍不知疲倦地為他的爺爺——「中國四大地主」之首劉文彩正名。從1990年代起,劉小飛開始自費調查劉文彩的生前身後事,造訪一個個當年的佃戶、長工和鄰居。1998年劉小飛從大邑縣城乘中巴車去安仁的路上,當司機得知他是劉文彩的孫子時,他對劉小飛說:「我爺爺今年95歲了,現在還在,他說的,當年在你們家交公糧的時候,八個人到齊了就開飯,結果編他媽B個啥子《收租院》出來!」有了當年老佃戶的這句話,《收租院》所有的藝術性和它所有的思想性通通落得分文不值!
1941年,劉文彩為了興辦一所公益學校——文彩中學,看中了四川大邑縣安仁鎮南面街口附近的一片稻田和羅、李、楊三家的屋基、墳園。劉文彩動員農民搬遷是這樣做的:用自己的兩畝地換置規劃區的一畝地,用自己的兩間房換置規劃區內的一間房。個別拆遷戶還有額外的優惠。小農陳啟賢本來只有十畝地,按照約定應該給二十畝,但是這時因為劉文彩手裏的地契至少是40畝的數目,劉文彩嫌到縣政府辦事麻煩,乾脆給了他40畝地。誰料陳啟賢因福得禍,就因為這多得的20畝地,大陸建政後成分被劃成地主。兒子陳澤章六歲時跟一個少年口角,那少年一邊大罵「地主狗崽子」,一邊舉起扁擔攔腰砍下去。陳澤章躲閃不及,從此終身殘疾。陳啟賢因為是地主,大躍進時「攻擊三面紅旗」「攻擊大躍進」而身陷牢獄,妻子怕受牽連改嫁他鄉。
劉文彩對學校的建造質量要求極高。他自己投資了3億5千多萬元法幣(合當時美元200多萬元),但資金還是很緊張。即便如此,劉文彩堅持不減一磚一瓦,高標準嚴要求,寧虧自家不虧學校。拿學校的禮堂來舉例。修建此禮堂時,劉文彩要求儘量大些,但是要大到什麼程度呢?長28米,寬23米,面積約644平方米,禮堂的房頂不用一根橫樑,全是鋼材焊接。劉文彩從成都請來了最好的焊接工人,買來了質量上乘的鋼材。這個禮堂至今仍氣派不凡地矗立在學校內。
文彩中學建成了。一個縣級中學,它的規模讓人驚嘆,不說鄉鎮,就連大城市也不多見。開學典禮上,劉文彩當眾宣佈:「學校成立之日,劉家對之不再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劉文彩沒有把學校看成自己的私產,放棄了校產,還規定自己的子女不得佔有,更不能繼承。劉家惟一保留的權力,就是對學校的監督權,及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口頭宣佈後劉文彩還不放心,他特意僱人把自己的訓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學校園裏,讓天下皆知,以防後裔隱匿、篡改。
文彩中學高男一班學生彭學鑫,當年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考入文彩中學後,他的學費和燈油費全部減免,所交伙食費也寥寥無幾,因此在該校順利地讀完高中,後來成了著名的機械專家。彭學鑫曾這樣回憶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學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養了許多人才,特別是把許多貧寒子弟培養出來,這實在是不簡單的事。」
不僅對貧寒學生照顧有加,對外地學生,劉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戰勝利後不久,24軍分到八輛卡車(24軍為劉文彩六弟劉文輝的部隊),劉文彩立刻挑了一輛,當成了文彩中學的校車,專供外地學生上學、回家之用,避免學生長途跋涉的辛苦。在教學設備上也花了大本錢,文彩中學儘量增加圖書室的藏書量及其它文化醫療設施,還大量購進理化實驗儀器,以便學生可進行分組實驗。劉文彩還聘專人在安仁修造發電廠,給學校改善早、晚自習的照明條件。
學校建成3年後,安仁發大水,全鎮被淹,大水從地勢高的仁和街湧進文彩中學,積水一尺多深。退水後,劉文綵帶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這一下,原來居高臨下的仁和街從此比文彩中學矮了半截。以後再發大水,文彩中學得以保全,可仁和街卻經常遭災,當街商戶損失嚴重。別以為劉文彩不顧別人的死活,被淹的仁和街是他獨資興建的,街上大多店鋪是劉文彩自己的,所以受損失最大的還是他自己,但為了中學,劉文彩也顧不了這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