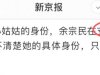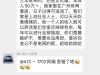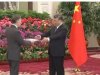設想下這樣一幅場景:有一天,你買了一張頭等艙,但上了飛機,發現不巧有人佔了你的座位,此時,你或許也像央視主持人李小萌一樣把這事放到微博上。
在頭等艙佔了別人座位的事情肯定不會多見,因為航空公司很少會出現讓「重要旅客」位置不佳的情況。事實上,把重要的客人服務好已是航空部門持續多年的任務。在中國民航局的要求下,幾乎所有的航空公司、機場都設有專門接待重要旅客的「要客部」。幾個小時的飛行中努力為他們提供最頂級的VVIP服務。
早在1993年,當時的國家民航總局就已下發《關於重要旅客乘坐民航班機運輸服務工作的規定》(下文簡稱《規定》),制定了詳細的要客服務規定,成為各大航空公司制定要客服務手冊時遵守的範本。
每年兩會、黨代會,或是奧運、亞運、中非論壇這些盛事,民航局都會成立重大航空運輸保障小組,領導航空公司、機場一起保障要客飛行安全。
一般來說,要客享受到的照料從他訂機票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
民航局規定,要客訂座、購票,應該優先保證。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的航空界人士均表示,每個航空公司的內部系統都有一個長長的要客名單。按照民航局上述《規定》的界定,如果訂票者的身份是省、部級(含副職)以上官員,軍隊在職正軍職少將以上軍官,公使、大使級別外交官這樣的重要客人(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要客目錄中,兩院院士也榜上有名),系統就會提醒:要客來了。
起飛前一天,各大始發站都得將次日航班的要客名單表,送至民航局、航空公司、機場及所有業務單位,其中最操心的也是最核心的部門是航空公司。
對於一些特別的要客,航空公司高層要親自迎送,有的會親自駕駛飛機。根據深航的一篇宣傳稿,2009年,一位省部級官員從無錫出發的航班,就是深航無錫分公司總經理親自掌的舵。
到了機場,辦理乘機手續、託運行李這些雜事,要客部門有專人協助。而在硬件一流的機場貴賓休息室專用房間,要想辯認哪位才是省部級以上官員,有時候可以看看他手裏捧的茶具是不是專用的。
「在我們這兒,所有省部級領導都有專用茶具,機場會一直為他保留,新上任的省部級領導也會為他準備一套。」西部某機場要客部服務人員陳偉(化名)說,兩院院士除外。
至於這些重要的客人喜歡喝什麼茶,一旁的服務員都會記錄在案,下次一來便知。「比如西部某省省長最愛普洱,也愛吃鳳梨酥、牛肉乾。」陳偉說。
隨後,會有車輛通過免檢通道將要客先行送達機艙門口,「要客如果來得太趕,不需要在機場停留,直接把車從辦公室一路開到停機坪。」一位知情人士說。對於要客來說,有頭等艙的航班坐頭等艙,沒頭等艙的,民航局規定,航空公司也會給他們挑個舒適的座位。
剛剛坐下,是想來點麵條,還是米飯?是吃軟食,還是硬點的?是中餐,還是西餐?這些很多時候無需要客操心,上飛機之前,空姐們已經會對很多重要客人的喜好有所了解。
海航的空乘人員在一篇公司宣傳稿中回憶,他們曾發現一位重要領導對部分食物過敏,在一次包機任務中為他特製了清淡的餐食。如果是在包機上,要客們還可以享受點餐服務。根據金鹿公務航空公司的一份採購清單,可供要客選擇的菜品有百種之多。
有的時候,飛機就要起飛了,要客卻堵在了路上,這個時候,有的機長會選擇等待。「等個15到20分鐘都很正常,我們一般都跟乘客說是航空管制,大家已經習慣了飛機晚點。」某航空公司要客部空姐王璐(化名)說。
不過乘客為此付出的等待會得到回報。民航局規定,凡是要客乘坐的航班,不得隨意取消或變更,而讓有要客的飛機先飛起來,亦是多年來的原則。
如果飛行旅途中要客想好好休息一下,空姐們則會最大程度地保持安靜。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的乘務員回憶,他們在有要客的客艙巡視時往往是腳掌着地,沒一點「咚咚」的聲音,關洗手間也是極輕極慢地拉動門閂,不發出一點刺耳的噪音。
經過幾個小時的飛行,飛機緩緩降落,按規定,要客會先走;民航局還規定:貼有「VIP」標誌牌的行李應放置在靠近艙門口的位置,以便到達後優先卸機。
要客們微笑着邁出艙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鬆了口氣。對於這些重要的客人而言,這只是一次普通的公務飛行,但對於參與服務的航空業者來說,卻是盡善盡美的巨大挑戰。
在獲悉要客要來的當下,一個VIP保障預案就已經啟動,分工之細,程序之多,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根據各大航空公司公開的地面保障手冊,調度室調來一架狀況最良好的飛機還不夠,維修基地還得對飛機來一次深度體檢,從頭等艙有沒有劃痕窗戶,到發動機整流罩內有沒有殘留的積水和油液,都要一一排查。
同時負責培養VIP航班乘務人才的質量管理室,會展開乘務組人員的預先選拔和培訓,許多航空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同一個標準:「業務精湛,政治過硬」。
業務精湛自然不在話下。根據空姐王璐的說法,空乘必須是氣質出眾、言談優雅、處事周到。至於政治過硬,「說白了,還是從安全出發。如果空乘對社會很仇恨,那還得了。」中國民航管理幹部學院原院長田保華說。很多時候,往往是資深的黨員乘務長才能勝任。
民航局同時規定,各單位對保密的要客乘機動態,儘量縮小知密範圍。「因為擔心恐怖襲擊,登機之前,乘務人員都會和安全員討論安保監控方案。」王璐說。民航局還明確規定,在國務委員、副總理以上要客乘坐的航班上,嚴禁押送犯人、精神病患者乘坐。「如果被要客投訴,整個飛行艙都會依次被降級。」王璐說。航班出港前,乘務組將會收到一份由航空公司運行艙匯編的要客喜好資料,對於這些從各種渠道得知的每個細節,空姐們都要熟知。
要是碰到惡劣的天氣,還要做好吃苦的準備。根據東航一篇宣傳山西客艙部乘務長的報道,有一次,一位省部級官員乘坐航班到達目的地後恰逢大雨,可傘只有兩三把,空姐們不得不冒着大雨一趟趟地護送旅客下飛機。等所有旅客都上了車,空姐們的衣服已經濕透,該官員很感動,打開車窗大聲說:「姑娘們,雨太大,快回去。」
重要客人一句感謝的話,對於空姐們來說是莫大的驚喜——可以獲得不少的績效加分。李軍說,即使是要客私人出行,購買的是經濟艙,航空公司發現後也會通知空姐,提供VVIP服務。
但要是要客們不滿意,受到處罰的可不僅只有他們自己。田保華記得,幾年前,有個重要客人從上海坐飛機到北京開會,當時因為一些事情跟機長吵了起來,沒過多久,民航部門就收到了相關部門的電文通知。
南部某航空公司要客部空乘李軍(化名)說,普通人投訴空乘,公司需要核實情況後再看有沒有效,但要客的投訴通通有效,「如果要客不滿意,整個飛行艙都會依次被降級。」
南航海南分公司的規定更嚴,如果誰在執行要客航班任務中,受到中央領導批評,除了乘務員降級使用兩年,甚至直接開除之外,乘務員所在單位領導也將被追究責任,例如直接責任人所屬部門的副經理、黨政一把手通報批評,罰款2000元。
下如此重罰,源於2009年7月20日一次要客投訴。對於投訴原委,南航海南分公司的網站並沒有透露,只強調這次投訴「嚴重損壞了南航形象,也給客艙部留下了一記疤痕,客艙部將謹記教訓,落實整改」。
就商業而言,航空部門未必是想從這些重要客人那裏獲得什麼回報,而更多的是考慮品牌和口碑的效應。「把要客服務好,有助於樹立品牌,屬於航空公司一個重要營銷手段。」田保華說,「甭說VVIP,一個頭等艙的普通旅客,如果他都不滿意,你想想,誰還坐你的飛機?」
每次要客航班任務完成,乘務長都寫一份總結報告上交客艙服務部。對於航空公司來說,這份包含了要客評價、服務過程的報告,不僅是乘務員培訓的實戰案例,更是宣傳自身形象的重要文案。
一般情況下一篇諸如《××對我公司服務豎起大拇指》的文章將出現在航空公司的主頁,以及各大民航論壇上。這些作者單位多為「航空公司黨群工作部」的稿件,內容上大概是:公司「高度重視」,貴賓「讚不絕口」,一般會附上空姐們和要客的合影。
另外在飛機上,各航空公司也會試圖更多地影響這些重要客人,宣傳自己。海航要求每個VVIP航班都要配備一本企業文化書籍。海航在一篇宣傳稿中稱,有一次,海航旗下的金鹿航空承擔一位重要官員的包機任務,途中,上述重要官員航班的「一些領導對《海航崛起告訴人們什麼》這本書非常感興趣」。
因為有了艙內的良好互動,航空公司和重要客人們之間的彼此了解自然也會延伸到艙外,尤其對一些身份是省部級領導的官員。如果能贏得各地政府的支持,航空公司們自然可以獲得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各地政府官員,也希望航空公司能為地方經濟發展助力。
這種雙贏的格局,同樣存在於航空公司和他們的上級主管部門民航局之間。
一來,由於是民航局下達的上述對待要客的接待要求,使得航空公司可能會為了接待要客犧牲些許的經濟利益。
但另一方面,把要客服務好,在良好的口碑之下,各種業務也會接踵而來。且不說諸如兩會這樣的公務包機,即便是公務人員出國,民航局也儘量考慮了國內公司的利益。
1995年,民航局聯合財政部下發文件,重申公務人員出國時「如無特殊情況,均應乘坐中國民航班機」。一個配套的保障性規定是,報銷時「應憑我國航空企業國際航班機票和專用發票」
機場,航空公司,航空管制,飛機延誤的原因,像一條多方都在拉扯的橡皮筋,扯不斷也理不清。如何讓民用航線這條專家眼中的「縣級公路」變成「高速公路」,人們在體制之外寄望於新技術。
90分鐘航程,兩個小時延誤。這是在廣州工作的余雁今年出行經常撞到的鬱悶事。經常乘飛機出差的他,從上海飛廣州,飛機延誤一小時;從杭州到廣州,晚點兩小時……
幾乎就在一夜之間,人們發現飛機「飛不動」了:航班大面積延誤,旅客們滯留在各地或新或舊的候機大廳,某些時候,甚至被關在艙門緊閉的飛機內在跑道數小時。焦慮、憤怒的情緒在封閉的空間內積累,乘客和航空公司的衝突一直在爆發,三個月前,一位55歲的航空經理,甚至跪在了情緒失控的乘客面前。
在業內人士看來,航空公司「下跪」的姿態,對中國方興未艾的航空大國戰略目前所處的尷尬境地,具有頗深的隱喻意義:它似乎只是拿自己的大腿在行走,慢,笨拙。中國民航局官方給出的航班準點率是76.98%,但像余雁這樣經常坐飛機出差的人,則從自己的切身體會懷疑,航班延誤的數字要比官方給出的更高。是飛機太多了嗎?是民航可資飛行的空域太少了嗎?還是航空公司自身的管理過於滯後?
記者發現,目前中國航空業的管理者、研究者們,正承受着和堵在候機大廳內的乘客同樣的焦慮:截至2010年5月底,中國全民航運輸飛機達到1486 架,按照發展需求預計,中國2015年在冊運輸飛機架數可達2600架,2020年將升至4360架。這幾乎是在以幾何級數增長,但目前如此擁堵的空中交通不免令人擔心。
「航空管制」被潑污水?
很多時候,乘務員給出的航班延誤,似乎只是在敷衍乘客。其中,提及最多的,便是「航空管制」,有一次從杭州到廣州航班延誤,余雁詢問原因,乘務員答覆是因為天氣,她打開電腦了解航路上所有城市天氣,都是晴空萬里,沒有任何雷雨天氣。再次詢問,乘務員又回答是空中管制,但不久機場廣播解釋是,飛機因為調配原因造成延誤。
「空中管制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裏裝。正因為大家不太懂空管,廣播延誤情況時這樣比較好說。」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航空界人士說,航班的運行牽涉到機場管理、航空管理、航空公司管理、機場公安管理等諸多方,任何一方都會影響航班運行。
國家空管新航行系統技術重點實驗室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張軍告訴記者:「將很多延誤都歸為是空中管制所導致,是不合理的。目前從數據統計分析來看,空管原因引起的延誤大概在20%左右。」
中國民航大學劉光才教授經過三年研究得出結論:「2006-2008年我國航班延誤各種原因的統計,三年裏,航空公司分別占 44.2%、45.9%、45.82%,空管分別佔23.8%、24.9%、21.64%,其次是天氣(19.9%、19.7%、22.31%),機場原因(2.0%、0.9%、2.35%)。」
那什麼是「航空管制」?為什麼它會造成航班延誤呢?
「飛機從起飛到降落,一直處在空中交通管制之下。」劉光才教授說。
現代空中交通管制涉及飛行的全過程,即嚴格按預定時間、航線、高度、速度飛行,受機場空域管制中心、沿途航路管制中心和終點機場空域管制中心的指揮與調度。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管制空域分為四種類型,即高空管制空域(A類空域)、中低空管制空域(B類空域)、進近(終端)管制空域(C類空域)和機場管制地帶(D類空域)。
比如一架飛機要從機場起飛,那麼出發前5分鐘會向地面管制匯報,好讓塔台有一個準備。5分鐘過後飛機會向地面管制提出放行申請,這時地面管制會向飛機頒發放行許可(主要內容就是飛行航線等信息),之後便向飛機指明該從哪條跑道起飛……
「空中管制的影響因素包括:民航自身管理上的原因、突發事件、軍事演習軍隊飛行管制,還有重要人物保障等。」張軍說,「這個時候必須限制某空域的航班飛行。」
但「空中管制」導致的大部分延誤,集中在大機場的終端區。就像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流量很大,到了收費口容易堵,「空中高速路」的終端區也是有個「收費口」——下降的時候就可能發生擁堵。「其中很大的程度上是終端區流量控制,那麼多航班排着,特別是前面有航班積壓過來以後,後面等的就會加重流量的控制。」中國空軍空管專家陳志傑少將說。
拋開上述兩個原因,有業內人士指出,中國空管的效率和空管人員整體素質不高,也導致一些空域資源被浪費掉了。
「現在的安全責任是跟官本位掛鈎的,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讓你飛,飛機在地上趴着是最安全的,有這種管理理念,怎麼可能提高效率?」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航空界人士說,一些防雷性能比較高、制動性能好的飛機,在天氣不好的時候,一些航班稍微做些調整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因為空管部門往往一刀切,管制流程人為干預過度,導致了不必要的延誤。
有人比喻中國航線的現狀:開車的希望有更多道路,民航也希望有更多的道路,而且希望每條道路能夠容納下更多的車輛。但是目前還是處於縣級公路的水平,並且這條道路還在被一個特殊的體制管理着。
中國空管體制屬於軍民融合體制。是國家空管委領導下,由空軍負責統一組織實施,軍民航分別對航路內外的航空器提供管制指揮服務,即「統一管制、分別指揮」。上世紀80年代,中國民航才從軍隊序列分離出來,民航在空中有固定航路,而軍用飛機可以相對自由地飛行。這種「不平等」延續至今。
民航局空管局副總工程師文立斌在6月21日舉行的全國政協民航調研座談會上指出,中國空域在劃設上條塊分割,在管理上以空軍為主體,在協調上以軍航為主導,在程序上民航申請、軍航審批,在使用上民航局僅限於航路航線。
比如民用航空公司申請新的高度層飛行,只有得到軍隊批准後,向民航局申請時才有意義。在具體的某次航班飛行中,如遇到雷雨等特殊天氣,需要繞飛,也需要空軍批准。「如果你飛上去了,空軍不讓你繞飛,你就得返航,那我不如在機場呆着呢!」
空軍專家陳志傑少將對記者作出回應:「有些媒體報道,民航只佔了百分之幾十空域,實際並不是這樣,從1080萬平方公里空域而言,分為可航空域和非可航空域,並不都是可用的。」
陳志傑解釋說,中國空域面臨的現實是,要保證軍隊各級管制區、民航28個高空管制區、37個中低空管制區所有軍民機場高效運轉,讓通信、導航、情報、氣象保障各種系統協調運行,讓軍事飛行和民航飛行互不干擾,確實很難……這必然導致空中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合理、有效的利用。
在現實環境下,陳志傑提出了以「融」為主的頂層設計思路:「軍方空域並沒有24小時在用,軍民兩方可以協調使用,我們稱之為空域靈活使用技術。軍民航空管制部門之間,如果能夠採取更充分、更完整的信息共享,未來飛機上飛行員都能夠看得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由飛行員自己來選擇這個航線。」
陳志傑說,融合軍隊和民航用戶的需要,融合航管諸要素的功能,實現軍民航空管一體化,實現空管空防一體化,可以在現有條件下,提高航線的運轉效率。
現在的困境是,中國民航這條「縣級公路」上的汽車越來越多。在管理體制短期內無法突圍的前提下,張軍、陳志傑均認為,可以通過一些技術上的改善來提高運轉效率。
張軍和陳志傑分別引領着民航和軍隊在進行新航行系統技術的研究。在他們看來,天空是一個大的立體箱子,航路絕對不是在天上劃幾根線,而是20公里寬、加上飛行高度的設定的一個立體通道。需要沿着這個航路基礎之上,提供通信、導航,監視的一種服務能力,航路的水平取決於通信的水平、導航的水平和監視的水平。「容量需求越來越大,但容量並不僅僅取決於機場地面硬件設施的擴張。這是一個管理問題,也是一個技術問題。」張軍認為,航空運輸業需要通過技術進步提高科學管理水平,通過採用優化航線結構、數碼化放行、為飛機提供及時的氣象服務、建立流量調配機制等空管新技術,會使問題得到改善。
像在美國丹佛那樣的國家真正意義上的樞紐機場還沒有建立起來。「要利用新技術建立新型的星基新航行系統航路,並提供安全、可靠的空中交通服務。」張軍強調,「治理延誤還需要對空管、航空公司和機場進行綜合治理。」
在陳志傑看來,「治理航班延誤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實際是上要發展我們的衛星技術。」北斗二代運行以後,其定位、通信、時間等等都會為航管應用提供非常廣闊的天空,特別是這個新系統,最大的優勢是飛得精確了。
在眾說紛紜之際,中國早已開始了把自動相關監視(ADS)技術、衛星導航技術和數據鏈技術運用到空管系統中的研究。
「風的影響,空氣的影響,對整個空域容納那麼多架飛機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了衛星以後,最大的優勢是飛得更精確了。天上飛機多了以後,如果我們國內用北斗的話就可以增加更大的空域。」陳志傑說,「整個工程涉及衛星導航和現代通信技術等新技術新潮流,我們現在正在建設國家飛行流量控制中心,準備2011 年建好,這就可以保證國家以後對領空進行有效管理,發揮空間最大效能。」
「未來通信系統,導航系統,監視系統都『搬』到天上去了,就變成以衛星為主了,就是星基新航行系統航路,是一種新型的航路。」張軍說。
另外一些業內人士建議,能不能把飛往諸如廣州的航班分流到佛山、東莞的支線機場。佛山跟廣州很近,高鐵和地鐵都可以接過來。張軍很贊同這種觀點,因為這種「樹狀機場」形式在美國很多城市都被採用。
據新華社11月14日報道,國務院、中央軍委近日印發《關於深化我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見》,對深化我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作出部署。
中國公務航空公司董事長廖學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改革意見的出台是中國低空開放的重要一步,相信更多實施細則很快就會出台。」他認為,此次意見最大亮點在於,4000米以下低空飛行無需報批只需報備,這打破了國內通用航空業發展的制度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