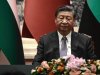當團派真正全面執政之後,他們長期形成的跟從領導的習慣變成了一個致命的弱點,因為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的中國需要的是能夠做出決策的領導人,而團派不習慣決策,但又沒有人可以繼續跟從。不僅如此,優柔寡斷的團派還必將面臨政治上強勢而又有治理經驗的技術官僚和太子黨們的挑戰。由此看來,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權將喪失在團派的手中可能並非是無稽之談。
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無論是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還是中央委員會,出身共青團的成員的人數必將大幅度上升。對這一點,中外政治分析家們似乎沒有什麼的異議。團派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物?他們的崛起對中國的政治格局究竟意味着什麼?這正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無論是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還是中央委員會,出身共青團的成員的人數必將大幅度上升。對這一點,中外政治分析家們似乎沒有什麼的異議。團派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物?他們的崛起對中國的政治格局究竟意味着什麼?這正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團派的定義及成分
在繼續討論之前,有必要先統一團派的定義。人們通常說說的團派,主要是指那些曾經在共青團的中央委員會和省一級的團的領導機構擔任過主要負責人,現在又在中央和省部一級的黨和政府機構擔任主要負責人的那些人。由於現今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曾經擔任過團中央的第一書記,而被稱之為團派的成員多與他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所以團派成員在政治上的發展便格外地引人注目。
團派在中國政壇的上升具有必然性。這是因為由於青年團組織的性質,團各級組織的負責人必須由相對年輕的人來擔任,這使得他們在中共的官僚系統中與同級的官員們相比,具有了年齡上的優勢。再加上由於工作的性質,團的負責人大多與當地的黨的一把手有比較多的接觸,這為他們在轉業後的迅速升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正由於此,在胡錦濤成為中共的一把手之後,團派在他周圍迅速地聚集便顯得是水到渠成,甚至連他的反對派也找不到什麼把柄。
團派的成分其實很不相同。一些人在青年團的崗位上工作的時間很短。他們中的許多人之前已經在不同的崗位上擔任了領導幹部,把他們放在團的崗位上,只不過是為他們在中共的幹部體系中提供的一條升遷快車道而已。例如,文革後期的團中央第一書記韓英、文革結束後的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瑞環、以及現在被看作是團派領軍人物的王兆國、胡錦濤等人。這些人在調入團中央以前都已經是相當一級的政府或國企官員,而且他們擔任團的負責人的時間也都不長。團的工作崗位對他們而言顯然只是一個過渡。這樣的例子在各省、市還有一些。團派中的這部分人,相對說來操作能力比較強,在權力鬥爭中也比較強悍。他們在團派中只是少數。
團派中的另一部分人則是長期在團的系統工作的。他們大多從學校起就擔任學生幹部,畢業後或是留在學校擔任團的幹部、或是分配到團中央、團省市位擔任團的幹部。他們在團的系統內升遷,直到擔任團的中央書記或省市團省委書記,然後轉業到其他的黨、政工作崗位。這些人已經成為當今團派的主要力量,包括人們常常談到的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陝西省長袁純清等人。這一部分團派成員,除了個別人之外,真正地從事黨政實際工作的閱歷較淺。
團派對中國政壇的不可預測性
共青團的性質是黨的助手。包括團中央、團省市為在內的各級團的領導機構,在中共系統內級別很高,但是與其他同級的部、廳、司、局相比,他們的人權、財權、物權都很小。同時,由於他們的工作不像地方工作和部門工作那樣有明確的指標和責任,所以對他們能力的判斷多半只是看他們是否能夠領會領導人的意志。長此以往,形成了這部分人會說不能幹,不敢獨立負責,沒有創見等職業特點。這一點在那些長期在團的系統內發展的人身上特別明顯。在轉業擔任地方或者部門領導人之後,他們多半是依靠當地原有官僚機構的慣性,很少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鮮明烙印。不像從基層打拼出來的幹部,無論是好事壞,個性都十分鮮明,如習近平在福建和浙江、薄熙來在遼寧、王岐山在廣東和海南。
也正是由於這個特點,團派人物在中國政壇的崛起給中國的未來帶來了巨大的不可預測性。在文革之後,面對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執政的失望,為了應對黨的領導的合法性危機,鄧小平以降的領導人將最容易做的事情都做了,留給下一代領導人的是一個矛盾更加突出的社會。當團派真正全面執政之後,他們長期形成的跟從領導的習慣變成了一個致命的弱點,因為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的中國需要的是能夠做出決策的領導人,而團派不習慣決策,但又沒有人可以繼續跟從。不僅如此,優柔寡斷的團派還必將面臨政治上強勢而又有治理經驗的技術官僚和太子黨們的挑戰。由此看來,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權將喪失在團派的手中可能並非是無稽之談。
——原載《動向》雜誌2007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