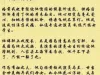曾經有人把秋雨寫的歷史散文稱之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口紅」,確實是很有見地的觀點。至少,我讀秋雨那些「文化苦旅」散文的感覺,除了對他把文章寫得朗朗上口有點印象之外,幾乎從中體味不到什麼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獨到的歷史見解,卻仿佛在聽一個無恥的上海三流戲子在自己的書齋里自言自語,絮絮叨叨地對着當代戲班首領的畫像傾訴其師爺的戲班中發生的那些道聽途說來的往事和韻事。我想,我的這個感覺絕對不是獨一無二的。
前些年,上海學者張閎在他評論秋雨的文章《我為什麼要批余秋雨》(注1)一文中說:「作為散文家的余秋雨,他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傾向和價值立場是值得認真反思的。余秋雨代表了中國文人在現實世界中左右逢源、如魚得水的典型品格。在任何時代,他都是時代的寵兒。從《學習與批判》時代到市場經濟和民族主義泛濫的時代,余總是能恰當地撓到主流文化的癢處,他實際上是接過了楊朔的接力棒,他用虛誇的民族主義熱情,替換了楊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與楊文的赤裸裸的高亢謳歌不同,余文用竊竊私語和交頭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歷史和文化的燦爛碎屑,掩蓋了這一切,因而顯得更為隱秘和曖昧。」
我一直以為,張閎對秋雨的批判在文化的層面上,確實深入到了他的骨髓:「通過他(指秋雨)的散文,總是可以看到他在歷史迷霧所籠罩的深閨中,向現實發出迷人的媚笑。這種迷人的笑容,很容易被一般讀者理解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們甚至感謝余用虛偽的文化光芒照亮了自己蒙昧的雙眼。正是在這種曖昧不明的狀態下,余文贏得了市場。在文體上,余文則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化之最惡俗和浮誇的一面。有人把這種文體稱作『娓語』的當代復活,但這種變異了的、用來向主流和市場雙重獻媚的『娓語』,不如直截了當地叫做『媚語』。」
如果要我來為秋雨的散文找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我認為只有「無恥」二字才能概括其精神實質。我甚至認為,誰要是說秋雨是「文痞」或「文化流氓」,都是過分地誇獎了他,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長一根能做「痞子」和「流氓」的脊樑。秋雨,其實就是神州這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道德荒漠裏,因為缺乏羞恥感的滋潤而長成的一個無恥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他靠的既無恥又無情地對走進了歷史的大小人物胡亂鞭屍而名傳遐邇並獲得文化市場的。這,就是我最近重讀了他早先寫的《道士塔》(注3)和最近寫的奇文《我說的就是這個名字》(注4)而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
我們先來看看,秋雨在他的奇文《道士塔》中是如何既無恥又無情地對可憐的小人物王道士鞭屍的。秋雨在文中繪聲繪色地寫到:「歷史已有記載,他(指可憐的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見過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周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裏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齣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淒艷的晚霞。那裏,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尤其令人無法想像的是,秋雨仿佛就是王道士當時身邊的道童或豢養的一隻狗轉世一樣,他對王道士當年的一舉一動居然刻畫的令人嘆為觀止的栩栩如生:「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里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着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顏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這兒空氣乾燥,一會兒石灰已經干透。什麼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淨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順便打聽了一下石灰的市價。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當幾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顯得過分惹眼。在一個乾乾淨淨的農舍里,她們婀娜的體態過於招搖,她們柔柔的淺笑有點尷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個道士,何不在這裏搞上幾個天師、靈官菩薩?他吩咐幫手去借幾個鐵錘,讓原先幾座雕塑委曲一下。事情幹得不賴,才幾下,婀娜的體態變成碎片,柔美的淺笑變成了泥巴。聽說鄰村有幾個泥匠,請了來,拌點泥,開始堆塑他的天師和靈官。泥匠說從沒幹過這種活計,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點意思就成。於是,像頑童堆造雪人,這裏是鼻子,這裏是手腳,總算也能穩穩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們刷白。畫一雙眼,還有鬍子,像模象樣。道士吐了一口氣,謝過幾個泥匠,再作下一步籌劃。」
對我等此生都難以涉足一回敦煌的凡夫俗子而言,秋雨的上述描述是永遠無法去核實的,也是永遠無法去印證的。可憐的王道士被秋雨胡亂鞭屍後殘忍地按在中國歷史的糞缸里,似乎永遠不得超生了。
然而,書寫中國歷史和王道士的歷史,畢竟不是秋雨一個人可以包辦的。據作家華山劍在他新近寫的文章《余秋雨的〈道士塔〉憑什麼選進教材》(注5)一文中說:「筆者也親身去敦煌考察過,像王道士這樣的故事,筆者也在敦煌和蘭州地區就聽到過,因此,筆者去敦煌之後就尋找到了文物保護部門的人員打聽了這個流傳於世的關於王道士的故事是否屬實,那些文物保護部門的朋友們全部都哈哈一笑了之,他們都勸筆者不要相信那些街頭巷尾的類似於評書那樣的傳說,一個文物專家回答的很好,他說,一個普通道士算老幾,他能夠做主把文物低價賣給外國人麼,說王道士沒有看護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說他破壞了敦煌文物,那都是舊社會中不了解內幕的人們不敢和無證據去直接指責政府當局而把王道士當替罪羊的說法,其實,當時那些偷運和掠奪敦煌文物的外國人,不都拿着中國政府當局的護照和相關文件進來的麼,有的還是中國政府當局派兵護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過是個居住在敦煌中的很普通的居士,他有什麼資格和能力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況的發生呢!由此可見,發生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敦煌文物和破壞的主要原因,還是應該是當時中國國內政局混亂和軍閥亂來所致,就像孫殿英為自己軍隊集軍資就開挖清朝墳墓的那樣,就像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歷朝歷代的戰亂,都造成了文物書籍的大量破壞厄運的那樣。」
看到沒有,無恥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秋雨在書齋里憑空杜撰的極度煽情的「文化苦旅」散文,居然是靠如此無厘頭的捏造事實,和對王道士這樣的可憐蟲一樣的小人物的毫無根據的殘忍而又無情地胡亂「鞭屍」,終於贏得了中國一大群沒有文化的無腦兒們高聲喝彩和持久不斷的掌聲,其捏造史實的奇文竟然被選進了中學教材而流毒深遠。秋雨也因此而登堂入室步入文化殿堂,進而被著名的CCTV捧上了神州的文化巔峰來當華夏文明的判官。
也許秋雨可能在《道士塔》一文中對可憐的王道士鞭屍得逞後忘乎所以,這回他作為上海市委、市政府曾經的著名文化顧問,同樣可以對成了政壇上廢物的「良宇」進行政治上的「鞭屍」。誰料想,當他把自己的獻醜加獻媚的奇文《我說的就是這個名字》剛發表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他用來「鞭屍」得心應手的那根滾壯的鞭子才剛剛落下,就有許多人立馬抓住了他那雙長了眼睛的巧手,從而把他那副無恥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嘴臉永遠定格在了歷史的鏡像之中。
如,知名網絡作家張銳在他的文章《鞭屍者余秋雨的滑稽戲》(注2)一文中寫到:「秋雨的文章大意是,陳良宇在位時,滬上的教授、學者多次在學術討論中向陳良宇獻媚。大師說,學者、教授們失去人格的吹捧習慣,助長了某些領導人的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總之,大師很不爽,陳良宇在位的時候,大師不爽在心裏,陳良宇倒台了,大師說,看看看看,我早就覺得不對了吧,阿拉說的就是這個名字。」
看到沒有,在張銳的筆下,一個無恥之尤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活脫躍然紙上。在這裏,我想還是選用秋雨寫於十多年前的《小人》(注6)一文中的文字來描述他,才最能刻畫他那無恥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的真正面目,也才能顯得既惟妙惟肖又極具喜劇、鬧劇和活報劇的三重效果:
秋雨確實「知道一點文化品格的基本經緯,因而總要花費不少力氣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就是民族氣節和文化品格的最後代表。」
秋雨非常擅長於對那些走進了歷史的死人和政治殭屍「潑上很多髒水而使他們無以言辯」,從而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捍衛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別人說的特點倒栽在別人身上。」
秋雨用自己那雙長了眼睛的手上的一支巧筆,「幾乎沒有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像模像樣地做過什麼,除了阿諛就是誹謗。」
秋雨,他是當代中國的文化人不假,但卻是個無恥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如果有人非要問我為什麼要把余秋雨親切地喚作「秋雨」?我的想法是,這是為了最後好借用一下秋雨的著名標題:我說的就是這個名字:余秋雨。